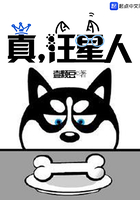刘嫂赶忙过来,先请了安,见贺义同与那女子全身都湿了,遂道:“我去给你们烧水,顺道煮碗姜汤。”撑了伞,向后院去了。刘峥又拿了干净的毛巾,贺义同已帮善香解开辫子,刚好取过来为她擦着头发,动作轻柔的很。刘峥看得有些懵,他是跟着十几岁的少爷来这里读书的,后来怕这里荒置了,也就没有再回贺府。出国前每隔数月,贺义同都会来这里休息几日,可总不见他会照顾自己,如今,却照顾起别人来了!刘峥暗自笑了笑,道:“少爷,我去看看水烧好了没。”贺义同点头,善香却低头鞠躬,用很生涩的中文说:“谢谢。”刘峥愕然,呆了半晌,料不到她是个日本人,诧异的看着她,也不觉得有先前那般美丽了,甚至还有点厌烦。但一想到贺义同对她的态度,不好说什么,只尴尬的嘿嘿两声,就自去了。
善香歪着头,眨眨眼睛,轻声问,“他不高兴了么?”贺义同似明白了几分,索然道:“没有,你别乱想。”双手去握她的手,放到唇边吻了吻。善香却忽然把左手抽回,向身后一藏,慌张的说:“我把右手给你。”突如其来的反应,让贺义同不得不惊诧。他把善香的左手,强硬的拽出来,心头就是一痛,仿佛被千斤重锤猛击一样。眼睛,不离那尾指的部位,是空的,竟是被齐根切断。托着那只手,背心里生生透出虚汗,是谁?谁会下如此的狠心,去伤害一个纤纤弱质的女子?颤抖地去碰了碰那疤痕,低声问,“一定很疼吧?”眉睫揪到了一处。善香抿着嘴,好半天才幽幽的说:“很丑是不是?贺君,你还会喜欢我吗?”语气里满是惶恐。她怯怯的看着贺义同,那眸子,宛如受到猎人袭击的小兽。
外面的雨声很大,贺义同却只能听到自己的心声,从此以后,绝不能再令善香受到一星半点的伤害!摸着她的脸,承诺道:“喜欢。我不是早说过,这辈子,心都不会辜负你的吗?”善香听了一恸,哭着说:“贺君,我对不起你。”停了一停,哽咽道:“你走后没多久,我就被松本亨抓了,他要我陪他,我不肯。贺君,我是真的不肯的……所以……他却还是不肯放过我!是阿部君救了我,安排我来找你,可他……他为了救我,被松本亨杀了。贺君,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贺义同一下子没反应过来,那晴天霹雳,打得他好似到了十八层地狱。不晓得是第几声对不起,才把他叫回到人间,怨声道:“善香,你没有对不起我,是这不太平的世道,让我们都失去了太多。健一的心肠实在好,就算不是你,他也会救的。在西点军校读书的时候,他就向往和平。”不禁苦笑,继而道:“和平?鬼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和平!善香,为了健一,我们也要开心的活着。答应我,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要放弃,好吗?”善香重重的点头。
门,吱咯一声的开了,是刘嫂。她送来了热水,还有两套半新的衣裳,“少爷、善香小姐,把湿衣裳换一换吧。这还是刚结婚那前儿做的,也不成个样子,可眼下,实在找不到好的衣裳了。”贺义同谢过了刘嫂,善香也跟着说了声,“谢谢。”刘嫂打量着善香,不免可惜着,这样温婉的女孩子,怎么会是个日本人!疑惑的出去,过了有两刻钟,又送来了姜汤。那时贺义同已换上了刘峥的灰鼠长衫,因他身材高大,长衫倒显得短了好几截,人看上去也是有些可笑的。善香在一旁哧哧的笑着,看到刘嫂,又客气的点了下头。刘嫂却是眼前一亮,那酒红色滚黑碎辫的无袖旗袍,仿佛是为善香量体而裁,本就玲珑有致的身体,更含了风韵。难怪少爷会对她一往情深,人漂亮,又懂礼貌!连连望了好几眼,才收拾着把换下的衣裳拿下去,预备洗。善香不好意思地阻止着,慢吞吞的说:“还是……我自己来吧。”刘嫂道:“这些粗活,应该我做的。善香小姐,快点把姜汤喝了,不然真的要伤风了。”迅速的走了,留下一脸感念的善香,在不停的鞠躬。
拉回善香,贺义同一字一字的叮咛着,“这里不是日本,不用逢人就鞠躬哈腰的。善香,以后对我也不必那么客气,还是像以前那样,叫我仲谦吧。”善香顺从的应了声,“是。”贺义同笑了笑,看看天色,依旧烟雨凄迷,但月亮上了中天,时候定然不早。喂善香喝完姜汤,道:“天气不好,又实在晚了,我叫刘嫂给你下碗面,明天再带你去吃桂林风味,好吗?”善香一把搂住他,依依不舍的说:“你要回去了?仲谦,我不想你走。”贺义同拍着善香的背,低声哄着,“你总要好好的休息,我在这里,不方便。”善香的眼眶红了,眼看泪珠就要掉下,她扭开脸,轻轻的问:“我一直都在害怕,你是不是嫌弃我了?”贺义同急忙解释,“我没有嫌弃你。善香,但是在中国,很多事情是必须先过了礼的。”善香慢慢松开了手,只拿泪眼望着他,一声也不出。那目光像网似的,罩住了贺义同,瞧着他的心,仿佛漓江的水波,流的再远也想回到源头。最后是缴械投降,陪她一同吃了面,看着她睡着,才安心得离开。
雨夜里郊外的路,格外难走。风一阵一阵的刮大了,天气好像是骤然间寒冷到结了冰,贺义同握着方向盘的手,不觉抖动着,心也在抖动着,他困惑于健一的死。又不能问善香详细的经过,一来怕触动到她的痛处,二来她一个女孩子,能懂什么?可健一的死,毕竟是因为他,假若他没有把善香托付给健一,结果就不会是这样!无比自责着,却什么也不能做。那种无力的痛苦,慢慢的渗入骨髓,折磨着他,没有尽头。
回到家里,已是后半夜了。书房里的灯,还没有熄,他知道一定是父亲。贺宅的仆从不少,要看到他是带着个女人走的,一点不困难。乖乖的进了书房,对父亲承认,“是善香来找我,怕您生气,没带她进……”早晚都要说,不如趁这个机会,表明立场。贺言则干笑一声,打断了那未说完的话。削瘦的脸颊就出现了一道道的皱纹,好似大地被赤日所晒,爆裂的样子。一瞬不瞬的盯着贺义同,不悦道:“那你还真是知道孝顺,顾着我这把老骨头!你要是不想把我气死,明天,明天你就送她回日本!”贺义同没答应,只说:“父亲,我做不到。善香为了我,不辞辛劳的来这个语言不通的国度,一片深情厚意,我绝不能负了她!你与母亲同意我娶她,我只有感激二老对她的认同;不同意,那我只好不要你们的祝福娶她。父亲,你根本不了解善香,就这样对她全盘的否定,对她公平吗?”贺言则冷声道:“不需要了解。善香再好,也改变不了她是一个日本人的事实!中日战争是迟早的事儿,别忘了,你还是一个军人!”喟然一叹,缓声道:“仲谦,你醒醒吧。善香能来找你,我不是一点都不感动,她为了我儿子,连性命都不顾。这样的女孩子,确实难得。可是仲谦,百姓的眼睛只会看到她是一个日本人,而不会看到她是一个好人,这就是社会里的现实,你不可能摆脱了社会独立的生活!自己想想吧。如果你还是坚持要娶她,我不会再阻止,却也不会承认她是贺家的媳妇。”蹒跚的走向门外,停下步子,多说了句,“仲谦,希望你别叫我和你母亲失望。”
目送父亲消失在夜幕里,贺义同心乱如麻,一边是亲情,一边是爱情。以前,他可以轻而易举的选择亲情而舍弃爱情,可现在,心中的天平已明显的倾向了善香。她为他吃了太多的苦,受了太多的罪,他不能不选择她!在京都时,他就知道爱她是错的,但是开始了,便无法回头。他错的义无返顾!现在要同她在一起,不过是错无可错,那又如何呢?身处乱世,总会遇到形形色色不得已的错!思前想后了一个晚上,决定立即带善香回来与父母相处,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说不定他们会看到善香的好,继而接纳她。希望虽然渺茫,总比没有要好!
翌日天气晴暖,院子里的芍药花开了,争妍斗艳的,热热闹闹。他去了衙门,因心里惦记着善香,多少是心不在焉的办公。过了晌午,就火急火燎的去了漓江小屋。善香正坐在屋檐下乘凉,桂林的气候,比起京都,简直就是火炉。她一路南下的寻来,始终不适应这样的热。手摇着扇子,一下一下,看到贺义同来了,顿时嫣然一笑,把扇子一扔,就向他跑去。贺义同见她还是穿着昨日的旗袍,娉娉婷婷的衬在幽竹的屋壁上,酒红碧翠,有一种张扬的美。长发在风里飘飞,摇曳生姿。不知怎的,就想到了早晨起来,那盛开的芍药花。双手一伸,就将善香抱了个满怀,脉脉的香,叫他心旌摇荡。搂着她,含笑道:“去跟刘嫂他们辞行吧。今天,带你去见父亲、母亲。”善香灿烂的笑了笑,神情紧张得问,“伯父、伯母会喜欢我吗?”贺义同安慰道:“为什么不喜欢?你既乖巧,又听话,一定会喜欢的。”却更像是对自己说的。
车子刚进市区,因善香说饿,贺义同就带她去了鸿禧轩,那是家极不起眼的小馆子,埋没在巷子深处。也是偶然的机会,他知道的,因是地道的广西风味,就更为难得。巷子太窄,车子进不去,只得徒步。身旁有几株木笔开的正好,香气清清淡淡,馥郁的令人心也跟着软了起来。贺义同伸出手,“善香。”背着光,脸色暗暗的,可看在善香眼里,还是眉目清朗。心里喜悦的冒着泡泡,全是蜜一样的甜,她把手放了上去。亲亲密密的,两人进了鸿禧轩。来中国,还是第一次吃馆子,不免新鲜,瞧什么都是好的,结果满满点了一桌子的菜。贺义同朗声一笑,道:“最该点的偏偏没点。”回头又要了客新菇炖山瑞,旋即对善香说:“这才是广西的传统名菜。”善香吐了吐舌头,就用筷子挑起个水煮田螺,放在嘴边吸了吸,酸酸辣辣的,叫她不停嘘着气。贺义同递了杯水,“快喝点儿。”用手指轻轻擦掉了她脸上刚粘的辣椒酱。善香却是把脸,又向贺义同身边凑近了,示意他继续。但他只是捏了下她的鼻子,两人相视一笑,但觉温馨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