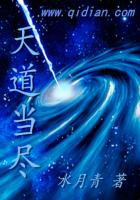如果对这类病人脑皮层上的某点加以刺激,就会不断地引发普鲁斯特式的重现或回忆。我们不禁要想,到底是什么在起作用呢?大脑组织的哪一部分能导致发生这样的现象?目前我们对于大脑运作与表现的研究还处在基本层面上,所以,对于这方面的描述大多采用概论、模拟、类比的方式。但显然仅凭这些还不够从艺术的角度提供丰富的个人经验,用数字的方式再现脑部的运作,再精确的手段也没有办法让画面重现。因为,这些画面是由生活的点点滴滴拼凑成的。
因此,我们从患者身上得知的,和生理学家告诉我们的一切之间,出现了差距,应该说是断层。会不会存在跨越断层的桥梁呢?如果不存在的话,有没有任何观点可以超越那些陈旧理论的束缚,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人类基本的天性和生命片段的再现呢?简单来说,我们能否在机械的理论之上,创建一门人性化的生理学?在《人类本质》一书中,谢林顿也暗示了这一点,他把人的心智比作一台“魔法织布机”,总是织出不断变化却又饱含深意的花样。事实上,它织出来的就是具有意义的图案……
这种有意义的样式却可以超越单纯的形式化、数字化的范式,让存在于记忆、知觉与动作里的个人的基本品质流露出来。深奥的电脑样式需要用图像或程序来呈现,同样,个性化的样式需要用剧本或乐谱表现出来。因此,在大脑的程序之上,一定还有大脑的剧本或乐谱。
我猜,《复活节进行曲》的乐章早已深深刻在欧麦太太的脑海里面,在最初的那一刻,她耳中听到、心中感受到的乐章就全部烙印下来,成为印象深刻的经验。欧康太太的情况也差不多,她脑中充满戏剧性的记忆,虽然表面上遗忘了,却依然可以全部恢复,且这部分记忆镌刻着她儿时一幕幕的场景。
我们也要指出,就彭菲尔德的病例来看,即使只是除去脑皮层??些许的痉挛点,或切掉一小块引起记忆重现的敏感区,都能完全消除反复播放的景象,从而把毫不寻常的记忆重现或记忆兴奋转换成完全奇特的失忆或健忘。还有一件特别重要、格外惊人的事:所谓的通过脑神经手术来改变人的身份这样的神经外科手术完全有可能实现。这样的手术比一般的截肢与脑叶切除手术要精细得多,而且更加专业化。它可能使整个人格变得扭曲或压抑,但还是无法触及个人经验。
只有组织成具体的形式,经验才能称之为经验,行动才能称之为行动。大脑对每件事的鲜活记录都是形象的。即使刚开始可能是数字式的或程序化的,大脑最后仍然会采用形象化的形式记录。这种记录一定是精细的场景,或者可说是各种经验和行动的旋律。
同理,如果大脑的再现器官受到破坏或损毁(比如健忘症、失认症、运动机能障碍等等),要重组这些景象(如果可能的话)需要双管齐下,既试着修复损坏的程序和系统(苏联神经学者正在研究这样的手段),又直接对内在音乐与场景采取措施。两种方式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交叉使用。如果要了解并帮助脑损伤病人,最好同时使用系统化与艺术化疗法。
一百年前就已经有人提到过这些方法了:杰克逊起初对于记忆重现的描述(1880年)、科萨科夫研究的失忆症、弗洛伊德与安东研究的失认症(1890年),都朝这个方向努力。随着系统生理学的兴起,他们敏锐的洞察力已经差不多被忽略和遗忘了。如今是回顾这些理论、启用这些理论的时候了,这可以让我们在这个时代里,开创一种崭新美丽的、有关存在的科学疗法,并与系统的理论相结合,从而为我们提供全面的理解。
六十三岁的不良“少女”
在治疗癫痫症或偏头痛病人时,我偶尔会遇到记忆重现的状况,特别是在使用左旋多巴而变得兴奋的脑炎后遗症病人身上,这种现象很常见。由于这种病人见得太多,以至于我把左旋多巴称为“一种奇怪的个人时间机器”。尤其是有个病人身上出现的状况,实在是太戏剧化了,所以我将她的案例写成文章并投稿到1970年6月的《柳叶刀》季刊(下文会再次引用)。在文中我论述的是精确的记忆重现,这种症状是遥远尘封的记忆突然大量涌现。后来在《觉醒》一书中记录这位病人(罗斯)的病例时,我较少从记忆重现的角度来思考,而是多以“停滞”这一词来形容。(我在文中写道:“是不是她的生命在1926年之后就是一片空白?”)哈罗德·品特也曾在《一种阿拉斯加人》一书中使用这样的词语来描述黛博拉的状况。
左旋多巴最惊人的作用之一,是某些脑炎后遗症病人服用之后,会出现发生在疾病早期的、已经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症状或行为。在这一点上,我们已经谈到,病人会有呼吸暂停、动眼神经危象、运动机能亢奋及抽搐等症状。同时还能观察到许多“静态的”初期症状,例如肌肉阵挛、暴食症、焦渴症、性欲亢进、中枢性疼痛、强迫症等。在更高层次的功能上,我们看到深思熟虑、受感情影响的道德境界、思维系统、做梦及记忆等,都出现了回到过去、变得活跃的现象,而这些功能早已被遗忘和压抑,或者运动机能受损,甚至是瘫痪,或者受到脑炎后遗症的压迫,因而失去反应,不能活动了。
唤醒已成“化石”的记忆
由于服用左旋多巴引起的强迫性记忆重现症,在一名六十三岁的老妇人身上表现得很严重。她从十八岁起就患上脑炎后遗症和帕金森病,且不断恶化,伴随着无法停止的剧烈眼动,在辽养院里住了二十四年。左旋多巴起先非常有效地使她从帕金森症与动眼神经危象中得到解脱,让她差不多可以正常说话和行动。很快,(就像其他几个病人一样)她出现了过度亢奋与任性而为的现象。这个时期最显著的表现就是回到过去,十分快乐地认为她正是年轻时的那个自己,同时也情不自禁地回想起曾有过的性记忆。病人要了一台录音机,在几天内录下了数不清的淫秽歌曲、黄色笑话和打油诗。所有的素材都是来自于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一些聚会时的闲言碎语、淫秽漫画或者夜总会的表演。这些叙述让人重新回忆起过去那个年代发生的事情,她说话时用到以前的俗语和腔调,不禁让人想起那个时代的轻佻女郎。对于这种情况,没有人比患者自己更惊讶了。“实在是太奇怪了,”她说,“我真搞不懂,已经四十年了,我都没听过,甚至没想过这些事情了。我都不知道自己还记得这些事情,但现在它们一直不断地从我的脑袋里冒出来。”由于她持续亢奋,我们就减少了左旋多巴的剂量。而这样做的结果是,病人虽然变得比较有条理,但立刻把所有早年的记忆忘得一干二净,再也想不起任何一小段她录下的歌曲了。
强迫性的记忆重现常常和似曾相识的感觉联系在一起,也和杰克逊医生所说的“双重意识”有关,在偏头痛或癫痫症发作时经常出现,或在服用了安眠药、精神病发作的状态下时有发生。不那么戏剧化的是,当我们听到某些话、声音,看到某些景象,特别是闻到某些气味时,每个人都可能有这样的体会。根据记载,动眼神经危象发作时也会使记忆突然大量涌现。彭菲尔德与珀罗曾经通过刺激脑皮层上发生癫痫的那一点,成功地引发了某些固定的回忆,并据此推论,自然产生或人为引发的癫痫会重新激发这类病人大脑中“已经成了化石的回忆”。
我们认为,病人(跟每个人一样)脑中堆积了多得几乎数不清的“休眠”状态的记忆,其中某些记忆在特殊的条件下会重新活跃,这一现象在异常兴奋的时候更为明显。我们认为,这些记忆的路径就像大脑皮层上刻下的印记,记载着很久以前发生的、早已被现在的精神生活遗忘的事情,它们仍然鲜明地刻画在神经系统内。由于没有受到刺激或者保存得很好,这些记忆可能永远都处于休止状态并一直保留下去。而这些记忆被再度启动所造成的效应,可能和当初完全一样,而且能够相互影响。
因为左旋多巴、脑部探针、偏头痛、癫痫等引起的强迫性记忆,都可看做是由刺激引发的;因为年纪过大或酒醉引发的、不能自已的回忆,则更像是记忆通道被重新打开。所有这一切都能释放记忆,也都能让人重新体验过去,重新界定过去。
回到印度去
巴嘉罕蒂是一位患有恶性脑瘤的十九岁印度女孩,1978年进了我们的疗养院。她的肿瘤属于星形细胞瘤。第一次发病时她才七岁,当时还仅仅是低恶性的肿瘤,还能得到有效控制并完全切除,从而使她恢复常态,重返正常的人生。
她的病十年之内都没有发作,这期间她尽情地享受生活,带着感恩的心情和自知之明尽兴地过日子。她是个开朗的女孩,知道自己的头部有一颗定时炸弹。
她十八岁那年肿瘤复发,更为恶性并开始扩散,且再也无法切除。降压手术使肿瘤进一步扩张,也造成了左侧身体的软弱无力和麻木,同时带来不定时的癫痫发作和其他问题。于是,巴嘉罕蒂住进了医院。
一开始她相当坦然,似乎一切都可以听天由命。但是她仍然渴望走入人群做些事情,在她有生之年享受和体验人生。肿瘤寸寸逼近她的颞叶,而做减压手术的部位开始膨胀,于是,我们使用类固醇来减轻她的脑水肿。她的癫痫发作越来越频繁,状况也越来越怪异。
刚开始的时候,癫痫大发作只是偶尔发生,但是病情恶化之后又出现了新的症状。她没有丧失知觉,但是,感觉上却好像在做梦一样。很容易确定的是(可以用脑电图来确认),此时她的颞叶痉挛正在频繁发作。这种情况就是杰克逊所讲的,通常会出现梦境和无意识的记忆重现症。
很快,这种模糊的梦幻状态变得更明确、更具体、更有视觉特征。慢慢开始出现印度的影像(风景、村庄、房屋、花园),这一切,巴嘉罕蒂立刻就认出,是她熟知且钟爱的童年乐土。
“如果使你感到痛苦,”我们对她说,“我们可以改变用药。”
“不。”她带着安详的笑容,向我们诉说,“我喜欢这些梦,它们引领我回到我的故乡。”
有时候梦里会出现人群,他们通常是她故乡的亲人和邻居。偶尔会有谈话、吟唱或舞蹈。有时候在寺庙,有时候在墓地,但绝大部分是在平原、田地,还有低矮肥沃的、伸向地平线的山冈。
回到童年
这些都是颞叶痉挛的结果吗?乍看起来似乎是这样,但现在我们却越来越不确定,因为颞叶痉挛常常伴有非常固定的模式:单一的景象或歌曲随脑皮层里的固定点被刺激而不断地重复。然而巴嘉罕蒂的梦却并非固定不变,她眼前的景观千变万化,瞬间又消逝而去。会不会是注射的类固醇过量,造成了中毒并产生幻觉?这似乎有可能,但是我们无法降低类固醇的用量,不然她可能会陷入昏迷,并在几天内死亡。所谓的类固醇精神病患者常常会情绪激动、行为混乱,巴嘉罕蒂却始终头脑清晰、情绪稳定。用弗洛伊德学说的观点来解释,她是在幻想或做梦吗,或者是精神分裂症中偶尔会出现的那种梦疯癫呢?这又让我们难以确定。虽然梦境千变万化,但那些幻影显然全是记忆,它们跟正常的意识与知觉同时出现(正如我们知道的,杰克逊把它叫做“双重意识”),而且并未表现出明显的、过度的激情。它们似乎更像一幅幅画面或一首首交响乐,时而快乐时而悲伤,不断地被唤起,然后消失,来来回回地穿梭于珍贵的童年记忆中。
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那梦境和幻觉来得愈加频繁、愈加深入。现在它们已不再只是偶然出现,而是占据了大半天的时光。我们会看见她全神贯注地处在恍惚状态,一会儿紧闭双眼,一会儿又睁开,对当下的环境视而不见,脸上总挂着神秘的微笑,任何人只要走近她或询问她事情(例如护士要做些例行检查工作),她都会非常清楚、有礼貌地立即给予回应,但即使是最迟钝的人也能察觉到她活在另一个世界里,我们不该去打扰她。我试着去分享她的这种感觉,虽然好奇不已,却难以查明,有一次也--只有那么一次,我对她说:“巴嘉罕蒂,发生什么事了?”
“我快死了,”她回答说,“正要回家去,回到我来的地方,可以说是落叶归根。”
又过了一周,巴嘉罕蒂对外界的刺激已经没有任何反应,看上去似乎把自己完全封存在了那个空间里,虽然闭着眼睛,但是脸上仍然挂满微笑。“她正在回家的路上,”看护人员说,“过不了多久她就会到家了。”三天后,巴嘉罕蒂去世了,或者我们该说,她已经完成了前往印度的旅程,到家了。
那段拥有狗鼻的岁月
斯蒂芬今年二十二岁,是一所医学院的学生,因为吸毒而变得神志不清。
有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栩栩如生的梦,梦到自己变成一条狗,置身于一个超乎想象、充满各种味道,而且意义非凡的世界中(水的味道是快乐……石头的味道是勇敢)。醒来之后,他发现自己正处在这样一个世界:“就好像我过去是完全的色盲,却突然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色彩缤纷的世界。”事实上,他连对于色彩的辨识能力都增强了,“某个地方,以前我只能看见一种棕色,现在我可以辨认出十几种棕色。我用书皮包起来的书,以前看起来都差不多,现在所有的书在色调上都各不相同,大有区别”。同时他的视觉能力与记忆能力也戏剧化地增强了,“我以前不会画画,我没办法在脑中‘看见’东西,如今心里却好像有台照相机。我‘看得见’每一样东西,他们就像投射在纸上一样,我只要把我‘看到’的东西的轮廓画出来就可以了。我也突然可以画出最精确的解剖图了”。
嗅觉像狗一样灵敏
不过真正改变他的世界的,则是对味道的超常分辨能力:“我梦到自己是一条狗,这是一个充满气味的梦,当我醒来的时候,我真的走进了一个有无尽气味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其他感官能力再强,跟嗅觉比起来还是显得苍白无力。”随之而来的还有某种颤动、渴望的情绪以及一种奇怪的怀旧之情,仿佛这是一个被人遗忘的、若即若离的世界。
“我走进了一个香水店。”他继续说,“我的鼻子向来不怎么敏感,但现在却可以马上分辨出各种味道。我发觉每一种味道都很独特,都能为我勾勒出一个完整的世界。”他发现自己可以用味道来辨认他的每个朋友,还有病人。“我走进诊所,像狗一样抽动鼻子,在我还没有看到人之前,我就能够闻出有二十个病人在那里。每一个人都有其嗅觉上的特点,一张充满气味特征的脸,这比任何视觉中的脸更鲜明,更容易让人想起,也更容易让人记住。”他能像狗一样闻出人们的情绪:恐惧、满足、性欲高涨。他还能嗅出每条街道、每家店面的味道。他能靠着嗅觉逛遍纽约,从不会迷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