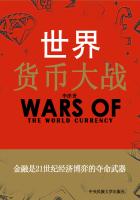他的用意是说:
中国的外交策略,不必联俄拒英,也不必联英拒俄,这些国家各自有利益打算,“非有爱于我也”。以海关加税的事来说,中国政府应独立决策,否则与殖民地何异。梁认为关税本是国内行政之一环,有主权的国家应有独立的关税权,即使偶用外人,任免权仍应在我手中。尤其中国海关岁入几占国库总收入的三分之一,要整理国家财政,更应将关税权回收。
然而,当清政府在1906年4月下令,要把各海关所用华洋人员统归节制时,梁却反对此事,理由是:此事于理宜行,于时势则不可行。(19:68)
为何清廷会有这项突兀的举动?这是长期受到不平等待遇心结的反应,也是因为主管机关变动后,在政治作为上不协调的结果。中国海关虽由外人主导,但形式上从1861年起就属于总理衙门统辖。
1901年“总理衙门”改称“外务部”,海关也跟着改属此部。1906年清廷成立税务处,把原属于外交部门的海关统辖权,改隶属于财政部门的税务处。1906年4月16日,清廷给海关总税务司一项札文,内称:“户部尚书铁良着派充督办税务大臣,外务部右郎唐绍仪着派充会办大臣。所有海关所用华洋人员统归节制。钦此。”这对各国政府确实是一项大震撼,但清廷有此动作并非毫无前兆:从1904年3月起,清廷就开始限制、削弱海关的权限(刚成立的商部接管了海关的商标注册权);同年9月接管由海关主办了30年的“国际博览会”中国的展出权;1905年10月伍廷芳上奏建议收回治外法权。
梁在《关税权问题》内,先说明中国海关的沿革变迁:在五口通商之前,进出口额不大,政府任由行商随意征收。1842年《南京条约》之后,由驻扎通商口岸的各国领事征收;1851年之后中国政府收回此项权利,但既无经验又无效率,因而怨声载道,终与各国协议,通商口岸税务司以欧美人充任,时为1854年。因英国占华对外贸易之大半,故历来皆以英人主持。自1854年之后设总税务司,中国政府已无权过问。梁总结这50多年海关史的变迁:“而所以致此者,实缘我前此着着放弃权利,倒太阿而授人以柄,……此前此所造之恶因,而今日受其恶果,无可逃避者也。”(19:70)海关总税分司的人员编制,在1899年时已膨胀至将近6000人,其中欧美人居高位者有60余人。如今朝廷突然下令将华洋人员统归节制,此项耸动之举必引人疑虑其背后动机:不知中国是否日后不再屡行前此所订的诸项通商条约,或是进一步要把海关税率订定权收回。梁认为中国政府在未说明动机的情况下骤然有此变动,可谓“不度德、不量力”(19:73)。因为中国的外债大都以海关税收作保,“而我国政府于事前未尝一采列国之同意,而毅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行之,其勇气固可敬,而勇而无谋,则亦可惊也。吾至今犹未能知政府目的之何在”(19:73)。他认为这种孟浪举动,必召猜忌于强邻,若列强反弹,中国政府必然失败。但若要收回成命,则大损政府威信,所以梁提议六项主张(19:74-75,在此不细引),目的在于重新界定各国对中国海关的权限,希望因此能“稍挽此次之失体”,也希望能因而“庶可以减杀总税务司之势力,而盖朝廷谕旨无效之羞”(19:74)。梁所提议的六点是否可行,他自己也无把握,但若能行一两项,也可以因而稍自解嘲。此事后来的发展果然如梁所料:“此文撰成方付印,得最近电报,知各国干涉,已不幸不言中矣。”(19:76)
事实上各国的反应并不相同,即使干涉也未必如梁文中所隐含的那么严重。铁良和唐绍仪在这道谕旨颁布的第四天,才召见总税务司的关键人物赫德。赫德认为此谕的实质改变有限:“除了向外务部报告工作以外,还必须向他们(即新成立的税务处)汇报工作,或许在一些事情上,不向外务部而向他们汇报,但其他一如既往。”(陈诗启,1993:494)虽然海关内部与各国的反应强烈,但处于龙头地位的英国官方反应竟然如此平淡。
这道谕旨只是设置了两位税务大臣,并未设立新的财政机构,但政治意义却很明显:海关总税务司过去参与了中国和各国使节之间的往来与关系,也介入了中国向列强借款的事项;从今而后,总税务司只是中国税务处之下的机构,与外务部无涉,因而不得再干预外交事务。赫德的地位以及他和清廷的关系,自此急转直下。两年后,1908年4月税务处宣布设立税务学堂,培养本国的高级税务人员以取代洋员,追求海关自主。然而限于中英协议,以及英国对华贸易的重要性,所以海关总税务司仍由英人担任,对中国的政局还是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同年,梁另在《新民丛报》写了两篇文章(第85号与第86号,未收入文集内),析论中日改约的关税问题。1895年《马关条约》之后,中日双方协议:在约满十年之后,双方在六个月之内皆可提议修改条文。日本华商在1906年电请中国外务部提议改约,内容大致有三项议题:领事裁判权、最惠国待遇、国定关税税率。此三项中,领事裁判权牵涉甚广,非与日本所能分别议定;而国定税率问题,必然引起列强反对,非中国主观意志所能行。所以梁把目标放在较有谈判可能性的最惠国条款上。
最惠国条款的基本意义是:甲乙两国订约时,其中一国若与第三国丙另有定约,则所许予第三国丙之利益,甲乙两国亦应相互许与。
这种最惠国条款有相互的(双方明文签订),也有片面的(甲国许乙国,而乙国未明文许甲国)。梁列举中国与列强所订的条约中,与最惠国条款相关者,都是属于片面性的:中国许与他国之利益,诸国一体均沾,而列强之间互许之利益,则未明言中国是否适用。梁写此文的用意是:今届改约之期,可就此事提议力争,或许有成功的机会,因为“日本近今政策常刻意欲与我交欢,我若提此议而坚持焉,其必不以此区区者伤我,……此又可据情理而信之者也。故吾曰非漫无把握而云然也”(86:47)。
梁认为最惠国条款是中国政府所能争者,而所不能争者,是他在另一篇文章的主题:协定税率。海关税率大约可分两种类型,一是国定税率(由主国自定),二是协定税率(对甲国为甲种之协定,对乙国为乙种之协定)。此事起因于日本新颁税则,载明诸国之协定税则,但中国不在此列。中国驻日公使电请政府转告日本政府,请将税额改为各国一律,以示平等对待。
梁有几项主要理由反对此事。(1)他对比十二项货品的旧税和新税,大致说来新税比旧税最低增加了一倍,也有增四五倍者。这是与日本通商的各国所共苦,非专为苛征华商而设;若以此点要求日方必无效果,反易被认为中方对此问题理解不足。(2)日本实行这项国定税率,是几经血汗和欧美列强争议之后才获得,现在才刚要通体施行,必定不会因中国的抗议而改动,中方的抗议必然无效。(3)日本所课重税之物,有好几项是中国出口货的大宗,但课税对象是以商品为客体,而非特定针对某国。中国若抗议,日本可答曰此非专对贵国而设;这是暗亏,难以具体抗议。梁久居日本,尤其留意这些与外务相关的经济谈判,上述三项理由甚有见地。
以上两篇是属于时事评论性的短文,或许《饮冰室文集》的编者认为重要性不高而未收入。中日双方协议税率是一件具体的谈判事件,可申述之处不多,但最惠国条款则有再论述之处。现在有一些文献在研究晚清不平等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但立场上大多偏向谴责性的角度:片面的、无条件的、概括性的、滥用的、伤害性的。王国平(1997)从比较冷静均衡的观点,认为一般人认为清政府是不加抗争地就轻易让出最惠国待遇,这种全盘负面的观点并不符合事实,其实清政府的立场会因优惠内容的不同而异。一般说来,决策时较着重政治效果而轻忽经济效应,但这种经济上的伤害在程度上并不如印象中的严重。其次,中国和列强所订的条约中,并不完全是片面性的最惠国待遇,也有一些是双方互惠性的。这项题材在过去的研究中,时常流露出民族情绪,现在应该要冷静地重新审视个案,评估它们对中国的利益与伤害,在哪些事项上产生过哪些不同的冲击,才能得出较公允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