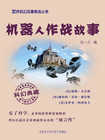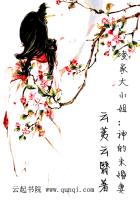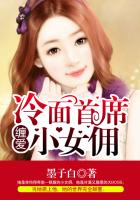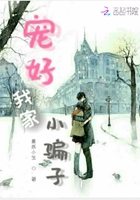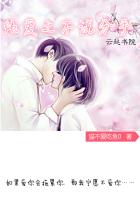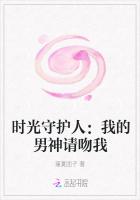弘治九年(1496年)十二月,刑部典吏徐珪[徐珪,幼从名师,聪颖过人。弘治六年(1493年)中贡士,同年,供职于刑部,执事于监狱。因为人刚直正派,不善夤缘,无后台可依,故一直为刑部八品典吏。其职位算起来,只不过乃衙门一胥吏而已,或相当于今日一看守所所长罢了],虽位卑职低却敢抱不平,他愤慨地在奏折中称:
袁璘咆哮公堂、出言不逊,理应处以杖刑,丁哲的处断非常清楚公正。
镇抚司与东厂共同蒙蔽事实,欺君罔上。
陛下令三法司、锦衣卫会审,可他们都惧怕东厂,不敢明言,以致审讯大堂众口一词,这都是他们事先已经串供所致。
满仓儿居然诬陷自己的亲生母亲,按罪当诛,而仅处以杖刑,丁哲等无罪反判其刑。轻重如此倒置,都是东厂胁迫所造成的,公理难容!
我在刑部三年,案中的“盗贼”,大多因东厂和锦衣卫镇抚司被抓,其中有东厂校尉挟私诬陷的,有东厂校尉为人报仇的,有东厂校尉收受首犯的贿赂而改为从犯另找旁人抵罪的。刑部的官员都知道这些,可谁敢擅自更改一个字呢?
天理昭昭,善恶必报!如此伤天害理,势必破坏天和,导致灾异频繁出现。
我希望陛下能够革去东厂,限制宦官的权力,废除弊政。处死杨鹏叔侄、贾校尉和他的干女儿贾芸,谪戍锦衣卫镇抚司官员到边疆。
对于刑部郎中丁哲、刑部员外郎王爵、御史陈玉、主事孔琦等人,应快快释放回到本部门,并各晋升一级,以洗清他们所受的冤枉,如果这样,上天才不会发怒,太平才得以保证。
如果不废除东厂,也应该推选谨厚的宦官如陈宽、韦泰等人管理东厂,且要派一个大臣与他们共同管理。
锦衣卫镇抚司理刑时不能只用锦衣卫的官员。我希望能够选在京各卫一二人,及刑部主事一人,共同审理案件。或三年或六年一个任期,如此处理,就可以避免巡捕官校作奸擅刑,诬陷无辜。
我本是一个身份低微的人,前后左右都是东厂和锦衣卫镇抚司的人,我的这次上奏必然会给我招来灾祸。与其死在东厂和锦衣卫的手中,不如死在朝廷的手中。希望能够斩下我的头颅,践行我的建议。然后把我的骸骨送还我的妻子儿女,让我回归应城,我虽死而无恨。
徐珪这一奏章,充满浩然正气和大无畏精神,字字铿锵,掷地有声,其气概感人动容,忠义可见。
然而,徐珪企图改变明朝宦官与内阁并行的权力双轨制,结果就是要改变明朝的君主专制,这无异于与虎谋皮,是绝对办不到的事。徐珪的掷地有声的建议,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朱祐樘对东厂宦官特务无限信任的态度。孝宗皇帝看完徐珪的奏疏,表面假装被他的忠义精神感动,认为这个案子事关江山社稷,应当查明真相;实则怒斥几个相关的臣子,然后将案子交给都察院审理。
都御史闵珪等抵赖说:“徐珪诬陷会审官员,他所说与事实不符。”
孝宗皇帝看了闵珪的奏章,听信了闵珪的话,也认为徐珪所奏与事实不符。
在孝宗看来,一个身份低微的徐珪竟然敢于参劾东厂、锦衣卫、三法司,讥贬满朝公卿,为此,他不由得勃然大怒,“小小的典吏竟然如此胆大包天,直言无忌!着都察院审判徐珪!”当即发交都察院,对徐珪进行严刑拷问。
执法官员们看到孝宗如此大怒,生怕丢了乌纱帽,当即息事宁人。虽然都御史等人都很惊叹徐珪的勇气,但又不敢得罪东厂的杨鹏、锦衣卫和三法司参审官员,就胡乱给徐珪加上“奏事不实”的罪名,疏请处以徒刑,但准循例赎刑。
有关官员见天威震怒,大事不妙,当即上疏认罪,结果被从轻发落,处以不同数额的罚俸。丁哲为民,王爵杖赎,而杨鹏等依然继续作恶。
徐珪办完赎刑手续后,被发回原籍为民。
徐珪削职为民后,朝中许多正义之士,纷纷为他鸣不平。
在刑部观政的进士孙磐,领先上疏,就徐珪上书揭发东厂遭到罢官一事上疏建言道:“现在的谏官,面对皇上,多是阿谀逢迎,不敢讲真话、说实情,更不敢上疏揭发权臣之奸。而今天,为皇上揭发宠幸、弹劾权贵的人,只是一个身份低微的刑部官员。对此,我们都深感羞愧,自叹不如!我看他在谏言中提到的臣子,不外分为四等:一等是不避祸害,敢于抗弹权贵的人;二等是敢于扬清激浊,能补阙拾遗的人;三等是能够就时政提建议,有益于军国的人。上述三类,都应当被擢升重用。而第四等则是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人,或者是那些不敢说真话的人,应当罢黜他们。圣上啊,兼听则明!现在,朝廷内外,议论朝政的人很多,应广泛听取。上述之言,我都是言之有据的,决不是信口空谈。希望圣上能够明察。”
然而,对于这一个含有珍贵的治国良策的奏折,孝宗皇帝看完,居然将奏章搁置一边,不闻不问,无一采纳。明代中期的厂、卫横行不法,司法黑暗、冤狱重重,明孝宗虽然主张励精图治,重视司法,慎重处理刑事案件,但从满仓儿一案看,仍然是东厂干扰司法,司法无法清明。明代的宦官专政,实质上是君主专制的反映。
从朱棣开始,宦官逐渐把持了政治、军事、刑侦以及经济方面的大权。文武官吏在明王朝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的只不过是配角而已。明朝的第一个贪残的大宦官是英宗朝的王振,其后又有同为英宗朝的曹吉祥以及宪宗朝的汪直,武宗朝的刘瑾等等。
有人可能会因此认为,宪宗和武宗之间的孝宗弘治时期,宦官的权势得到了控制,其实并非如此。
不可否认,朱祐樘即位之初,迫于形势曾经不得不惩治梁芳、韦兴、陈喜等宦官。同时弘治年间又有几个知书奉法的太监如怀恩、何文鼎等,但总的来说,宦官势焰熏灼、恣意贪残,与成化年间毫无二致。弘治初年,李文祥曾上书指出当时的情况是:“权移内侍而不在内阁。赏罚只根据宦官的喜怒,祸福也由他们摆布。他们仇视言官,公行贿赂。谁要是对其阿谀逢迎,则引为知己而得到超升。谁要是敢于揭他们的短,得罪他们,便会被暗中谗害并贬谪远方。这种颠倒是非的举措,真使臣僚们寒心,也使诸百姓慑于彼等淫威而不敢论说。”弘治年间宦官势焰熏灼的例证很多,本案就是一个。
《明史·王献臣传》说:“孝宗励精图治,信任阁臣,中官的势力稍微有所收敛。”这完全是根据表面现象得出的错误结论。朱祐樘与其列祖列宗一样,内心深处并不信任大臣,因而在官僚士大夫组成的官制之外,又竭力使宦官统治机构从中央到地方都完善并巩固起来,形成另一套操纵自如的统治系统。自然,一个稍有头脑和政治手腕的统治者,总要力求使官僚士大夫之间、宦官之间以及官僚士大夫与宦官之间既相互制约又能基本协调一致,这样才能使统治得以维持和巩固,否则就会出问题。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自永乐以后,明王朝愈来愈把宦官作为主要统治工具。朱祐樘也不例外。
弘治初年,对宦官偶有罢黜,这不过是玩弄政治权术,或者是宦官内部因权势的消长而倾轧的结果。实际上,当时谁要是敢于纠劾宦官,或者得罪宦官,必然遭到他们的打击陷害,而且宦官是不获全胜决不罢休。
弘治九年(1496年),满仓儿案件后,御史胡献曾上疏弹劾杨鹏等宦官借小事制造冤案,打击异己,并请求废除东厂。他在奏折中说:“东厂校尉,本来的职责是惩办奸恶之人,现在却成了宫中太监和外戚发泄私愤的工具。如御史武衢忤、寿宁侯、张鹤龄、太监杨鹏、主事毛广忤、太监韦泰,皆用鸡毛蒜皮的小事,夸大成罪。满朝文武都知道被判有罪之人是冤枉的,但无人敢说。我也知道,今天说了,他日必被他们陷害,然而我不怕。”奏疏送上以后,张鹤龄与韦泰各自上疏辩解。恰好此时给事中胡易奏劾监库内臣贺彬贪黩,贺彬也使用宦官们的一贯伎俩,诬告胡易。朱祐樘于是下令将献、易都关进诏狱。后来,谪胡献为蓝山(今属湖南永州)县丞,胡易被释放。
弘治十四年(1501年),内侍刘雄经过仪真,知县徐淮没有及时迎接,惹恼了刘雄。刘雄乃渡江诉于守备太监傅容,傅容上奏到孝宗皇帝朱祐樘那里,朱祐樘随即命令给徐淮戴上刑具抓捕到京师,交锦衣卫拷讯。六科十三道的言官们纷纷上疏请求赦免徐淮,朱祐樘都不允准。后来徐淮被执行杖刑,被调到了边远的地方。由此可见,朱祐樘非常袒护他的宦官。“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句话很适合于朱祐樘的所作所为及其身后所获得的赞颂。一般说来,为尊者讳,为长者讳,特别是对专制君主,尽可能地美化,而对其缺点错误则尽量回避或者进行辩护,这是很早以来就形成了的一种“合理”的做法。所以,即使是一个坏皇帝,也会获得美誉,史官会尽可能地对其加以赞颂,何况朱祐樘这样一个在明代诸帝中算是较好的皇帝,后人对他大加赞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过,如果谁要相信朱祐樘真的像史书上所赞颂的那样好,就难免要上当了。
总之,朱祐樘决不是将司法公正放在君权之上、雄才大略、大有作为之君,当然也不是荒淫的昏君,而是惯于玩弄政治手腕、力求维持朱家皇权统治的专制君主。
满仓儿案审定三个月以后,也就是弘治九年(1496年)十二月,与本案有关的官、民,被关在监狱中的还有三十八人。给事中庞泮再次上疏,请求予以处理。结果,刑部员外郎丁哲被判补偿袁家安葬费,罢官为民;刑部员外郎王爵、御史陈玉、主事孔琦被处杖刑,赎刑后官复原职;满仓儿被处杖刑后发交浣衣局执役。至于罪魁杨鹏叔侄、媒婆张媪、乐户张氏却依然被判无罪,逍遥法外。一场历时半年,经三法司两次会审的大案就此草率了结。
一年后,清宁宫发生火灾,刑部主事陈凤梧借机再次为徐珪鸣冤,希望能够让他官复原职,或者授予他其他官职以安慰他。孝宗这才同意下令授予徐珪正八品职衔。吏部接到孝宗的旨意后,授徐珪为浙江桐乡县丞。
一年后,大概为了平息官愤、民愤,杨鹏也被削职为民。
后经人举荐,徐珪历任浙江唐县署教事、福建罗源县知县、山东高唐州判、河北涿州同知、江西赣州通判、广西钦州知州等职,所到之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人称“徐青天”。徐珪虽然身份低微,却破例地登上青史之塔。《二十四史》之《明史》为他作传;《浙江通志》、《光绪应城志》等地方志书都载有他的事迹。
弘治十八年(1505年),孝宗皇帝病逝。其子朱厚照继位,帝号武宗,改元为正德。正德元年,徐珪于弘治九年(1496年)所谏言的“革东厂,限权宦官”的政见得到逐步的实现。这一年,曾紧随徐珪步伐的孙磐,再次上疏新帝,痛斥“内臣典兵”(即将宦官、锦衣卫派往军中监军)之弊端与罪行,遭司礼监掌印太监(宦官之首,与首辅大臣并列)刘瑾反击,身陷囹圄,险遭杀身之祸。正德二年(1507年),又因刘瑾专权,搜刮民财,致使河南及甘、陕、川等地农民不堪重负,聚集十数万之众,攻城破府,捉杀贪官,其势浩大,席卷中原大地,危及朱明王朝。武宗审时度势,派出五路重兵围剿,镇压了这次农民起义。后查证原由,皆为刘瑾专权所致。武宗大怒,旋将刘瑾打入天牢,并亲率锦衣卫,囚押刘瑾同去刘府,抄没家产。锦衣卫从刘瑾家中搜出了伪玺、穿宫牌以及衣甲、弓弩、玉带等违禁物品。此外,还有黄金二十四万余锭、元宝五百万余锭、宝石二斗。细心的士兵还从刘瑾常用的折扇中,发现两柄锋利无比的匕首。朱厚照勃然大怒,说:“你这狗奴才,果然想造反!”气急之下,照着刘瑾连挥数拳,并下令将他处以磔刑(凌迟极刑,俗称剐刑。剐刑,古代的一种割肉离骨的残酷死刑,把人的身体割成许多块,凌迟的俗称)。
刘瑾之事,对武宗震动很大,忧愤之情,在武宗心中久久难以平静。他辗转反思,深感父皇孝宗之内官近臣,十有八九犯有贪赃枉法之罪,而那些逆耳谏言之臣,反多廉洁勤政,言行一致,深受百姓爱戴。因此,他认为先帝确有识人之误,用人之失,忠奸不辨,招致民枯财尽,国运气衰!
家贫念孝子,国难思忠臣,武宗在闭门思过之时,再次翻阅徐珪昔时之奏章,又被其情所动、其理所服。他连连点头,赞叹不绝:“徐珪忠肝义胆,乃大明一大忠臣义士也!”因此他决定采纳徐珪之谏言:撤销东西两厂、限权宦官不准干预朝政。同时,平反了丁哲、孙磐等数以千计之冤案,改革了自洪武以来一百四十七年之弊政,实现了以徐珪、孙磐为代表的忠义官员的意愿,大快人心!
后世在撰写明史时,破例地将徐珪这一胥吏微臣与孙磐合并作传,刊入明史列卷189卷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