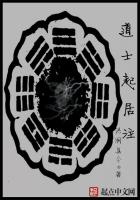三姐的老父吴养醇自送走张家伙计张四后,心中也十分不安,不知女婿一个活生生的人怎么失踪了。他一则怕女儿忧虑伤身,二则也惦记女婿,便派义子吴周到亲家公张乐那里走一趟,打听隽生下落,顺便探望女儿三姐。
张乐又加派人马,四处去寻找,仍然没有寻着隽生的踪影。张乐心中越来越担心,“这畜生没去探病,满大街也不见踪影,定是与那班狐朋狗友寻乐子去了。这还了得!快随我再去寻找!”恰好遇到张隽生一个姓高的朋友,说:“几日前见他走近城门。他说‘到丈人家中去’,以后便不曾相见。”
张乐带着伙计到酒楼茶肆和风月场中又寻找了一番,都不曾见着隽生的踪影。晌午过后,张乐一脸怒色回到家来,敲桌拍案,怪家人伙计们平日惯坏了孩子。家人伙计们心中暗想,这不都是您老人家带坏的吗?怎么怪起了我们?
三姐越想越伤心,悄悄回到屋内,暗中怪自己苦命,又不知眼下的事将会如何收场。
着急上火的张乐正思虑是否报官,家人进来报告说三姐娘家派她的义弟吴周前来探望。
那吴周因是来姐夫家做客,也不拘礼,直接闯入家中,与迎上来的三姐叙话。
三姐一见娘家弟弟来到,心头一热,竟落下两行清泪。
吴周连忙“姐姐,姐姐”地叫着,去给三姐拭泪。
恰在此时,被迎出来的张乐撞个正着。
张乐正为找不到儿子焦心,却不料进来一个模样英俊、文质彬彬的后生,进门来就与三姐搂搂抱抱,甚是亲密。再看那吴周,生得仪表堂堂,眉清目秀,齿白唇红,高高的个头儿,风流倜傥,潇洒儒雅,稳重大度,竟比隽生强了几分。又见三姐突然没了悲戚状,与那后生十分亲热,张乐内心十分不快。
三姐慌忙收了泪水,将吴周介绍与公爹张乐认识。彼此见过礼后,三姐道:“这是孩儿的义弟,父亲派他前来探问隽生下落。”
吴周前来,本是亲家间的一种正常的关怀,哪知张乐经过一番胡思乱想,陷入了种种怀疑之中。张乐见吴周风流倜傥,与三姐极为亲近,三姐在吴周身边也显出一种亲昵情态,而这种情态以往他张乐从未见到过。于是,最初极为含混的猜想仿佛一下子有了比较清晰的轮廓:莫非这对姐弟之间早有暧昧之情不成?莫非是他们合谋将隽生杀害,又前来刺探情况不成?张乐一面思忖,一面将吴周让进客厅,自家坐了上首,吴周落座右首西宾席上,三姐则坐到吴周的右边。
依张家惯例,凡是待客,一等落座,即命家人奉茶。今日不然,张乐见三姐竟也陪坐下来,心里生出一股无明火,便瞪着三姐,“三姐,前去备茶吧。”
三姐刚要起身,吴周道:“自家人,不必客气。”
三姐见公公没有收回成命之意,仍是离了座,道:“姐姐去去就来。”说着便走开了。
吴周朝张乐一拱手问道:“亲家叔父,不知姐夫如今可有下落?”
张乐道:“我带人寻遍了全城的茶楼曲馆和热闹去处,探访了这个畜生的所有朋友,俱寻不见踪影,好生蹊跷。”
吴周此前已从他人口中得知隽生不时去勾栏瓦舍厮混,所以,他便试探着问道:“亲家叔父,小侄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张乐道:“贤侄但讲无妨。”
吴周道:“不知可曾去青楼问过。”为不致让张乐显得尴尬,他又解释道:“那种地方,后生吾辈一时好奇,偶一为之也并非不可能的。”
这句话,非但没能说动张乐,反而印证了张乐心中的猜疑:果然这后生不是良善之辈,将那大伤风化的丑行说得如此轻巧。心中有数之后,张乐说话便强硬起来:“看来,尔等都是见过笑馆世面的了?可我隽生儿再不才,也不致沦落到花钱买笑的地步……”张乐说着违心话,极力掩饰儿子的陋行,同时为吴周当前讲出这样的建议怒火中烧。
张乐正想发作,三姐将茶端了上来,先给张乐敬奉一盏,然后又给吴周奉上。
吴周见张乐火气冲天,正自心慌,见三姐献茶,忙用双手去接,慌乱中碰翻了茶盅,洒了一身茶水。三姐见状,忙掏出手帕为吴周揩擦。
吴周抢过手帕道:“我自己来吧,姐姐歇着。”不想那一盏茶水一滴未少地全都洒在身上,洇湿了一大片,任是如何也抹不干净。
三姐道:“弟弟,不如将外衣脱下来,我拿去晒一晒,很快会干的。”
当着张乐面,吴周有些不想脱。
三姐怕洇到内衣,便主动上来替他脱掉,嘴里还说着:“一家人,如何就见外起来了?”
及至脱下外衣,见吴周手腕上包着药布,忙问:“弟弟的手腕受伤了?”
“那天逗咱家那只猫,不想逗急了,被它用爪挠破了点皮,不碍事。”说着,吴周有些腼腆地笑了。
三姐与吴周的亲昵,吴周腕上的伤,以及他对逛妓院的轻率看法,在张乐心中逐渐串成一条线。张乐觉得血气直往头上涌,心突突地跳个不停,他心中的猜测似乎成了事实:肯定是这两个禽兽不如的男女早已通奸,合谋害死自己儿子,吴周手腕的伤即是自己儿子挣扎时将他抓挠所致。
“吴周,你这厮听着!”张乐突然一声吼叫,“我且问你,你是如何将隽生杀害的,尸首埋藏在哪里?”
突然的诘问直惊得吴周瞠目结舌,半晌才缓过神来,“您说什么?侄儿不懂。”
三姐惊讶过后跑过来道:“爹爹是怎么了,气糊涂了吧?”
张乐一巴掌把三姐打到一边,骂道:“好你个娼妇,不守妇道,什么姐弟,你二人分明早就有奸,勾结将我儿害了,好腾了你们的眼宽。待我将这恶徒送到县衙,回头再与你算账!”
“亲家叔您,您这是说哪儿的话呀?我来这里是受我爹我娘嘱托来探听姐夫隽生的下落,顺便看望您二老和我姐姐的,弟弟跟姐姐怎么会有那种事情?您误会了,误会了……”吴周辩白说。
“什么姐姐弟弟,你们是一个爹娘生的吗?别拿姐姐弟弟的话掩人耳目了。我问你,你们杀害隽生,把隽生的尸体藏到什么地方去了?说!快说!”
“姐夫跟我姐姐结婚,除了婚礼上和三天回门时我见过姐夫两面,再没见过,我怎么会知道姐夫到什么地方去了?”
“少废话,快把我儿子的尸体交出来!”
“这……一点影子也没有的事,我怎么会知道?我……”吴周满身是嘴也说不清。
三姐有口难辩,顿时没了主意,号啕大哭不止。
家人伙计也都惊呆了,齐声呼唤:“老爷,老爷!”似乎要提醒他言语太离谱了。
吴周稍定片刻,醒过神来,问张乐:“你道我杀害姐夫,道理何在?证据何在?”
张乐道:“你与三姐眉来眼去,频传秋波,这等情形岂能瞒过我的眼?还要什么证据,这大活人没了就是证据,你手腕上的伤就是证据,你这次来打探动静就是证据!来人,快与我将这奸夫淫妇扭送县衙,有什么话到公堂上去讲!”张乐说完,不由分说,拽住吴周衣领就走。
到了这般时候,辩解也没有什么用了,吴周、三姐只好硬着头皮随同张乐及家人伙计等人往县衙见官。
一路之上,围观的人越聚越多,吴周与三姐直羞得无地自容,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一行人撕扯着来至县衙,张乐命家人看住吴周与三姐,休放跑了,自己登上台阶,用力擂起堂鼓来。一通鼓响过,招来了不少县衙附近的人,加上尾随跟来看热闹的人,直把县衙围得水泄不通。
扬州知县孙起向来刚愎自用,常以青天自居,时不时会闹出草菅人命的事。他听得堂鼓,急忙穿戴整齐,身着官服,喊齐衙役,一声“升堂”喝过,三班役吏排列两厢。
喊过堂威,孙县令问值日的差役:“何人击鼓?传上堂来。”
张乐到得堂上,跪倒在地,磕头如捣蒜,连呼:“青天大老爷为小民做主!”
孙县令见堂下跪着一个老头儿,便问道:“堂下何人,姓甚名谁,谁是原告,谁是被告,有什么冤情?详细说来,老爷我自有主张。”
张乐磕个头诉道:“回大老爷话,老儿名叫张乐,宜和茶庄掌柜,扬州城里人氏。老儿只生一子,名唤隽生,半个多月前娶城外吴养醇之女三姐为妻。谁知三姐不守妇道,早与其义弟吴周有私,只是瞒了老儿一家。几日前,三姐声言我儿隽生去探望岳父母,可老儿派人前去探问,那吴养醇竟一口否认隽生到过他家。实是吴养醇见其继子吴周与三姐私情有露,将我儿隽生骗至无人处杀害了。”张乐先将自己的猜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说完,竟呜呜地哭起来。看那样子,并非装腔作势,而是真哭。最后,张乐道:“都道孙大人断案如神,执法如山,恳请大人为小民做主,为我儿报仇,小民将没齿不忘大人的恩德。”
孙县令听完张乐的诉告及赞扬,颇觉顺耳。他暗自思忖:张乐是城内知名富商,一向奉公守法,如果不是真有其事,断不会撕破脸面,抛却名声,前来状告儿媳与娘家弟弟,便命传吴周与三姐上堂。
吴周、三姐二人跪拜过孙县令,屏息等待孙县令审问。
孙县令命二人抬起头来,二人遵命将头直面县令。孙县令见二人都生得俊美清秀,气质朗丽,若不是前来打官司,真可谓郎才女貌,天生的一对标致夫妻。于是孙县令连连点头,似乎心里有底了。他心想,连自己这样富有经验、历世深厚的人都会产生这样的感觉,他们之间发生奸情是再可能不过的了。
孙县令见吴三姐长得确实漂亮,有这样的美色,谁人见了会不动心?于是就想先从三姐这里突破,他厉声喝问吴三姐:“你跟吴周是如何勾搭成奸的?又是如何一起谋杀你丈夫张隽生的?说!”
“大人这话从何说起?我怎么不明白呢?”吴三姐茫然反问孙县令。
“你公公告你跟弟弟吴周通奸,合谋杀害亲夫,怎么还装迷糊呢?!”
“吴周是我弟弟,我是他姐姐,姐弟之间怎么会有那种事情?”
“什么姐弟?分明是奸夫淫妇,快说,你们把张隽生的尸体藏到什么地方去了?”
“没有的事情,大人让我说什么呀?”
“那我问你,张隽生是你丈夫,失踪了八日又找不到,你丈夫现在哪里?你从实说来,不得隐瞒。”
三姐未曾开言,先已垂泪,呜咽半晌道:“自民妇嫁到张家,夫妻俩恩恩爱爱,和睦度日。只因那日民妇思念娘家父母,说与夫君,夫君慨然允诺前去探望。是民妇亲自将夫君送上路的,谁料一去竟杳无音信。公公派人这儿问,那儿找,都说没有见我夫君,这事,别说公公着急上火,我心里也着急呀。民妇自幼遵从父训,恪守妇道,决无苟且之事,还望大老爷明断!”
孙县令见三姐没有招认,就转向吴周:“吴周,张乐告你因奸害命,匿尸灭迹,可有此事?从实招来!”
吴周连呼:“大人,这是天大的冤枉!三姐是我姐姐,我怎么会跟姐姐通奸呢?小人被义父吴养醇收为义子,与三姐情同亲姐弟,绝不会做此禽兽不齿的苟且之事。至于杀害姐夫,更是子虚乌有。我跟我姐夫半月多没见过面,怎么会杀害他呢?至于尸体,就更不知道了。亲家叔父的加罪,全凭臆想,毫无根据。姐夫失踪,事出奇特,失子之情,人可体谅,应下力寻找,而不必横生枝蔓才是。望大人明察,妥善处理,则小人有幸,合家有幸。”
吴周这一番话讲得很得体,既合情理,又无怨言,说得孙县令也踌躇转身问张乐有何话讲。
那张乐天生犟种,从不肯认错,何况儿子失踪,人命关天,于是,重新跪下,磕头至地,道:“那吴周面似和善,实极狡诈,大人不可为他的言语所惑。小人告他,自有道理,愿与这厮当堂对质,乞大人允准。”
孙县令道:“本县准你当堂对质。”
张乐问吴周道:“我问你,你道隽生可能到勾栏瓦舍厮混,且说后生之辈一时新奇偶然去去那种卖笑场所乃情理之中的事,这话可曾说过?”
“说过。不过我是说可能,却未曾说我去过。当时,我不过是想给你和姐夫一个面子。”
“大人,我的儿子隽生自小受名师教诲,又有我时常督训,一向知书达理,视那种勾当为大逆不道,这是尽人皆知的,如何会因所谓新奇而做苟且之事呢?吴周之言,分明道出了他的意念和境界,足见他是个不逞之徒。”说罢,又转向吴周,“我再问你,你手腕的伤究竟怎么回事?”
“大人,小人手腕是被猫抓伤的,与杀人毫无干系。”
“我再问你,你那外衣为什么与我儿所穿的一样,究竟是怎么来的?衣袖上的血迹是怎么回事?”
“血是猫抓破后染上的。至于衣服一样……”这一点吴周万没想到,他也不知道是否一样,一时语塞起来。
张乐见状,逼进一步,“你解释呀!”
孙县令听张乐这一番盘问,又倾向到张乐这边,遂将惊堂木一拍,“吴周,你从实招来!”
吴周道:“大人容禀,这件外衣是姐姐为我缝制的,小人并不知我与姐夫隽生穿的是否一样。”
张乐见机马上咬住,“我儿那天去你家,便穿着这件外衣,如何现在穿到了你的身上?”
三姐大声道:“大人,我弟弟这件衣服原是爹爹从苏州买回的绸料,我为弟弟缝制了一件。因质料花色俱都上眼,做出的衣服耐看,故将余下的绸料为夫君也缝制了一件。这两件乍看相近,尺寸却不相同。”
孙县令大声喝道:“张隽生已失踪,即或做了两件,又如何相比尺寸?我看血迹、衣服绝非巧合,吴周,你还敢强辩!快快将实情招出,免得皮肉受苦!”
吴周忙道:“大人如此草率,难以服人。”
孙县令道:“我问你,张隽生离家出走的这几天你都在哪里?做些什么?!”
“前两天家父病重,小人除买药外,一直守在家中伺候老人家。”
“第三天呢?”
“家母念小人那几日过于劳累,加之家父病已好转,教小人出去散散心。”
“你去了哪里?”
“扬州北郊的天宁寺。那里曾是晋太傅谢安的别墅,后改为谢司空寺,佛陀跋陀罗曾在那里译《华严经》。天宁寺环境清幽、风物宜人,小人闲时总爱去天宁寺盘桓。”
“第四天呢?”
“第四天在家,下午见到亲家叔父派来的家人张四,才得知姐夫失踪。我父亲担心姐夫,我于今日一大早就遵父命起程赶往姐姐家,今日下午才到的。”
“你的腕伤在哪日?”
“出游那日。”
“你进城探听消息,是先见三姐,还是先见张乐?”
“先见到姐姐。”
“都说了些什么,又做了些什么?”
“只问了姐夫有无下落,便同姐姐一起见了迎出来的亲家叔父。”
“好,你且站过一厢,速去传吴养醇夫妇。”县令吩咐将张乐与吴周、三姐分别拘押。
围观群众都称这个案子离奇,迟迟不肯散去,但等吴养醇夫妇来到,再看会是什么结果。
吴周与三姐被带到一间值更的小屋,堂役将房门上锁后退去。吴周见四周无人,便问三姐:“事情如何变成这个样子?”
三姐反问吴周:“你道该如何是好?”
“看来有理不让讲,也讲不清了。眼前最要紧的是找到姐夫,一切自然明白。你看他现在会在哪里?”吴周希望三姐能提供些张隽生下落的线索。
三姐说道:“八成是在勾栏院馆里贪欢。”
吴周问:“你的推测有多大把握?”
“我也说不准。姐姐日里深居简出,很少与人来往,偶或听到家里的下人私下议论以前隽生常去那里贪欢。”
吴周道:“为弟之所以在堂上回避此事,为的是顾及张家颜面,想平和了结误会。谁知亲家叔父却将我们往死处逼,既然是这样,我只有在大堂上直接讲出来。只有如此,真相才可大白于天下,还你我清白。”
三姐犹豫道:“要说隽生去了春市,并无实在的证据,人家不相信,我们该怎么办?”
正在二人困惑之时,只听脚步声响,衙役前来提他们二人过堂。
事实上,那孙县令是有意设了这一个让吴周和吴三姐二人独处的机会,他让书吏在隐蔽处窃听,以便抓到些证据。待二人对言至此,县令以为真相已定,便吩咐升堂。
此时,吴养醇夫妇也被传到。
吴三姐、吴周一见父母来到,泪如泉涌,一家人抱头痛哭,一时间衙堂里哭声一片。
孙县令呵斥道:“哭什么?你们合谋杀害张隽生,现在哭也晚了!”
孙县令又向吴养醇道:“吴养醇,你女婿张隽生可到过你家?”
吴养醇答道:“不曾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