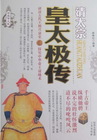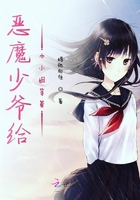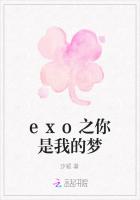对邓宝珊不接受馈赠之事,参与办案的帮办和一些随从,竟在私下啧啧烦言,表示不满,认为邓宝珊标新立异。邓得悉后十分生气,立即召集全体人员讲话。他说:“我们是本地方人,藏族民众发生这样的事是不幸的,我们一定要处理好。决不能收人家一文钱,一只羊。”为了照顾随行人员的情绪,邓除批评外,又指示从公杂费中开支买了十几只羊,犒劳部下。对惯于官场世故、自私短识的两位帮办,邓特与之个别谈话,严厉批评:“我们看到藏族人民的艰苦、贫困,应有同情之心,还忍心向他们勒索?”邓宝珊主张解决民族纠纷,唯有平等、公正一途;只有诚恳对待,才能在各民族之间建立真诚信任的感情。这种慧眼卓识在当时的确是难能可贵的,至今一些甘南藏族老人忆及此事,犹称赞不已。
最后,在各部落头人临别时,邓宝珊分别等级,以省府名义赏给银质奖牌,以及马缌、砖茶、糖、绸缎等。对于保护地方及有勋劳的头人,如陌务部落的红布公布才旦等,另给馈赠,以资勉励。受奖头人感到无比荣耀,满心欢喜而归。行前,邓宝珊又备了酒席宴请各位头人,双岔、西仓的头人、土官也均应邀出席。宴会气氛热烈、感情融洽,冤家变成了朋友。
本案处理结束,邓宝珊仍往黑错,认真处理善后事宜。一时不能收尾的工作,逐一交给黄正清、邓隆办理。在广征各方人士对此案处理之意见后,稍事休整,于1935年1月3日登程返回省垣。过岷县时,训诫鲁大昌不要自行扩兵,更不能向防区民众摊派粮秣、饷糈。鲁的新编第十四师,名义上是新一军编制,但鲁大昌割据自为,从不听邓的话。朱绍良为便于驾驭,放任鲁之行为,该师军饷不通过新一军拨发。这次值鲁大昌插手藏区事端,支持械斗之一方,酿成大乱,自己也受了损失,理亏气沮,又慑于邓宝珊的威望,只好诺诺称是,事后也有所收敛。
1月13日,行抵临洮,新编第十四师团长任谦通过王新令向邓宝珊反映,国民党当局要在临洮修建一个长2000米、宽600米的飞机场,已征得地方缙绅意见,场址选在临洮县城郊东山根。这里有几千亩良田,其中还包括一些学田,老百姓坚决反对。一些开明人士为了保住良田主张飞机场址选在县城外的河西滩上,则仅损坏几家豪绅的水磨坊。然而,这些豪绅却不答应。邓宝珊回到兰州后,立即向朱绍良说明了这些情况,并坚决主张将飞机场改建在河西滩。临洮人民因此称赞邓关心民瘼的德意。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处理类似双岔事件的纠纷,由于办案人员偏袒一方,无不留下隐患。邓宝珊这次甘南之行主持公道,促进团结,废除旧规陋习,减轻人民负担,制止了部落间冲突。对藏、回、汉民族隔阂,也有所弥合。当年夏秋,双岔土官、西仓头目、赛赤佛先后来兰,亲向邓宝珊表示感谢。1984年,藏族爱国人士黄正清为了纪念邓宝珊,著文盛赞邓在藏族人民心目中树立了“公正廉明的楷模”。
西安事变后襄助杨虎城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行径日益猖獗,民族危机越来越严重,每一个爱国者都在为国家和民族的存亡忧心忡忡。邓宝珊此时的心情,从他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鸿山先生道席:
顷接挺俯来函并附先生致于院长、杨主席两稿,拜读之余,且佩且奋,慨自暴日侵陵,华北摇动,覆亡之祸即在日前。而环顾国中民气消沉,人心散涣,瞻念前途,痛心疾首。先生以关中儒宗,古稀高年,奋进疾呼,亲赴国难。义声所播,无不闻风兴起。宝珊分属军人,为国效命,义所当然。只以饷械两绌,兵力有限,刻正简练部伍,并会同各方,募款购械,以俟稍能应敌,即当躬与抗战。比闻高风,盖足壮我声气。惟先生高年硕德,似应暂在后方计划一切。至于冲锋陷阵,躬冒矢石,尚有壮年后进,望先生指授方略足矣,似不宜亲赴前方也。不知高明以为然否。专此,敬颂
道祺
晚邓宝珊拜启
他十分关注国际形势和日本对华侵略的动向,1934年5月,在一次讲话中说:“最近国际间的情形,据报纸所载,最重要的就是国联谋与我技术合作,而日本极力反对,即诉诸武力亦所不惜,以致惹起英美各强国联合制日的趋势,世界各报纸群相攻击,甚或书面质问。日本以众怒难犯,即假词将有吉调回,同时把原定的焦土政策,变为以飞机轰炸的铁鸟政策。现在因畏怯欧美各国之攻击及我国之积极抵抗,又转变为水鸟政策,就是变刚硬的策略为柔软的方针,集中全日本的外交人才,对欧美各国施其造谣煽惑手段,竭力破坏中国。在各国因为不明了中国国情的关系,当然有受其愚弄的。如萨尔尼多小国竟然宣布承认‘满洲国’,现在日本对华北的侵略表面上似趋向缓和,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丝毫放松,像派员测量地图、调查物产等等,仍旧秘密进行,而最近又在台湾召开对岸会议,对华北、华南同时压迫。”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邓宝珊十分赞同中共中央“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主张,曾奔赴晋、冀、鲁三省,会晤了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敦促他们同仇敌忾,抗击日寇。同年10月,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为了争取东北军、西北军共同抗日,11月间,毛泽东派汪锋持他分别写给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的信到西安进行联络工作。可惜邓宝珊当时不在西安,未能见面。后来当邓从杜斌丞处知道这一消息,曾准备亲自往西安见汪锋,因汪锋已回瓦窑堡,终未实现。
12月26日,新一军中将总参议、邓宝珊“华山聚义”时结识的挚友续范亭,因痛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决心以一死唤起国人,实现全民抗战,前往南京,剖腹中山陵前,幸为人及早发现救治。续范亭是11月初离开兰州,来到南京的。一月多来,奔走国事。在此期间,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续范亭对五全大会抱有希望,希望国民党政府能做出坚决抗战的决策,但是,会议的结果令他十分失望,五全大会并没有做出任何像样的决定,续范亭的希望彻底破灭了。12月9日至16日,北平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学生爱国示威运动,得到全国各地人民的热烈响应和声援,这使失望中的续范亭仿佛又看到了某种希望。为了唤醒国人的爱国意识,抗议蒋介石“消极御外,积极内战”的反动举措,他故有此切腹明志之举。事前,他写有“绝命诗”五首和《敦促抗日绝命书》。其诗第一首云:“赤膊条条任去留,丈夫于世何所求?窃恐民气摧残尽,愿将身躯易自由。”邓宝珊在兰州闻讯,立电慰问:“于院长尊密请转范亭兄:接友琴梦九电,惊悉吾兄忧国至深,愤而自刺,闻之实觉不安。除兑洋五百元暂作医药费外,报国之日方长,尚希旷观静摄,特电示慰。弟宝珊叩俭。”同时,派出代表携款去南京慰问,协助抢救。续范亭伤愈出院后,杨虎城、邓宝珊又和国民军时期的一些老朋友,共同捐助了一笔钱,资助续范亭去杭州疗养了一段时间,续范亭当时拒绝了蒋介石的巨额赠款,但对老朋友的馈赠则欣然接受。1936年,杨虎城、邓宝珊等又接续范亭到西安。
同年,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部队,同蒋介石集团的矛盾日益尖锐: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与他们的爱国思想格格不入;蒋介石驱使他们的部队“剿共”,又使之面临着被红军打垮的可能。在全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情绪的影响下和中共中央团结抗日号召的感召下,张、杨二将军认识到内战不能继续,只有和中共联合一致抗日,才是一个爱国者的唯一出路。
11月下旬,张学良、杨虎城在甘肃平凉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密筹谏蒋之策。参加的有张的心腹将领王以哲、于学忠、高福元、张君尧等。于学忠时为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军长兼甘肃省主席(朱绍良因与张学良不睦,蒋介石暂去其省主席职,专任甘肃绥靖公署主任)。几天后,张学良亲至兰州与于学忠密谈。12月10日,张、杨多次劝谏蒋介石失败,决定对蒋实行“兵谏”。张学良电召于学忠到西安,参加了11日召开的东北军高级将领会议。杨虎城也出席了会议。与会者在八项抗日爱国主张上联合署名。第二天凌晨,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当晚7时,驻兰州的于学忠部队奉张学良命令,将驻兰州的胡宗南部队、甘肃绥署特务营,以及省会警察局解除了武装。扣押了军统特务头子史铭、绥靖参谋长章亮琛等人,公布张、杨八项主张,响应和支持西安事变。
张学良、杨虎城“兵谏”之举,事出突然,而且十分秘密,远在兰州的邓宝珊未能与谋。但事变前邓曾几度赴内地途经西安,与张、杨晤谈,深知他们厌倦内战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