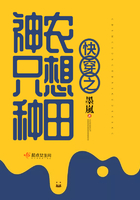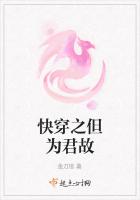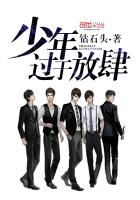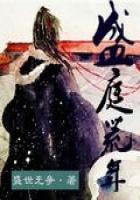由于邓宝珊政治上开明,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在新一军中活动受到保护。在邓部工作的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接受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以后逐渐走上革命道路的不乏其例。杜汉三曾任邓的教导队队长,后任新十旅第一团团长,驻在定西。1937年5月,中共中央派彭加伦到兰州筹设办事处,杜留住了九天。杜思想进步,十分拥护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请彭加伦每天给该团连以上干部作时事和抗日形势的报告。杜汉三又亲自陪彭到兰州,帮助彭寻找办公地址。后来他又主动找中共中央代表谢觉哉谈心,通过谢邀请雷鸣、黄俊耀等到他的团部当政治指导员和剧团团长。此外还让官兵大量加入抗日民族先锋队。他让士兵把大幅拥护共产党抗日和国共合作的标语贴到定西的大街通衢,团部礼堂也悬挂起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画像。在邓宝珊赴榆林后,杜汉三团仍留驻定西。朱绍良因此下令停止对该团的供给,并强行撤换了杜的团长职务。杜汉三因此长期“赋闲”在家。他暗中参加革命活动,1947年经葛曼(葛霁云子)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前夕在党的领导下参与组建了“西北前进同盟策动委员会”,密谋在陕西渭南地区发动武装起义,事泄后在西安被捕,于解放前夕惨遭杀害。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北上抗日,经甘肃进入陕北根据地。红军到达四川后,蒋介石严令驻甘的嫡系和杂牌部队全力堵截红军。惟独邓宝珊持消极态度。
这年夏天,红二十五军团徐海东部由川、陕、甘边境向陕北迸发。驻静宁、会宁、隆德等县的新十一旅,在邓宝珊授意下放弃庄浪,集中于静、会、隆三个县城。红军由静宁城外绕过,守军亦未出击。驻隆德的一个骑兵连,与红军一经接触,就撤回了城内,红军攻占县城数小时后东撤。同年9月,中央红军由岷县进入甘肃中部,国民党军抵抗无力,红军突破固原——平凉一线封锁,从环县、华池进入陕北。这次,在新一军防区也没有与红军发生战斗。
1936年夏,工农红军二、四方面军入甘,朱绍良要邓宝珊亲到定西督师,以其新一军的两个旅在定西、靖远、会宁一线堵截红军。8月,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派赵树雄到兰州会见邓宝珊,做和他建立统一战线的工作。赵树雄到兰后,在邓宝珊公寓详细转达了徐向前等领导的意图和信件。邓宝珊将军当即表示:国难当头,我中华民众应竭尽全力同仇敌忾,驱除敌寇。并表示红军如通过西兰大道,他决不做戕杀自己同胞的祸首。临行,邓宝珊取出一件狐皮大氅,让他转交徐向前。不料,赵树雄出邓公馆的行迹,引起了特务的严密监视。邓宝珊又让秘书驾小车将他送往洮沙。他回陇西后,向徐向前等汇报了接头送信的情况,受到徐向前总指挥的赞扬。当时,新十旅第一团驻在马营镇,该团在华家岭的骑兵连,一见红军就撤退,中途曾与红军遭遇,接火即撤。后来该团全部撤回定西城。在会宁会师的红军,曾派出侧翼掩护部队,攻占了定西东山一带部分阵地。新十旅第一团三营营长李彦和轻举妄动,自己率部出击,被红军击退。第二天,邓宝珊由兰州抵定西,下令固守阵地,不准出击。红军方面并不打算进攻定西,双方互不相犯。红军完成侧翼掩护任务后便撤走了。
新十旅第二团随旅部驻靖远,集结于县城内。9月上旬红军到达岷县后,该团团长王五田奉朱绍良指令,领第二营进驻城南70里的红堡子,以便与驻会宁西区的新十一旅互为策应。10月11日,红军徐向前部突然北进,王五田立即撤退,黄昏时行抵小路子,与红军遭遇。红军放出信号弹,吓得该团官兵慌忙溃退,王五田与营长李万福也随队逃走。王在乡里隐藏十余天,未敢回城。李万福逃回靖远城内,旅长李贵清下令紧闭城门。红军亦未攻城。直至红军过了黄河七天后,乡民进城购物,李贵清方知红军已去,遂派兵四出侦察,并向朱绍良虚报战绩说:“曾与过境红军,作了殊死战斗。”
新十一旅驻会宁城有两个连,10月2日晨被红军先头部队缴械,然后以军乐鼓号把两个连长礼送出城。朱绍良闻讯大怒,电令该旅旅长刘宝堂“立即收复会宁,否则即派飞机轰炸该旅”。刘被迫集结该旅驻定西以东的部队,反攻会宁。到达城下时,正值中午12时,第一团中校团副张锡轩,站在一高地上观察城内情况,立被城上红军击毙。遂围城准备夜间攻击,突然接到邓宝珊由定西转来朱绍良的命令,称红军将会师会宁,大军云集,着该旅立即撤退,于拂晓前退守定西清凉山。这一行动实际上是邓宝珊作用于朱绍良后实现的。原来,上年红二十五军团过境时,新十一旅未主动出击,朱绍良深为衔恨,这次决定让它与红军拼一下,胜了自己可以邀功,败了也乘机牺牲这个旅,削弱邓的实力。邓宝珊闻讯,赶去对朱说:“共军此次由南、北两面会集会宁,兵势之强胜于往昔,我们和他们打起来,将是一场恶战,牺牲一个旅有什么用,还是把它撤下来吧!”朱碍于情面,才勉强下了撤退令。这支队伍走到西巩驿时,又接到飞机以沙袋投下的字条说:“附近山头,已被红军占领,希立即撤出。”该旅便在飞机掩护下撤下山,退到定西东山。同年10月下旬,红军分别向陕北、靖远进发。新十一旅奉命尾随,实际上并无接触。一部由一团团长陈国宾率领,尾随红军到靖远,眼看着红军渡河而去;一部由旅长刘宝堂率领,跟在红军之后到达陕甘边境,便返防静宁一带了。
维护民族团结的楷模
邓宝珊在甘肃期间,一直兼任省政府委员。他于1934年负责处理甘南双岔事件的经过,反映了他尊重少数民族,注意调查研究,晓以大义、秉公断案的作风,在甘肃各族人民中留下了一段维护民族团结的佳话。
民族问题在甘肃历来是一个重大而又敏感的问题。清代和民国时期甘肃历任文武官员能妥善处理这类问题的,可说是凤毛麟角。生长在西北、深谙地方民情而又笃信孙中山“五族共和”思想的邓宝珊,在这一问题上表现了与国民党统治时期一般军政界人物迥异的特点。在当时条件下,作为一个汉族军政官员在处理民族问题时,最重要的是:一要交好上层,二要谨慎、公正地处理民族之间或民族内部的争执。邓宝珊到甘肃后,凡遇到有关民族之间的争端总是注意分清是非,支持受损害的一方。1933年下半年,国民政府行政院决议要把甘南夏河地区划归青海省辖。这一消息使甘南藏族群众和民族上层十分震惊。该地区原先饱受青海马麒家族的残酷统治和无情掠夺,经过斗争,才于1928年初由拉卜楞设治局改为夏河县,从马麒所辖西宁道划归兰山道管辖。国民政府行政院的决议意味着这一地区将重新为“青马”所统辖。当地藏族上层领袖人物、拉卜楞寺活佛嘉木样五世之兄黄正清,听到消息后立即打电报给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和蒙藏委员会,要求改变决定,继往兰州向甘肃绥靖主任兼省主席朱绍良面争。在兰州,黄正清在省政府一次会议后见到邓宝珊,当晚即到邓家拜访。邓宝珊仔细听了黄正清讲的情况,明确表示夏河的属归应尊重当地僧俗群众的意愿,鼓励黄去南京请愿。黄到南京,向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和行政院院长汪精卫陈述情况,力争挽回原议,终于由行政院下令撤销了原来的决议。
第二年,邓宝珊受命处理甘南双岔事件。甘肃南部藏族地区,系安多藏区的一部,即今天的甘南藏族自治州。这里当时分布着25个藏族部落。各部落间常常因为砍伐林木、争夺草原而起争端,屡酿械斗惨剧。当地官府和甘、青两省的汉回军阀乘机插手,坐收渔人之利,以致冲突连绵不绝,愈演愈烈。1933年,双岔、西仓两部落的草山和林地纠纷更加升级。在多次派员解决无效后,国民党甘肃军政当局不得不再派邓宝珊为查办大员前往查处,于1934,年11月20日会衔发布了训令,要求“刻日起行,前往肇事地点”,就地解决问题。
邓宝珊接受任务后,即让新一军秘书长王新令收集有关资料,不仅了解事件本身,也对“番情”、“番规”各个方面,特别是宗教方面的情况注意收集、研究。对事件及藏区情况经过初步了解后,乃公开向社会发表办案方针:(一)以往查办“番案”者,率多贪婪妄为,藏民望而生畏。邓某此行誓以廉洁从事,公正处理,不蹈前人覆辙。(二)以往办理“番案”之员,率多带重兵,名为安抚,实际上是胁迫接受处理。本次绝不重兵压境,务使两地藏民不畏威而怀德。(三)以往办理“番案”,多取压制手段。此行决以和平方式处理,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从11月28日起,办案人员先后启行。12月5日抵拉卜楞寺。当地僧俗群众在寺外马莲滩举行隆重欢迎仪式,五世嘉木样致欢迎词后,邓宝珊即席讲话说:“此次奉命前来查办双岔案件,当广泛征求各方面对处理此案之意见,特别希望嘉木样大师、黄司令、邓县长全力帮助,参酌‘番理’‘番规’,秉公和平处理,以敦睦汉、藏及肇事各方之感情。务使双方相持已久之纠纷,得以适当、公正的解决。此外,并要考察当地各种实际情况,以资建议政府,改进文化、教育与耕耘方法。”最后要求肇事各方头目及活佛“即日前来,听候处理”;“各寺院僧众及附近居民,亦须各安心生产,不可妄生惊疑,以免滋扰”。
同时公布夏河保安司令黄正清和夏河县县长邓隆为“查办大员公署”顾问。在黄、邓和随行之新一军秘书长王新令协同下,邓宝珊就“番理”、“番规”和肇事人的情况作了广泛、深入的调查了解,作为处理事件的依据。
双岔事件的起因是两个问题:(一)双岔林场问题。在双岔、西仓两部落间,有一片纵横开阔,水草丰饶、森林茂密的林场,藏语叫“阿涅达赖”,意思是“插剑祭神的地方”。这一片覆荫绵长、兼有林牧之利的地方,许多年来成了双岔、西仓两部落争夺的对象,曾屡起争端。1921年,五世嘉木样活佛坐床后,宁海镇守使马麒的势力侵入拉卜楞地区,西仓头人唐隆郭哇和红布花觉即投靠马麒,双岔土官阿拉木教则仍倾向拉卜楞寺。双方各有两千余人,枪五百多枝。1933年,新编第十四师鲁大昌部进驻临潭,临近双岔,阿拉木教又投靠于鲁。双方势均力敌,各有背景,互不相让,武装冲突,时起时伏。(二)宗教问题。双岔寺活佛桑岔仓,是拉卜楞寺四大赛赤(佛位)之一,成人理事后中断了对土官的固定布施和牛羊供应,并以寺内一喇嘛还俗到土官衙门当了管家一事,衔恨阿拉木教,派武装喇嘛冲入土官衙署将还俗者抓回,复求助青海马步芳(马麒已死),打算彻底驱走土官。阿拉木教乃求救于鲁大昌。鲁派员“调解”土官与活佛之矛盾时,西仓头人唐隆郭哇率骑兵百余人,将赛赤佛接到自己部落,并于第三天乘大雾笼罩时袭击了驻临潭的鲁大昌部谷开基骑兵团,消灭了一个连,谷开基被打死。赛赤活佛见事态扩大,遂携走双岔寺院之银钱财物,焚烧了寺院,逃往西仓久住。鲁大昌部受挫,不得不撤退。得势的唐隆郭哇逐日抢劫双岔部落,大肆烧杀。在冲突中,西仓寺也毁于大火。至此,双方剑拔弩张,戒备森严,形势紧张。这才引起了省府方面的特别重视。
在对有关情况作了深入了解之后,邓宝珊一方面与助手反复研究、多次商讨,决定现场处理,当众宣布结果,以收教育僧俗群众之效。同时,他经过慎重考虑,也决定了在处理此案中扫除历来办理草山、林地纠纷时的陈规陋例。
12月12日,“查办大员公署”抵黑错(今合作),时肇事双方的头人、活佛、土官均已到达,听候处理。邓宝珊派帮办裴建准、马训,以及黄正清、邓隆、王新令等向他们说明情况,宣布和平公正解决之宗旨。又历数小争引来巨祸,荼毒僧俗民众之先例,晓以迷途知返的道理,令其反省。几天的审理中始终坚持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结果双岔头人对查办大员的处理方法心悦诚服,表示无条件接受处理,并保证今后与相临部落和睦相处。但西仓头人和赛赤佛仍态度强横、强词夺理。继而邓宝珊亲自晓以利害,使之改变了推诿责任的态度。
25日,邓宝珊亲自召集并主持大会,肇事双方及各部落头人,还有僧俗千余人与会,会场设在黑错寺院。会上宣布了裁判结果,主要内容如下:
(一)赛赤佛与双岔土官因小事引起忿争,致酿兵祸,乃不遵清规、有违佛法之行为,罚洋六千元。今后当忏情修悔。不许干预土官权限,不准与唐隆郭哇勾结。如不遵守,即将呼图克图(授予藏、蒙地区佛教上层大活佛的封号)名号褫革。唐隆郭哇以事不干己,怀挟旧忿,受人勾煽,聚众越境截杀官军,事后又不遵从省府命令进省,应罚洋四万元。准减罚款为三万一千元,并交还第十四师枪支。双岔土官小事不忍,致起大祸,念该员迭次呈报有案,从轻将双岔林场收省上直接管理,准该土官继续使用。
(二)西仓寺无故被焚,政府恻念殊深。应予帮助修复,拨给木料及款项。
(三)整编第十四师肇事官兵,概交甘肃绥靖公署军事裁决后以军法论处。
(四)明文规定:“最要者,唐隆、双岔皆系甘肃地方,属夏河县管辖……嗣后地方有事,概须呈报夏河县政府、拉卜楞保安司令部处理。大事转呈省政府处理。不得越界控诉。”
(五)双方具结,保证永久互不侵犯。
宣布之后,各肇事人因邓宝珊主张公道,并革除历来在少数民族地区办案官员索取贿赂,接受馈赠的陋规,故众皆心悦诚服。继又召集各部落头领,提出了一些有关行政管理的要求,其中特别提到“寺院、头人对藏民及汉回民众等一律平等待遇”,“不准打人,虐待部民”;“藏民子弟若能送学校受教育者,准优免当兵义务,头人不得干涉阻碍”,“黑错原有营房旧址改建学校,教育汉、回、藏子弟”。
邓宝珊此行,对随从人员约束甚严。途经各地一概不受民众的供应和招待,要求进入“番地”后不准乱窜寺院,不准调戏妇女,违者严惩。先行派出骑兵两名,携带绥靖公署及省府会衔的“不受任何招待”的布告,沿途张贴,俾众周知。办案过程中,邓宝珊除按藏族礼节接受哈达之外,拒收各头目所献的全部礼物。往昔办理“番案”,往往是官吏对少数民族敲诈勒索的好机会。就在这次案件发生的先一年,夏河县和陌务头人发生械斗,查办大员来“办案”,藏民所送现款就近一万银元,酒食供应,索需日繁。结果问题并未得到认真解决。邓宝珊此次一来就宣布要革除陋规,当地上层人士多有不信者,仍然循例办事,准备了马匹、钱款、珍贵皮毛等。直到此案处理结束,他们才确信当时真有廉洁之人。使藏区僧俗更感意外的是,查办人员的伙食也由“查办大员公署”自己办理,不接受当地供应和招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