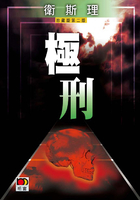程一路虽然一直跟蒋和川若即若离,但是,作为南州市最大的民营企业,他们是不可能不打交道的。不仅仅打交道,而且还得经常地打交道。对蒋和川早些年的实干,程一路是很欣赏的。但对后期,蒋和川的一些做法,他不太容易接受了,这也促使他与蒋和川逐渐地拉开了交往的距离。儿子程小路当初是以南日集团公派出国学习的名义出国的,后来张晓玉也是南日公派出去的。这里面,虽然程一路没有明地找蒋和川,一切事情看起来都是鲁胡生操作的,可事实上,没有蒋和川的同意,鲁胡生又能做得了什么主?民营企业,除了老总,是没有太多的民主的。
蒋和川出走后,把南州的政局一下子给搅乱了。有人抱怨,但程一路知道,他这一走,其实是稳定了南州的政局。一把悬在头上的剑,走了,难道不是更多人的定心丸?现在,这把剑彻底地消失了,许多人也许在梦中都会兴奋得笑出声来的。
第二天刚上班,齐为民就过来,告诉程一路,“叶茜叶总特地从北京过来了,说给程秘书长带了点东西。是不是现在就给你拿过来?”
程一路问:“什么东西啊?是她带的吗?”
“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齐为民说,“不是叶茜带的,而是她的一个朋友托她带过来的。”
程一路马上知道这是岳琪带过来的东西了,就让齐为民拿过来。不一会儿,齐为民就拿了个盒子过来,放在程一路的桌子上,说:“就是这,拿起来挺轻的,而且封了口的。”
程一路说:“谢谢了。”齐为民出去后,他拿起盒子,确实不重。他想了想,关上门,用小剪刀慢慢地划开外包装。里面又是一个小盒子,再打开,竟是一块手表。程一路一看表上的英文,就清楚这不是一般的表,而是一块进口名表。里面还有封信,是写在办公室的便笺上的:
一路:
不要惊讶,我怎么这么贿赂你了?不是的,首先声明,这表是我自己出国时,外国友人送的,是男式的。我想了想,除了你,我找不到合适的接受它的人选。
希望你能喜欢,也希望它能使我们感知到我们永远生活在同一个时间之中。
岳琪
程一路看着信,又拿过表看了看,心里五味杂陈。他将手表装到小盒子里,然后给岳琪发了条短信:
谢谢你。表收到了……
岳琪没有回,大概在忙吧。程一路将小盒子放进抽屉,在关抽屉的一刻,他又回味了岳琪写的那句话:永远生活在同一个时间内。这其实是一个多么美好也多么朴素的愿望啊!世界再大,可是时间很小。我们也许不能生活在同一个狭小的空间,可是,借着时间的长长的纬线,我们是能在茫茫的飞翔中彼此感知的。
程一路小心地撕碎了信,撕得很细,很小,然后放到桌子边的碎纸机里,又过了一遍,再看,已经完全是不成形的碎片了。刚才还是一封令人温暖的信,现在却成了一小堆没有任何意义的纸屑了。事物的变化是否就是如此?
手机响了,程一路看了看,是马洪涛的。他不用接也知道,一定是蒋和川的事。果然,一接起来,马洪涛就道:“蒋和川死了。”
“啊!是吧?”程一路问。
“是啊,刚才他的两个亲戚才到市委来说的。说蒋和川临死时要求他们转告南州市委,就说蒋和川自己并没有带走什么钱,而是……”
“嗯……”
“而是也用在别人身上了。但是,是谁,他们没说。”马洪涛道,“其实现在的市委班子里,大部分人都不认识蒋和川了。他大概是想死得明白些。”
“唉,人死了,就不说了吧。”程一路叹了口气,问,“望春小学开学了吧?”
“开学了。我前几天还专门去过。孩子们坐在新校舍里,别提多高兴了。看着他们,我就想起程书记您。我甚至有种冲动,想告诉他们‘这是你们程伯伯捐款建设的’。”
“瞎搞!没说吧?”
“当然没说。只是冲动。但是我感觉县里可能有些猜测,乔亦晨就侧面问我,说:‘到底是怎么回事?人家捐了这么一大笔钱,不能连个感谢的话也不说吧?’”
“那你……”
马洪涛一笑,“我对他们说,这人捐款的前提就是不透露姓名。你们把学校建好了,再把教学质量抓一抓,就是对他最大的感谢了。”
“这话回得好。既然学校已经建成使用了,洪涛啊,从此以后,就别再提这事了。好吧?”
“那……行!”马洪涛顿了下,道,“程书记,还有个事,我想征求一下您的意见。”
“说吧。”
“齐鸣书记让我到湖东搞书记,说要将朱潇凌换上来。我觉得不太合适,程书记您说呢?”
“当然不合适。这事以前齐鸣同志提过,我没同意。看来,他还是想……”程一路道,“不需要我和齐鸣同志说说吧?”
“我准备向他汇报下,明确表示不同意去。暂时就不麻烦程书记了。”马洪涛说,“什么时候程书记,不,程秘书长再回南州来看看。底下很多同志都很相信程书记呢!”
“就你会说。”程一路停了下,“以后有机会过去吧。”
“那好!”马洪涛却并没放下电话,而是继续道,“天白书记昨天到省纪委,就南线工程的事,据说……”
“是吧?”程一路没想到莫天白还在一直地找,“这事组织上会有考虑的。就这样了,下次再说。”
挂了电话,程一路坐下来,喝了口茶,头竟然猛地晕了下。他赶紧用手压住太阳穴,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再缓缓地呼出来。这一呼一吸之间,头晕的感觉消失了。可能是刚才一直站着接电话,大脑受到辐射的缘故。人到了这个年龄,是由不得自己的了。
程一路长舒了口气,拉过文件,正要看,来琴叩门进来了。
见她有点慌张的样子,程一路就问:“怎么了?有事?”
“是有事。刚才我接到个电话,是个女的,说辛民辛秘书长他……”来琴望了眼程一路,脸却是红的。
“他怎么了?”
“说他在广州出差时,同她发生过关系。现在,她怀孕了,找辛民,辛民却不认账。你看这,这……”来琴攥着双手,急道。
“有这事?”程一路也吃了一惊,不仅发生了关系,还怀孕了?这事……平时看辛民副秘书长,人不太像能做出这等事的样子。怎么就……
“程秘书长,这事要不要向其哲秘书长汇报?”
程一路皱了皱眉,“暂时别汇报吧。我回头单独向其哲秘书长汇报。这事更不要在办公厅内部说,我会处理的。”
“那好。不过,那女的再来电话怎么办?”来琴走了几步又转回来问。
“那就告诉她,让她直接找辛民嘛!”程一路道。
来琴说那好,就出去了。她前脚刚走,辛民后脚就进来了。辛民脸上有一种不太自然的笑,印象中,辛民这还是第一次踏进程一路的办公室。
“坐,坐,辛秘书长,有事?”程一路说着起来,陪辛民一起面对面坐在沙发上。
辛民的脸色更难看了,“一路秘书长,有个事,我想……”
“怎么就吞吞吐吐了?说吧,什么事?”程一路其实已经明白辛民也是为刚才来琴所说的事来的。那女人敢给办公厅直接打电话,就一定在打之前和打之后,都告诉了辛民的。辛民是聪明人,与其等着出事,还不如先说出来为好。我们党的政策一贯是“坦白从宽”,事实上,坦白也是掌握解决问题的主动性的一种有效方式。
“有件事,我想先和程秘书长通个气。”辛民刚才还小着的声音,渐渐地提高了。
“啊,是吧?”
“是这样。”辛民道,“上半年,有一次我到广州出差,不是和交通厅的几个同志一道嘛。晚饭后去洗了个脚。不想前几天,竟然有个女的,说她同我……而且还怀孕了。你说,这……这不是天方夜谭嘛!”
程一路向前倾了下身子,“啊,有这事?是不是讹你啊?现在这样的骗子挺多的。”
“当然是讹我。”辛民有些气愤了,“我左想右想,大概是洗脚时,身上的名片不慎落下去了,被她拾着,就来这一招。再怎么说,怎不……”
“也是啊。”程一路心想,要是传出去,事情马上就不一样了。一个堂堂的省委副秘书长,在外嫖娼,而且弄大了别人的肚子,这还了得?要是曝出来,岂不成了江南省一号新闻?
辛民声音又小了,“本来,我想这事也没什么。可是她老是打电话来,而且可能还打到办公厅电话上了。我怕……到时候,就是有十张嘴也说不清哪!”
“这个是得慎重。”程一路起身回到椅子上,“我问你,到底有没有那回事?”
“怎么会有呢?”辛民的声音又低了。程一路也就不再问,而是道:“这样吧,这事刚才来琴同志也跟我说了。我说暂时不要给其哲秘书长汇报。毕竟事情还没弄清楚嘛,是吧?既然你过来了,我想关键是两点:一是向对方申明,如果再这样纠缠,就要向公安机关报案了;二是了解一下当时其他在场同志有没有也收到这类电话,请他们在适当的时候,为这件事作个澄清。辛民同志,你看呢?”
“这很好,”辛民笑着,“我就是怕大家误解。男女的事,谁说得清啊!”
“就是啊,因此还是慎重些好。”程一路也笑着,应了句。
辛民说:“既是这样,那我就走了。”说着,就往门边上走,刚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一路同志啊,在办公厅的有关制度上,我可能有些做法……这个还请你谅解啊!我也只是说说嘛!前不久,我和王浩同志在一块还聊到你,他说你是一个心胸坦荡的人,这就好!我喜欢和这样的人共事。以后还要多多关照啊!”
程一路哈哈一笑,“哪里。彼此关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