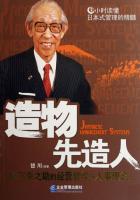终于闹到筋疲力尽,嗓子也沙哑得说不出话来,才一头栽倒,横卧在酒菜之上,酣然睡去。
亲兵听到鼾声才敢进去。先把他抬到干净处,把衣服擦拭一下,方抬进卧房床上。然后又开始打扫大帐,光摔坏的杯盘碗碟等器皿,就装了整整大半竹筐。
酒醒之后,忆起自己席间所讲之话,王錱越想越怕。尽管听他讲话的人都是自己的亲随,不可能去出卖自己,但须防隔墙有耳、门外有人。自己讲的话,只要有一句传进曾国藩的耳中,不仅功名无分,恐怕连营官也要做不成!——自己这一生,就算彻底毁掉了!
想到这里,王錱再也不敢躺下去了。
尽管时候已是子夜,但他仍把亲兵传来,吩咐备马,又把两名帮带从睡梦中唤起来,把营务交代了一下,便只带了二十名亲兵,打马离开郴州,旋风也似赶往衡州。
他要抢在“门外人”的前面,当面向掌握湘勇命脉的统帅曾国藩,表表自己的忠心。
曾国藩离开湘乡的第一站是湘阴。曾国藩到湘阴的当晚,由知县邹汉章陪同匆匆吃了碗豆腐白米饭,便连夜检查了湘阴的城防及团练的会操情况。
湘阴在月前也招募了一营团练,由知县邹汉章亲自做营官。
曾国藩的轿子进城关时,邹汉章已经提前得到了消息,便让五百名湘勇全部着了勇字营服,一半人拿了火枪,另一半人背了单刀,排列成两队,在城关迎接自已的统帅。
仅仅经过一个月的训练,曾国藩见邹汉章管带的这营湘勇,很有经制之师的模样。曾国藩不由对这位邹知县,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些许佩服。
邹汉章本人也对曾国藩恭敬有加,始终站着同曾国藩讲话。
这令曾国藩大受感动,当即决定,由衡州返回省城后,就从发审局粮台和湘勇各营,抽调三百支火枪、两门前膛开花炮过来,并把这五百人纳入到老营的建制。由发审局粮台统一拨饷、拨弹子,统一调遣。
邹汉章闻听之下,登时大喜过望,口里连连称谢不止。没有人会想到,邹汉章做得这一切,就是要达此目的。
曾国藩离开湘阴,邹汉章送到城外,小声问一句:“大人下一站去哪里?要不要下官派人护送?”
曾国藩道:“我哪儿也不去了,直接回省城。邹明府,你请回吧。”
邹汉章把曾国藩扶上车,驻足看轿车走远,才带着属官回城。
曾国藩的车子上了通往省城的官道,才对萧孚泗交代一句:“去衡州。”
萧孚泗闻言大惊,急忙下马走到车前,小声问道:“大人,天太晚了,去衡州的路不太平啊。您老既然要去衡州,应该让邹大人加派些人手啊!”
曾国藩道:“孚泗,你不必担心。只要不走漏风声,湖南各县任由我们来去。白天太热,夜里凉爽,正好赶路。——去衡州!”
萧孚泗不再多言,翻身上马,带上亲兵簇拥着马拉轿车直奔衡州。
湖南的夏夜甚是凉爽。正是水稻扬花授粉的时候,瓜果也正熟得迸蜜。微风徐徐,满世界的稻香和果香。
蛙声是夏夜里最美的歌声,无论夜有多深,更无论年景如何,只是唱个不休。此起彼伏,一浪压过一浪。
深冬看雪,夏夜听蛙,是人世间最省钱又最不费力的浇愁办法。
曾国藩此时此刻的心情也很好,一扫半年来的郁闷、忧愤情绪,竟然看着看着顺口吟诵出两句诗来:“我本世间俗物,却成画中仙人。”
本想就着心情再续上几句,哪知路过一处村庄,竟使他猛然忆起初访彭玉麟的情景。脑海中一蹦出彭玉麟三个字,他马上便想起了水师,由水师又想到了造船。
一想到这些,曾国藩吟诗的兴趣登时无了踪影。
曾国藩回湘乡为亡母行小祥之礼期间,彭玉麟曾去住了一夜,向他禀报了造船的进程及水勇的训练情况,并向他推荐了一位水师管带:杨载福。
其实,让杨载福出任水师营官,是曾国藩早就在心里确定了的。杨载福虽是湖南绿营陆路千总,但因一直驻湘阴防营,经常随水师在江面捕盗拿贼。这就使他不仅练出了一身好水性,对水上的作战方法,也很有自己的一番见解。
依曾国藩与彭玉麟原议,水师先募两营。彭玉麟自带一营,另一营交谁管带,曾国藩一直没有明说。
彭玉麟同时向曾国藩讲了船厂迁址的事。因原厂址离江太远,试船修船有许多不便之处。无奈之下,只好重新选了块离江边较近的地皮。
关于造船的进程,据彭玉麟讲,已有一只拖罟正在组装,两艘快蟹已经完成,六条长龙即将下水。现在匠工们正在刘长佑的亲自监督下,日夜赶造快蟹、长龙以及小舢板。
彭玉麟又说,知县王睿和知府赵大年,也经常到船厂帮忙出主意。用人用物,鼎立相助,全无二话,进程因此才得加快。
得知王睿与赵大年如此,曾国藩直到彭玉麟离开湘乡,仍唏噓不止,甚是感慨。
车子进入衡山县城关时正是夜半。
曾国藩着萧孚泗就在城关找了家客栈住下。
第二天一早,简单在客栈喝了碗稀饭,曾国藩便坐上车,直接赶到团练衙门来见刘长佑,然后再由刘长佑陪同,去船厂看船,去江边看正在训练的水勇。
到了辕门,曾国藩为了给刘长佑一个惊喜,便让萧孚泗等人候在大门外,自己直接走了进去。
进团练衙门要先见门政。因天色尚早,门政正在洗漱。
见曾国藩推门进来,门政急忙拿过布巾擦了擦脸,便问何事。
曾国藩看门政有些面生,想来是新人,便道:“我是来捐资办团的,想见你家刘大人。”
门政道:“刘大人还没有过来,衙门里只有昨夜值事的吴大人。你要捐银子,刘大人早有吩咐,直接进去就行,不用通报。”
曾国藩道一声谢,便背起手向里面走去。
走进衙门的值事房,果然见一名老胥吏正伏在案前看书。
听到门响,老胥吏抬起头来说道:“你要找哪个?如何不通报?看你也是个读书人,应该懂衙门里的规矩。”
曾国藩见又是个面生的,不由道:“我要见你家刘大人,有要事相商。”
老胥吏皱眉道:“刘大人最近忙得很,本官寻他也很费劲。你不妨到船厂去看看。说不定运气好,就碰上了。”
曾国藩道:“动问大人,船厂怎么走啊?可否劳您老的大驾,送我过去?我不是当地人,对这里不熟啊。”
老胥吏见曾国藩衣着朴素,又不是官员,便一脸不耐烦地说道:“船厂只在城北,过护城河便是。叮叮当当的声音,聋子都能听到。本官还有公干,老相公自已去吧。本官擅离职守,刘大人回来是要打板子的。本官没了差事,你赔不起。”
曾国藩见那人说的认认真真,以为他当真有什么大事要办,便不敢再勉强,说道:“那就劳烦您老说的再详细一些吧,也省得小人走冤枉路。”
那胥吏一听这话,却兀自瞪圆眼睛,大声骂道:“你这个穷酸老秀才,怎么如此聒噪!你读了几十年书,莫非都读到狗肚里去了?湘勇的船厂,全衡州都知道,咋就你闭塞?你慢慢地走慢慢地问,自然就能走到。你急什么急?急得又是哪般?又不是去抢孝帽子!”
老胥吏话毕,故意装出气忿忿的样子,把头仰起来望向别处。
曾国藩笑一笑,只好走出辕门,一边上车口里一边道:“往北走就是船厂。”
萧孚泗前边带路,轿车跟在后面,亲兵前后左右簇拥着车子。
因是城中闹市,车子不敢走快,停停走走,整整用了近一个时辰,才走到北城门的护城河边。
出了城门,走不多远便到了江边。
萧孚泗用眼四处张了张,却哪里有半点船厂的影子?便对曾国藩道:“大人哪,船厂不会建在水里吧?”
亲兵把曾国藩扶下车子,往对面望了望,也不见有什么作坊,只有个孩子在江堤上跑来跑去地疯玩。江面上,飘有几艘鱼舟荡来荡去,在往来张网捕鱼。
这时,一名汉子正挑着两担活鱼从吊轿上走过来。
曾国藩忙迎上前一步,笑着道:“动问老哥,湘勇的衡州船厂不在城北吗?”
汉子到了跟前,见是个书生,便道:“是哪个二大爷给你指的路?船厂在城西三里铺子,何时建到了城北?也不问清楚就瞎跑腿。这样跑来跑去,跑到天黑你也见不着船厂。你们以为,衡州城是自家锅屋呢?快往三里铺去吧!―――哼!”
萧孚泗气得几次想抡拳打他,都被曾国藩用眼止住。
见汉子走远,曾国藩对萧孚泗笑道:“孚泗啊,我们本应该在湘阴住上一夜的。但我看船心切,自然要受人奚落。”
萧孚泗一边开车门一边道:“不是您老拦我,我把他丢进水里去喂鱼!——看他还敢不敢耍贫嘴!”
曾国藩重新坐进轿子,吩咐一声:“去城西三里铺子!”
萧孚泗慌忙上马,一边问路,一边向城西行去。
曾国藩赶到城西的三里铺子时,时候已近午时。毒辣辣的烈日挂在当空,赛似一团燃烧的火球,直把江面烤得热气弥漫。
萧孚泗此时早已经汗流浃背,马也热得鼻孔翕张,通身冒着腾腾热气。
萧孚泗骑不住马,下马牵着缰绳,把车子引到一棵大树底下停住。
亲兵们早已不等吩咐,便纷纷脱掉勇服,团成一团挂在枪上,做出逃荒人的样子。
曾国藩在车里热得难受,也只好被亲兵扶下车。
萧孚泗一边给马擦汗,一边小声说道:“好你个彭相公!你是成心不想让大人好好看船!”
曾国藩这时却道:“孚泗,你细听听。我怎么听着有什么声音呢?”
萧孚泗一听这话,急忙聚精会神地听了听,果然听见叮叮当当的声音传入耳鼓。但声音却非常飘渺,时断时续,时有时无,像是来自天籁。
萧孚泗把马交给亲兵,快步走到曾国藩身边道:“大人,我们好像又走错了路。您老细听,是后面在叮叮当当。”
曾国藩向四外望了望,对萧孚泗道:“孚泗,你打发个人去前面寻一寻。我们在这里歇歇脚。我湖南还从未有过这么热的天气。”
一名亲兵很快按照萧孚泗的吩咐,打马向前边跑去。
约有两刻钟,亲兵顺原路返回,向曾国藩禀道:“大人,我们又走错了路。”
曾国藩问:“这里莫非不是三里铺?想不到,衡山城外的地理这么复杂。”
亲兵答:“这里是三里铺,但我们刚出城关时,应该拐到堤下走。我们没拐,所以错了。再往前,就是四里铺了。”
萧孚泗道:“怪只怪彭相公!恨不能把船都藏在水底下!”
曾国藩重新上车,奔原路返回。行至城垣,渐近河堤,看到堤下果然隐蔽着一条不甚宽敞的路。
下了大堤,又行了两里左右的路,两排简易泥草房,便出现在曾国藩的眼前。这分明就是船厂了。周围立着一人多高的竹栅栏,上面都削了尖尖的顶子,只留有一个大门供人往来出入。
在场地外围,曾国藩喝令停车,所有马匹亦都栓在车的周围。
一名亲兵,急忙打开一把遮阳大伞,飞速地罩在曾国藩的头顶。
萧孚泗仍在前面带路,当先走进大门;曾国藩在亲兵的簇拥下,跟在萧孚泗的后边进入船厂。
曾国藩一边走路,一面抬眼四处观察这一带的地形。这里地势较江面高出一大截,背靠一座偌大的沙土堆,作坊都设在竹席搭建的棚子里。从江上往这里看,应该是个晒鱼场;从其它方向看,是座大土山。看了这里的地形和船厂的位置,曾国藩不由赞叹一句:“真是天遣彭雪琴来助我成功!”
十几名巡哨的湘勇,持枪挡住了萧孚泗的去路。
萧孚泗跨前一步,手指跟在后面的曾国藩道:“曾大人到了,还不快去知会彭大人迎接!”
众湘勇一愣,齐向曾国藩望去。
一人对萧孚泗笑道:“你这位大哥,说不定是个真管带。曾大人是个侍郎,如何打扮得跟个老秀才似的?你说他是曾大人俺不敢怀疑,但这里现在管事的只有刘大人。但刘大人一早也走了,说是去接曾大人!现在,你又领来个曾大人!”
曾国藩这时已被众亲兵簇拥着,从湘勇的面前走过去,正向一只高大的拖罟靠近。
湘勇在后面大叫:“看只看,可不许用手乱摸呀!刘大人不许人用手乱摸的!”
萧孚泗不理睬,拔腿去追曾国藩。
二十几位做工的人正围着拖罟忙碌。有人在钉铁皮,有人在打磨船梆。还有两人手拎漆桶,在为打磨好的木板上漆。不远的空地上,堆满了大量的竹子、铁皮和板材,有上百人在这里往来搬运。土山的顶端,搭了一个不甚大的瞭望哨,上面有人在向这里张望,想来是监工用的。
曾国藩快步走到高大雄健的铁皮包舷的大拖罟跟前,心底不由一热。他一只船一只船地看,越看越觉着兴奋。
做工的人都忙着手里的活计,没人理会他,任着他绕来绕去地看个不了。
曾国藩忽然停下脚步,用手一边抚摸船底,一边口里呐呐道:“我湘勇也有了大战船了!长毛再也不能独霸长江了!”
话毕,又慢慢地走动。
就这样走着,看着,摸着,曾国藩忽然眼眶一湿,两行热泪滚滚而下。
曾国藩立住脚,仰天从心里感叹一句:“天助我成其功!”
萧孚泗跟在曾国藩的后面,猛见曾国藩哭了起来,不由一愣,忙道:“大人,风地里哭不得呢!俺娘就因为在风地里哭,哭瞎了眼睛呢!”
曾国藩这才意识到自已的失态,便忙掏出布巾把眼泪擦掉,口里却道:“孚泗,你何曾见我哭过?我这风沙眼一见风就淌眼泪!你去问问做工的人,刘大人和彭大人他们在哪儿?我们来了好一会儿了,他们怎么还没露面?”
萧孚泗却忘了湘勇适才说的话,忙让身边的人去问。亲兵很快回来禀告:“禀大人,做工的人说,这里现在管事的只有刘大人。彭大人在前面不远处的江边操练水勇。刘大人一早就去城外接大人了!”
曾国藩边往回走边道:“说不定,子默此时就等在衡州的团练衙门里。行了,船也看到了,我们先到江边去看看雪琴,然后再去城里会刘大人。看这样子,再有两个月,这些船就能下水了。”
萧孚泗喜滋滋地道:“大人哪,俺长这么大,还没见到这么大的船呢!像这么大的船,坐上一坐,死也值了!——大人哪,这到底是什么船哪?看样子像拖罟,但又比拖罟大。真稀罕!”
曾国藩边走边道:“这应该就是拖罟,不过型号大一些罢了。详细情形,进城一问子默和雪琴就什么都知道了。”
曾国藩步出栅栏来到车前,又回头看了两眼那只大拖罟,这才被亲兵扶上车。
这时有马车拉着一车西瓜行过来,车后跟着两名湘勇。
萧孚泗一见大喜,慌忙跑过去,用手指着曾国藩的车驾道:“曾大人来看船,和你们刘大人走岔了路。你们快切几个瓜给曾大人解渴!”
押车的湘勇一听曾大人到了,马上便飞跑过来见礼,一人口里说道:“曾大人我是见过的!曾大人我是见过的!”
两人到了车前,正要施礼,曾国藩已掀起帘子说道:“天气太热,都不要多礼了。工匠辛苦,快些把瓜送进去吧。”
一名湘勇高兴地说道:“果然是曾大人哪!”
话毕,两人匆忙给曾国藩行了个大礼,便又飞跑回车前,一人抱了一个大西瓜过来,塞到亲兵手里说:“给大人解渴吧。”
曾国藩笑道:“你们快把瓜送进去吧。”
二人又行了礼,这才走回去,押着瓜车进了栅栏。
萧孚泗走过来,掏出腰刀把瓜逐一切开,先递给曾国藩一块,然后便站在一旁伺候。
曾国藩接过瓜,犹豫了一下说道:“今天都不许拘礼,一起吃瓜,然后去看操。”
萧孚泗一听这话忙大声道:“大人有话,还等什么?”
话未及落音,他已当先拿了个大块的吃起来。
两个西瓜进肚,大家感觉凉爽了许多。
“国藩数年以来,痛恨军营习气,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一人不丧尽天良,故决计不用营兵不用镇将。吾师欲将省城现有之兵,移之于船,却与国藩初志不甚符合。此间拟尽招水手,令其学放炮而已。不特兵不可用,即陆勇亦不可移用。”
——摘自《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复吴甄甫制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