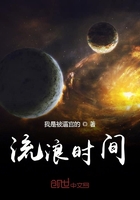“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
一曲未完,房宜主却不肯继续唱下去。疆儿为她倒了杯茶,又接过她手里的琵琶,问道:“小姐,你唱的很好听,怎么不接着唱了?”
房宜主啜了口茶,才慢慢道:“曲子好听是好听,就是太幽怨了,伴着琵琶的音律听起来更是愁思百结,我唱不下去了。”
“这曲子是讲什么的?”
“这是一首诗,名叫《子衿》,是《诗经.郑风》里的一首。《子衿》的意思是一个男子在城楼之上苦等自己的恋人前来相会,可望穿秋水,也没能等到。所以两人之间的爱意变得哀怨缠绵,唱起来就多了丝纠结。”房宜主耐心为她解释。
疆儿还是有点疑惑:“既久等不来,那男子为何不主动前去寻找他的爱人呢?”
“因为那根本就不是他的什么爱人。”
房宜主含笑回过头,见门外由远及近走进一袭白衣。
“哥哥。”
“你们在讨论《诗经》?”房易安寻了个离房宜主最近的凳子坐了下来,扫了一眼桌上的词谱,饶有兴致的问道。
房宜主一边收起词谱交给疆儿,一边向他挑眉道:“你刚刚不都听见了吗?”
疆儿收了词谱,抱起琵琶,像两人行了礼退了下去。
房易安看了眼疆儿抱走的琵琶,笑道:“还在练呐?这次打算玩多久?”
“谁说我学琵琶是玩啊!我每天都有认认真真的弹啊,你看看你看看,我十个手指都要磨出茧子来了!”
他握起房宜主的双手,触目所及,十根芊芊玉指变得红肿不堪,有两个手指已经磨得皮都要爆开,血丝隐现。他的心一阵刺痛,紧皱着眉道:“以后不准再练了!”
“为什么?我很喜欢啊!”她猛地抽回自己的手,惊疑道。
房易安手中一空,胸腔也像被猛地抽空一般,他仍是端着刚才的姿势,手虚虚握成半拳状。他竭力表现得自然,悄悄舒口气,语气平平道:“又不是让你参加什么比试,稍微练一练,知道琵琶几弦几音就行了,何必这么拼命?”
房宜主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仰天假笑几声,恶狠狠地凑近他道:“欸~你心疼啊?”
房易安略带尴尬的向后微仰身子,沉声道:“废话!你是我妹妹,我不心疼你谁心疼你啊?”
房宜主哦哦两声,不以为然道:“你跟娘亲一样,我每学一个新玩意儿你们都要挖苦我一番,好像我天生一事无成似得。我要真开始认真学了吧,你们又一副看笑话的模样。这次我要听了你的话,又半途而废了,以后你们一个个的不定拿这事怎么逗我呢!这次,我一定要证明给你们看!我房宜主还是很聪明的,凡事只要我想做就没什么做不到的!”
她那厢气势昂扬,房易安却不停地向她泼冷水:“你要早有这份决心,琴棋书画早就样样精通了。”
“你看!你又开始挖苦我!”
房易安无奈的摇摇头,轻笑:“好好好,我不说了,你过来,我看看你的手。”房宜主乖乖的将双手举到他面前,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房易安知道她这模样多半是装的,要真疼早就跑到娘亲面前撒娇哭嚎了!只是,就算是知道她是故意做出这可怜样子博取自己的同情,他还是忍不住想轻轻为她吹吹伤口,做一切事情来缓解她的伤痛。
房易昭昨天跟他闲言时,还感叹似得冒出一句:“全家人疼满愿真是疼的没边了,你呢,简直是疼她疼到骨子里!”
房易安并没有觉得自己有多么宠溺房宜主,她是自己的妹妹,又是房家最小的孩子,唯一的女孩。生的活泼可爱,怎能不让人心生怜惜?现在想来,大哥说的那句话还是有据可依的,从小到大,他将自己一切的温柔全部给了房宜主,在他这里,房宜主可以肆无忌惮,这也是为什么房宜主最粘他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他也已经习惯了这种相处模式。
房易安轻轻吹着她的伤口,自言自语道:“旧伤未愈,又添新伤,你真是不让人省心。’
房宜主嬉笑道:“腰上的伤早就好了,哥哥不用记挂了。“
房易安丢一记白眼给她:“你屋里的药箱呢?“
“不行不行!不能抹药,珠玑说手指只有破一次才能生出茧子呢,你现在给我抹上药我还怎么练琵琶呀?“
房易安哭笑不得,他挫败的重新坐下,醋意道:“你还真是···!你怎么那么听珠玑的话啊?她说什么你就是什么!“
房宜主不知道他哪来的火气,只能老老实实的回答:“我觉得珠玑说的对啊···”
房易安欲拍桌而起,只听屋外瑞伯的声音传来:“小姐,有人送来东西要您收下。”
房宜主立马应道:“瑞伯,你进来吧。”
瑞伯进来才看见房易安,又先向房易安行了礼,才将手里的东西双手呈给房宜主。
是一块红色包裹包着的小方盒,包裹上是上等的绣工绣制而成的夏荷图,荷叶翠绿,荷花嫩红,肆意的铺张在整个包裹之上,张力十足,活灵活现,似一阵风吹来便能见荷花摇曳起舞。
房宜主解开包裹,取出方盒,看了一眼,得到房易安的准许,才小心翼翼的打开盖子。看到盒子里的物什,她不由得睁大眼睛,倒吸一口凉气。
一块白玉石被雕琢成小巧的方形,手心般大小。白玉石莹润细腻,触手温和。方形六面皆用血红的玉石镶嵌了不同数量红点,像极了一颗颗圆润的小红豆。房宜主笑着惊叫一声:“啊!是一颗骰子!”
房易安挑挑眉,伸手从盒子里拿起这颗玉石骰子,骰子摇摇晃晃在半空中,金黄的长绳被房易安勾在食指,她才辨认出这是一件腰佩。
房易安拿着这件腰佩端详许久,不确定的口气说道:“竟是和田玉与血玉融合。”
房宜主好奇地盯着这颗骰子,骰子她见过,也玩过,但没见过用玉制作的,所以觉得很新奇。
“哥哥,你说什么?”
“哦,没什么···瑞伯,这东西是谁送来的?”
瑞伯回道:“是一个年轻男人,指明了要送给房府的大小姐。说这是他家公子为报小姐的救命之恩特意遣他送来的。”
房宜主低下头,思索片刻道:“那送东西的人呢?”
“回小姐,那人送了东西,只叮嘱说一定要亲手交给小姐,便走了。”
房宜主满脸失望,从房易安手里拿过腰佩,啧啧着不言语。
房易安追问她:“那个公子是谁?什么救命之恩?你那日的腰上与他有关?”
房宜主遣退了瑞伯,趴在桌子上摇着手里的骰子支支吾吾,不肯正面回答。房易安看着晃来晃去的骰子,心里莫名的一阵烦躁,他一把将骰子夺了过来。房宜主猛地起身,下意识大吼:“把骰子还给我!”
房易安将手背到身后,任她怎样张牙舞爪就是拿不回来。
“想要骰子当然可以,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好好好!”房宜主泄气的坐了下来。
“我的腰伤确实跟那人有关,但也不是完全怪人家。你也听瑞伯说了。这个送东西的人只是那位公子的家仆。我那日也只是顺带着伸出援手帮了那公子一下下,其实也说不上什么救命之恩。”
“你还没告诉我那位公子是谁。”
房宜主无奈道:“萍水相逢!我哪知道他是谁啊?我本来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谁知那公子能找到我,还···送这么贵重的东西。···欸?哥哥,这真的是和田玉吗?”
房易安“啧”了一声,一个没注意,骰子又被房宜主抢了回去,她朝他做出胜利的手势,做出一个鬼脸,最后拿着骰子满意道:“嗯,好新奇的玩意,刚刚好做我的挂饰,下次进宫带给繁婴看······”
房易安满脸阴沉,盯着骰子喃喃道:“浪荡公子···”
房宜主没听清,冲着他嗯了一声,他默默的摇头。
“哦,对了。”房宜主忽然想起了什么,将手里的骰子放下。“哥哥,你刚刚进门时说《子衿》一诗不是描写男女情~爱的,什么意思啊?”
房易安本想离开,听到她的问题又振振衣袖,背起手,一副说教的模样:“《子衿》一诗并非像世人理解的那样是讲述情~爱缠~绵的故事。它其实说的是同窗之间的友谊,男子想念自己的朋友又没有办法前去与友人相见才生出愁思。虽只一日未见,但却像是过了很多年。懂了吗?”
“原来是这样啊。”房宜主点点头:“珠玑也有说错的时候,嘿嘿,这次可以好好笑话她一番了···”
房易安听了,眉间流露出一丝不满:“她整天都教你些什么东西?”
房宜主不敢反驳,只暗暗吐吐舌头。
房易安叹口气,转了话题:“今日我上朝的时候,碰见祁护了。”
“咦?”房宜主已经很久没有听见这个名字了,她抬头看着房易安,问道:“怎么了?”
“你们现在是朋友吗?”
“嗯···谈不上。”
“他让我问候你。”房易安斜睨她,似乎想从她的脸上看出点什么。
房宜主也着实吃了一惊,祁护问候自己做什么?虽说他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但也不至于心眼那么小,到现在还对那件事念念不忘,想要报复自己吧?
“他为什么要问候你?他知道你是谁了?”
“呃···,他应该是知道了,不过我也不清楚他为什么要问候我,我也好久都没见他了。”
房易安摇摇手:“算了,反正问你什么你都不知道。你只要记住,以后没事不要招惹祁家人。”
“我哪敢呐。”
“别人也不行,陌生人更不行。”他再三叮嘱,房宜主有点不耐烦。
“你干脆让爹爹把我禁足好了!”
“······我巴不得。”
······
第二天,房宜主去找珠玑练习琵琶,珠玑虽没明摆着拒绝,但言词里总是婉言推脱,房宜主一碰琴弦珠玑就过来转移她的注意力,弄得她一整天连一首完整的曲子都没弹下来。
最后,房宜主忍不住了,拉着珠玑的手苦笑:“你这师傅真是不尽责,学生想安静的弹首曲子,你就不能清静会?”
珠玑弯弯嘴角,也是苦笑连连:“我的大小姐,不是我不想让你弹,是我不敢让你弹呐。”
房宜主咬咬下唇,试探道:“是我哥哥来找过你了吧?”
珠玑既不点头也不否认。房宜主哼哼两声,:“我就知道··,我不管,今天我一定要好好弹首曲子!”
珠玑劝了几次拗不过她,只得同意,但也不让她弹太难的曲子。
“前阵子我教你的民间小调你练得怎么样?”
“早就烂熟于心了。”
“你要坚持弹,就弹这一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