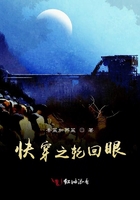作为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常安顺的办公室跟书记刘定国的办公室差不多大小,都带有一个小套间,里面支有一张单人床,平常加班或者中午不回家的时候,可以稍事休息。
近来,常安顺打破每天中午在办公室套间的床上眯一觉的习惯,开始回家睡午觉。他不得不打破这个习惯,原因是这段时间,到常安顺的办公室里准时来上班的,除了常安顺本人以外,还有一个人,一个女人——程小鸢。
程小鸢现在所有的工作,就是四处上访告状,一心要给自己的丈夫讨个清白回来。北京去过,省委、省政府、省纪委去过,有好几次她赖在省纪委不走,还是信访办的同志去省上把她领回来的。市委市政府就更不用说了,隔段时间,程小鸢就会找刘定国或者万长卿闹腾一回。常安顺也给闹腾过,但常安顺脾气好,觉得女人嘛,都是这个样子,何况刚死了丈夫,其内心的凄苦和绝望可想而知。
但现在,程小鸢的状也不怎么好告,原因是经常有人监视她,只要她这儿一有风吹草动,就立马会有相关部门的人找她谈话,给她做工作,警告她不能再越级上访,否则后果自负。
程小鸢也犯了浑劲儿,她想,越级上访你这管那管的,我不越级上访还不成吗?我就找市政府,找市纪委,找常黑子,把那些个贪官污吏、奸商的皮给扒下来,让老百姓瞧瞧,让雎阳人瞧瞧,还自己丈夫一个清白。
程小鸢的丈夫姓沈,叫沈阳,原衢水县常务副县长。沈阳当时死得很蹊跷,连人带车被泡在一个水库里足足过了半个月才被人发现。公安介入调查了,最初得出的结论是意外事故,死者在自己驾车的时候有喝酒的嫌疑,车速有可能太快,冲出了路面,直接栽进了公路下面几十米深的水库里。但有人提出了质疑,说是半夜三更的,沈阳跑到那个僻远荒凉的水库去干什么?这是第一个疑点。其次,从死者掉进水库的方向来辨别,即使是酒后驾车,车速太快冲出路面的话,按照物理学上的惯性原理,应该是冲进水库源头的浅水区,而不是跟滑落路面呈垂直方向的深水区。后来又折腾了些日子,得出了新的结果,这次定性为自杀,认为沈阳当时在竞争县长职位时,思想压力过大,导致精神分裂,心里承受不住自杀了,醉酒有可能加速了他的精神崩溃。得出这个结论的,是一位从国外留学归来的犯罪心理学博士。程小鸢之所以一直上访,除了丈夫死得不明不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公安部门得出的“自杀”结论,她认为这个结论压根儿就是在侮辱她的丈夫。
常安顺也不相信那个留洋博士的胡说八道,沈阳的承受能力如果那么差,他根本就混不到常务副县长这个位子上来——开玩笑嘛,一个干部,如果心理素质不过关,光大大小小的会议都能把你给开疯了。我们党的干部,不管是好干部还是坏干部,有一点儿是非常扎实的,那就是心理承受能力,不然,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矛盾、复杂的人事关系、工作当中的焦虑感等等,承受能力那么差,早都跳N次水库了,还能等到竞争县长的时候才去自杀?
程小鸢的申诉材料,常安顺不知已经看了多少遍。程小鸢口述的那些内容,常安顺也听得耳朵快起茧了,但常安顺不表任何态度。他没有态度。因为他的态度不起任何作用,照样破不了案子,也帮不了程小鸢什么。程小鸢认为,是万盛公司的孟少爷想要衢水的一块地,沈阳没有答应,孟少爷就和分管党群的副书记合伙害死了沈阳,因为那个副书记也想当县长,而沈阳是他的有力竞争者之一。这只是推测,在法庭上,这样的推测不起任何作用。常安顺当了多年的纪检书记,不知经手办了多少案子,但没有一件案子是仅凭推测就下结论的,所以,他无法就程小鸢的推测表示什么态度。
常安顺有个类似于钻牛角尖的理论,他自己称为“强奸论”。所谓“强奸”,第一个前提,必须是在对方不情愿的暴力情况下进行的;第二个前提,必须是施奸者的那件物事已经入了港上了道——只有满足这两个条件,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强奸”,否则,只要那件物事没有入港,就只能算是“强奸未遂”。常安顺感兴趣的是第二个条件,他认为,办案子,也得跟“强奸”一样,入港,坐实了,办成铁案,任你有天大的本事也翻不过来,那才称得上是过得硬的案子。基于这个理论,常安顺过手的案子基本上没有任何悬念,该抓的抓,该判的判,该杀的,照杀不误。
沈阳的死,不是常安顺不想过问,而是没有办法过问,因为结论是公安局得出来的,他总不能无根无据地给人家推翻吧。没办法过问,并不表示他就不再过问。常安顺有他自己的策略,他分别从纪委和检察院各抽调了一名干部,安排他们去省委党校学习半年,这半年当中,不需要来单位上班,但却必须直接听命于常安顺。常安顺让他们干什么?秘密调查沈阳的死。一个副县长,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在水库里泡了半个月,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死了,这还了得?这还是不是共产党的天下?查,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但常安顺也清楚,沈阳的死有可能只是一根导火索,跟这根导火索紧紧连接在一起的,有可能就是一颗或者无数颗定时炸弹。这根导火索断了,啥事没有,你平安我平安大家都平安;如果你把这根导火索又拽了出来,还给点燃了,那么,有可能就是一场血肉横飞的爆炸。
程小鸢的推测不是没有道理,沈阳的死十有八九跟那块地有关系。去省委党校学习的那两名干部,在沈阳葬身的水库周围转悠了近半个月,终于在附近的一个村庄里找到一名目击者。据目击者说,沈阳出事之前,有两个人在水库边晃荡了两天,其中一个人是瘦高个儿,刀疤脸。沈阳出事的那天晚上,他还在自己所在村子的附近看见过他们,他们好像显得很匆忙,之后就再也没有看到过这两个人。巧合的是,孟少爷身边的打手里边,就有一个瘦高个儿的刀疤脸,但自从沈阳出事以后,这个刀疤脸就像从人间蒸发了似的,再没了人影儿。但这都不能证明什么。按照常安顺的“强奸”逻辑,就是男人的那件物事儿尚未“入港”。接下来,对孟少爷的调查就更离奇了。因为没有人说得清楚孟学非的生平。
孟学非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你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来,更不知道他有着怎样的身世背景。常安顺最奇怪的就是这点,他安排的人专门跑了一趟孟学非的老家,但秘密查访了整整一周,结果是查无此人,没有,压根儿就没有这个叫“孟学非”的人。奇怪了,这个孟学非哪儿来的,难道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万盛的孟少爷,凡是公开的属于他的所有档案信息,都是伪造的。也就是说,孟少爷把他跟自己出生地的联系生生给掐断了,同时也把自己的过去生生给掐断了。这是为什么?一个人,为什么要给自己伪造一个出生地,伪造一个身份,而把自己原本的身世隐瞒起来呢?是不想让人知道,还是经历过刻骨铭心的大悲大痛,伤心往事不堪回首?这些都是谜,就跟沈阳的死一样,也暂时还是个谜。
常安顺安排人秘密调查沈阳的死和万盛的孟学非,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市委书记刘定国和市长万长卿。他下达的办案纪律是,知道这件事的,除了他和两名调查案子的人以外,再不能有第四个人,一切都处于地下状态,调查案子的两名干部直接对他负责。程小鸢就更不能告诉了,常安顺认为,大部分女人都是智障,短脑筋,会坏事的。
万盛的孟学非,在雎阳的根系并不复杂,但你就是搞不清楚,他是怎么发达起来的,就像一棵树,凭空长成了参天大树,没有过程,没有根由,促使他生长的是什么样的土壤,施用的是什么样的肥料,你一概都搞不清楚。他就是雎阳的一霸,到处是他的产业,违法的、不违法的,都有。万盛的主营业务是房地产和酒店,另外,万盛还有一家大型洗浴中心,里面卖淫的、赌博的、抽海洛因的,齐备了。据说孟学非在自己的别墅里就养着一大批女孩子,个个国色天香,说是要学古时候的皇帝,三宫六院,夜夜笙歌。这个孟学非,也是胆大妄为到了极点,吃喝嫖赌不说,还曾经在大庭广众之下把一个小矿老板的轿车撞成了一堆废铁,最后竟然大大咧咧地说要把自己的悍马车赔给人家。这样一个在雎阳地面上无法无天的人,竟然没有人敢管他。常安顺很奇怪,在奇怪的同时,也多了一份谨慎和小心。他知道,孟学非这样的人,你轻易不能动他,弄不清楚他的底细,坐不实他的犯罪事实,你动他只能给自己徒惹一身骚,屁事不顶。
还有两件事情是常安顺吃不准的:一件是市长万长卿在孟学非开发的水榭花苑里有一套别墅,产权是不是在万长卿的名下他不清楚,反正万长卿偶尔会去那儿住个一天半天的,十分隐秘,几乎很少有人知道这件事——水榭花苑的别墅,动辄几百万一套,万长卿哪来那么多钱?要不,就是某个朋友借给万长卿居住的,但又不像,市政府给万长卿安排了房子,难道他万长卿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需要另建一个秘密巢穴?另一件事情,就是市府办的主任李文韬有一次很神秘地来找他,出示了两张各五十万元的入款凭据,李文韬把这一百万元均转入了纪委开设的廉政账户。这钱是哪儿来的?谁送的?送给谁了?显然不是送给李文韬的,李文韬还够不上别人给他大笔行贿的分量。
显然,收钱的人不敢不收,收了又怕出事,只好安排李文韬出面把钱存进了廉政账户。李文韬来找他的意思,是要常安顺以纪委的名义出具一个证明,证明这笔钱存进了廉政账户,并严格保密,不能有常安顺之外的第二个人知道。李文韬不说他身后的那个人是谁,常安顺也就不再过问,每个人都有不得已的苦衷,更何况,即使他知道了是谁送的钱,知道了是送给哪个领导的,又能如何?去查,能查出个什么来呢?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他常安顺知道得越多,就越麻烦。这两件事情,究竟跟万盛的孟学非有没有关系,常安顺不知道,但这两件事情如同两锭秤砣,沉甸甸地压在他的心口上,让他时不时地喘不过气来。他坚信,任何事情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他也坚信,举头三尺有神明,上天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但水落石出的这一天,究竟是什么时候呢?
程小鸢每天按时来常安顺的办公室里静坐,也不闹腾,更不干扰常安顺的正常工作,只是安静地坐在常安顺对面的沙发上,痴呆呆地,可以很长时间动都不动一下。常安顺批阅文件、读报纸、跟人谈话、安排工作,程小鸢一概在旁边坐着。时间长了,常安顺也就习惯了,该干吗就干吗,偶尔加班,秘书去买盒饭,也会给程小鸢带一份儿,这个时候,程小鸢往往不客气,接过来就吃。看她大口吞咽满脸心思的架势,常安顺就知道这个女人压根儿就没有吃出饭菜的味道来,吃饭已经成了她的机械动作,就跟钟表一样,走到了那个点儿上,就该上上发条,拧拧紧什么的。下班了,常安顺往外走,程小鸢也就往外走,很准时。有时候,常安顺来办公室迟了,程小鸢就在常安顺的办公室门口靠墙站着等他。
偶尔,程小鸢也会给儿子打个电话,就用常安顺办公桌上的电话打。程小鸢的儿子17岁,读高中一年级,沈阳出事以后就送到了程小鸢的娘家,由孩子的外婆照看着。程小鸢跟儿子通电话,轻声细语的,嘱咐儿子天冷了,一定要穿暖和一点儿,要听外婆的话,外婆年纪大了,不要惹外婆生气,要好好学习,给自己的父亲争口气……
常安顺听得心里就有些发酸。这时候的程小鸢,是属于一个孩子的母亲,属于一个母亲的女儿,不管她走到哪里,不管她的内心蕴藏着多么大的悲伤、多么大的冤屈,始终都有两根亲情的线在牵引着她,一个是养育她的母亲,一个是她十月怀胎生下来的儿子!
电话打到最后,程小鸢无一例外地会说,儿子,放心,我会给你的父亲讨一个公道回来的,会的,一定会的。
她说着说着,就会哽咽起来,大颗大颗的泪滴顺着脸颊滑下来,落在常安顺的办公桌上,像是在无声地抗议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