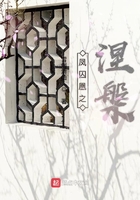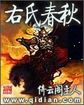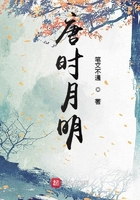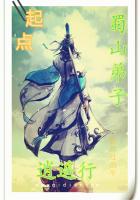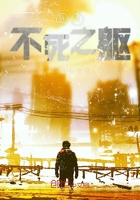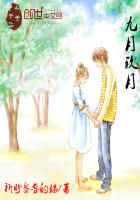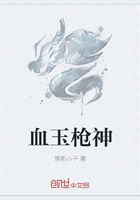当初,后梁与后唐征战,李存勖建立后唐,多次被后梁打击,是李嗣源带着骁勇的“横冲都”和众多“鸦军”,辅佐李存勖,争得了天下。当年李嗣源大军率先进入后梁都城开封,安抚城内军民时,李存勖得以顺利进城。后梁的百官开始跪拜李存勖,李嗣源也出来迎接,并祝贺唐帝灭梁。史称“帝喜不自胜,手引嗣源衣,以头触之曰:吾有天下,卿父子之功也,天下与尔共之”。后唐帝李存勖喜不自胜,用手拉着李嗣源的战袍,用头撞了一下李嗣源之后说:“我有天下,是你们父子二人的功劳啊!我要和你们共同享有天下!”
李嗣源灭后梁,进入开封城。曹彬灭南唐,进入石头城。功勋相近,但李存勖“喜不自胜”,扬言要跟功臣“共享天下”;而赵匡胤初则想着士庶罹祸,感泣流泪,接着是收回当初要封赏曹彬“使相”的承诺,并没有“喜不自胜”的心态。想起生命受难而感同身受、转念爵位收放而气定神闲,这之中,自有他人不及处,这就是格局。
首先慧眼勘透个中隐秘的,是王夫之。
《读通鉴论》有一段精彩议论,是智者真知,值得品鉴:船山王夫之认为,大人物做事,做成了能够持守而不败,做败了能够坚守而不亡,这之中,最大的可能是“存乎其量之所持而已”,存在于他的“量”所能够持守的东西而已。这里说的“量”,在我看来,就是格局。这类格局,与“智谋”之类无关。用船山先生意见,智谋,不过是“心之用”,而“心之用”最终要用到“体”。体用关系中,体是根本。“量”或“格局”就是“体”。这是人的根本。有这个根本,成事可受,败事不亡。因为格局在那里。无此格局,则虽成必败,败则必亡。船山以李存勖、楚霸王、汉高帝、宋太祖四人故实来说这个道理。
李存勖、楚霸王都是战而必胜的人物。但李存勖胜利之后,喜不自胜,楚霸王失败之后,一蹶不振。李存勖此前多次失败不怕;楚霸王此前多次胜利不骄。这俩一个能忍受失败,一个能忍受胜利。但一个是赢不起,一个是输不起。李存勖赢一次就要跟人“共享天下”,楚霸王输一次就要宣告“放弃天下”。这都是“量”不足也即“格局”不大的缘故。
汉高祖则多次失败,而神色不怵;宋太祖则多次胜利,而不沾沾自喜。反之亦然。胜与败,在刘邦和老赵那里都是程序中的章节,那都是理当翻阅的前篇,没有什么力量能够让他们惊慌失措或进退失据。所谓生死成败,都流转于“时势”之中,有格局者自可坦然承受,“其不动也如山,其决机也如水”,这就是所谓“守气”。能够“守气”而不为成败所动,即使只有百里之地,也可以“观诸侯、有天下,传世长久而不危”。这是那种仅凭匹夫之勇,无能接受胜败的人不能理解的。王夫之认为:“豪杰之与凡民,其大辨也在此夫!”豪杰人物与凡庸之人,其间的最大差异,就在这里啊!
王夫之看出了李存勖与李嗣源“共享天下”的“量”之狭隘,也即“格局”规模之小,但他没有说,之所以有此格局,是因为“私天下”之故。李存勖将天下视为“私有”,得之而与人“共享”。而赵匡胤则将天下视为“大公”,因此得之,而论功行赏,没有那种坊间常见的“有福同享”之江湖习气。以此来考五代十国,各藩镇之“犒军”“赏赐”,正是视天下为“私有”的积习。老赵有国之后,认“天下为公”之理,故心态大变。所有封赏不仅以功勋而定,更据时势而行。这就是他暂时不想封赏曹彬“使相”的深刻原因。曹彬,还需要继续为国家(而不是为老赵)建立功勋。
在老赵心目中,诸位,你们都是在为天下干活儿,不是为我老赵干活儿!我老赵不过是代为管理这个国家的最高首领而已。老赵的“格局”已经远在五代乱世诸君之上了。这也是他能够得到文武推崇,而心无二志的原因。他的格局让人信服而心服。
曹彬也不是凡人。
他从江南回来时,按规定要到官署报到,他递上的名片写着:“奉敕差往江南勾当公事回。”
这话用白话说就是:“奉皇上诏令,到江南出公差干了一趟活儿回来了。”字里行间看不到有那种可立了大功的感觉。他不自我表彰。史称“时人嘉其不伐”,时人对他不自吹自擂很是钦佩。此案可见,曹彬确有名士之风。这类人物,永远很少、很少。
老赵与曹彬,正是传统所谓“君臣际会”的人物。难得。
李煜死因成谜
李煜后来之事,也是坊间乐于谈论的话题。一般认为,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李煜被宋太宗下“牵机药”毒害,终年四十二岁。但此事正史不载,我也不认为此事为真。
所谓“牵机药”,据说与中药马钱子有关。据说主要成分是番木鳖碱和马钱子碱。说当初流行有“鹤顶红”“钩吻”和“牵机药”等几种著名的毒药。说“牵机药”服后,“服之前却数十回,头足相就,如牵机状”。就是两手两脚,一会儿张开,一会儿抓起,头部和足部相就,如弯弓状。不断做这个动作,如仰卧起坐。这就是现代医术描述的“抽搐”“强直性惊厥”之类。是中毒的症状。
据说皇宫内设有毒药库。据蔡绦《铁围山丛谈》记载,宋徽宗践祚时,曾骑着马巡视大内诸司务,在曲里拐弯的一个地方,对着后苑东门,有一库无名号,但谓之“苑东门库”。一问,才知道是贮藏毒药之所。有外官一员与大内官员共同监管。毒药都是从两广、川蜀进贡而来。说每三年一贡。药有七等,“野葛”、“胡蔓”都在其间,传说中的“鸩”,按其毒性,才排在第三位。毒性最大的据说“鼻嗅之立死”。宋徽宗于是亲笔写了诏书说:
取会(核实)到本库称:自建隆以来(毒药)不曾有支遣(取用)。此皆前代杀不庭之臣(所用)。藉使臣果有不赦之罪,当明正典刑,岂宜用此?可罢其贡,废其库,将见在(现有的)毒药焚弃,瘗于远郊,仍表识之(要在焚烧的地方竖立标识),毋令牛畜犯焉。
核实到本库报告:自从建隆年间以来,毒药不曾有过取用。这都是大宋建国的前代朝廷专门用来杀犯有罪恶的大臣所用。但即使大臣真的有不赦之罪,也应该明正典刑,岂应该用到这种东西?可以终止这种进贡,废掉这个仓库。将现在所有的毒药焚毁丢弃,但要在远郊去烧埋,还要在焚毁之地竖立标识,不要叫牛马畜生等沾上毒药。
这事证明:宫中确有毒药,但自从大宋开国建隆以来,就不曾用过。据宋王铚《默记》记载,说徐铉归附大宋后,为左散骑常侍,迁给事中。太宗赵光义有一天问他是否见到李煜,徐铉说:“臣安敢私见之?”太宗说:“卿但去见,没关系。就告诉他是朕让你见他好了。”
徐铉于是就到李煜居所去见故主。见一老卒守门,徐铉说:“愿见太尉。”他称李煜为太尉,是因为李煜被封为“右千牛卫上将军”,算作一种誉称。老卒说:“有旨,不得与人接,岂可见也。”徐铉说:“臣奉旨来见。”老卒进门去汇报。徐铉立在庭下很久,然后看到李煜“整衣冠”后,穿着纱帽、道服出来了。徐铉赶紧在阶下跪拜,李煜过来拉着他的手坐到宾客席位。徐铉不敢,继续行君臣之礼。
李煜说:“今日岂有此礼!”
徐铉只好将椅子挪动偏一点,这才敢坐下。李煜与他谈论间,不禁大哭,徐铉默不作声。李煜忽然长吁叹道:“当时悔杀了潘佑、李平!”徐铉离去后,太宗有旨召对,问他后主李煜说了啥话。徐铉不敢隐瞒。据说正是因为李煜这句话,惹恼了太宗,遂被“赐牵机药”。
又说后主李煜在府邸第七个晚上,命故妓作乐,闻声于外,太宗闻之大怒。
又传李煜“小楼昨夜又东风”、“一江春水向东流”之句,也让太宗不爽,等等,因此被“赐死”。
更有传说小周后,随后主归朝,封郑国夫人,循例随命妇入宫。每次进入宫中就要好几天才能出来,每次出来,必大哭大骂李煜,声闻于外,后主多宛转避之。还说李煜给金陵旧宫人写信,其中有“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字样。
更神奇的是江湖还流传有宋太宗强奸小周后的画图,还有各类题诗,如“北征他日记匆匆,无复珠翘鬓朵工;一自宫门随例入,为渠宛转避房栊。”如“江南剩得李花开,也被君王强折来;怪底金风冲地起,御园红紫满龙堆。”仿佛亲见一般。但一考察诗画来源,原来都是元人干的活。这就更不可信了。
太宗赵光义,也是一了不起人物。他不像坊间流传的那样好色。所谓调戏花蕊夫人、强幸小周后,都是子虚乌有的段子。《宋会要辑稿》“崇儒”篇记载:太宗淳化四年七月二十四日,雍邱(今河南杞县)县尉武程根据自己想象,皇宫中不定多么豪奢呢!就上了一道疏,说要请皇上减少后宫的嫔嫱。
太宗看后,对宰相说:“这位武程,一个疏远的小臣,对宫中事一无所知。现在内庭给使不过三百人,一个萝卜一个坑,都有自己的活儿要干,再也不能减少了。朕视妻妾就跟鞋子似的,就恨不能离世绝俗,追踪佛门或去学仙啦!朕岂能学秦皇、汉武,作离宫别馆,取良家子女以充其中,留下万代的嘲笑讥议?外间不知,卿等实在应该知道这些事。”
李昉等奏对道:“臣等家人朔日、望日,都朝集到禁中,很清楚地知道宫闱中的简易、俭朴之事。这个武程,官职很小,却敢如此妄言!应该加以贬黜!”
太宗道:“朕岂能憎恶他的言论?但念其不知尔!”我岂能憎恶他的言论,跟你说这个事,不过是因为他不知道宫中事罢了。
《续资治通鉴》也记录了这件事,太宗回答李昉的说法是:“朕曷尝以言罪人!但念程不知耳。”朕什么时候因为他人言论而加罪于人?我只是想到武程不知道内情罢了!
武程终于没有被处罚。李煜死后葬在北邙,小周后死后,与李煜合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