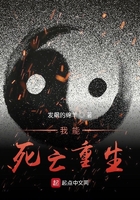老莫人聪明,他会双手打算盘,很早就会油归篓篓归罐、鸡兔同笼的数学题。这些年,老莫凭着这份聪明挣下几十万家产。在皮县,也算是富人阶层了。可老莫从来没有成功的喜悦,他总是一个失败者,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源就是乔月。老莫完全有条件背着乔月、甚至抛开她寻找一种刺激的活法,和乔月扯平。钱不是主要因素,就是没成为老板之前,老莫也有过“红杏出墙”的机会,比如和刘万年女人。
刘万年女人在场院里将老莫羞辱了一番之后,并不甘心。只要和老莫照面,她就堵住老莫,一遍一遍责骂老莫,骂他不是男人,为什么不把乔月一刀捅了。案犯是刘万年和乔月,她却把火撒到老莫身上,弄得老莫一出门,总是东瞅西瞧,生怕刘万年女人从什么地方钻出来。而刘万年女人就像鬼魂,总能给老莫个措手不及。
有一天,老莫起了个大早,他想割些柳条编个筐。他在树林间穿梭,割得差不多了,坐下来抽烟。他庆幸刘万年女人没跟来,这个娘们儿,赶上刘万年可恨了。一支烟没抽完,老莫闻见一股奇异的味道。他一回头,吓了一跳,站在他身后的竟然是刘万年女人。她的神情得意而挑衅,如果不是她嘴角浅红色的痣,老莫还以为遇见了鬼。不,她已经是魔鬼了。老莫想站起来,刘万年女人拍了拍他的肩,示意他坐着。
老莫横下心,她能怎么着?
刘万年女人反而笑了,老莫,你躲着我干吗?
老莫瞥了她一眼,谁躲你来?
刘万年女人温和地说,你别嘴硬,你就是躲着我了。
老莫折了截柳条塞进嘴里嚼着,我惹不起,躲还不行?
刘万年女人说,我今儿不和你闹,我就没见过你这样的男人,你的心也太好了。
老莫受了愚弄似地,脸涨红了。
刘万年女人不管不顾地说下去,乔月是个没良心的女人,不是你,就她那猪头芥疙瘩,到今儿还在家里老着呢。脸盘子一光就给你戴帽子,你咋咽得下这口气?换了我,我早杀了她。
老莫硬梆梆地顶回去,你咋不把刘万年杀了?
刘万年女人的表情跳了几下,绷成一张变形的弓,你真上不了台盘,到了这个份上,还护着她,她能和刘万年比?刘万年是她勾引坏的,过去,刘万年没这毛病。
老莫说,都不是好东西。
刘万年女人的声音大起来,你说得没错,都不是好东西,可我是女人,你是男人,你怎么就不耍点儿横的?说着刘万年女人就控制不住了,难听的话一句接一句往出蹦。你为啥不杀了乔月?你舍不得她?你是不是侍候不了她?你肯定侍候不了,要不她咋狗一样乱窜?你肯定阳痿,你的东西是泥捏的,是废物!
老莫终于被她激怒了,他像一只怪兽,张着大嘴扑过去,将刘万年女人扑倒在地上。
老莫想把这个女人撕碎、咬烂。可突然之间,老莫僵在那儿,刘万年女人将他抱住了,她的鼻孔几乎挨住了他的脸,热烘烘的气息扑过来,熏着老莫的眼睛。老莫的思维凝固了,老莫第一次和乔月以外的异性如此亲近地挨着。老莫探出手,刘万年女人眼里充满了热望和鼓励。可是,老莫胆怯了,他松开刘万年女人,慌慌张张站起来,狼狈不堪地逃了。
刘万年女人在身后吼,你占我便宜,我和你没完。
老莫跑回家,心依然狂跳不止。老莫等待刘万年女人上门算帐,可刘万年女人一直没来。奇怪的是,自此以后,刘万年女人不再纠缠。偶然碰面,不是老莫躲她,而是她躲老莫。
局面就这样发生了变化。
十几年后,老莫在夜幕的掩护下将数目不多的一卷钱塞给刘万年女人时,他常想起多年前那片树林里的事。刘万年女人凶是凶了些,可她也够可怜的。老莫用他的自卑和胆怯赢了她。不可否认,老莫的善举含着旧年的一份歉意。
可老莫并不后悔,以老莫当时的身份和地位,谁晓得会有什么后果?村子里,没一个人把老莫放在眼里,他怎么可能放纵自己的欲望。
老莫就像一粒灰尘,总是被人忽视,甚至包括他的儿子莫小有。作为一个父亲,老莫一直努力改变着自己在儿子心中的形象。老莫的努力像是堆砌肥皂泡,看起来山一样高,可轻轻一吹,便化作乌有。
莫小有是老莫最得意的成果。如果不是莫小有的个子窜到一米七五,他就是一个活脱脱的老莫。除了个子,莫小有的脸盘、眉眼、牙齿,甚至走路的姿势都和老莫一模一样。当然,莫小有的性格和老莫截然相反,莫小有不管不顾,野性十足。如果不是相貌的相像,没人相信这是老莫的孩子。莫小有总算给老莫撑了回腰。
老莫最初意识到莫小有的威胁还是他刚懂事的时候。有一天,莫小有玩耍回来,说孩子们叫老莫泥头,他问老莫泥头是么意思。老莫脸红了。他无法回答莫小有,而是勒令莫小有少出去玩。老莫不可能把莫小有拴在家里,莫小有像猴子一样,能从窗户窜到墙头上。莫小有很快知道了那两个字的含义,他渴望老莫替他出口气,哪怕找人干一架。老莫摆着父亲的架子,黑着脸教训莫小有好好读书,小孩子家别管大人的事。不久,莫小有和一个孩子干了一架,将对方打得头破血流。孩子的家长找上门,老莫赔了许多不是。老莫没问莫小有为什么打架,将对方打成这样,总是理亏。等人走了,老莫才回过头。莫小有冷冷地望着他,满眼的轻蔑。老莫极不舒服地抽了一下,他黑着脸说,打坏了,就得给人家花钱,你咋这么野?莫小有呸地吐了一口,大声说,我看不起你,你个泥头。呼得一声,血液冲上了老莫的头顶,他扬手给了莫小有一个嘴巴。莫小有并不躲避,更加大声地喊,我看不起你。老莫没有再打下去。莫小有是个倔犟的孩子,老莫无法改变他。从那个时候起,莫小有和老莫的关系就淡了。
老莫想,错的是乔月,莫小有应该把矛头对准乔月,可莫小有和乔月一直很好。
进城不久,老莫第二次提出离婚。乔月没像上次那样以死威胁,她搬出了莫小有。
那时,莫小有已是高中生了,唇上生出了淡淡的绒须。
莫小有替母亲与老莫谈判。
莫小有问,为什么离婚?
老莫说,你问你妈,她清楚。
莫小有说,我问的是你,你是男人,这个问题你应该回答。
老莫火了,“男人”这个词他听得太多,都过敏了。老莫说,你凭什么和我这么说话?
莫小有说,你别当我是你儿子,我现在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调解你们的事。
老莫说,你甭调解,我受够了。
莫小有说,那就说出你的理由吧。
老莫怎么能说理由呢,这是打自己的耳刮子。老莫说,你又不是不清楚。
莫小有咄咄逼人地说,我就是不清楚,你不说我怎么会清楚。
老莫说,我没得说。
莫小有问,没得说?没得说就要离婚,玩潇洒啊?
老莫生气了,你审问我呀。
莫小有说,你不是没得说,是不好意思说,不好意思,说明你心里有愧。
老莫冷冷地将脸扭开。
莫小有却教训起老莫来,这么大岁数了,你折腾啥?我知道你心里别扭,十年前就知道。一个男人没能力保护自己的女人,却将责任推到女人身上,可笑!这算什么男人?为什么你过去不离?不就是有了点儿钱吗?你也就是有俩钱,时髦不是谁都能赶的。
瞧瞧,这就是儿子和父亲的对话。
莫小有说话的腔调和口吻就像是训斥一个拙劣的学生。老莫撑不住了,心说你吃老子,花老子,还口口声声教训老子,他陡地站起来,说,我离定了。
老莫当然没离成。莫小有的威胁起了作用,他说他要离家出走,永远不回来。不管莫小有怎么瞧不起他,老莫却是疼爱他的,这毕竟是老莫唯一的成绩。
莫小有大学毕业,分到了市里。参加工作后,莫小有和老莫的关系有所改善,他眼里的冷淡和轻蔑少多了,看老莫的眼神也温和了。可内心深处,莫小有和老莫还是有隔阂的。比如分配的事,比如谈女朋友的事,比如买房子的事,他只跟乔月说。需要钱也不向老莫开口,钱都乔月管着,老莫成了纯粹的挣钱机器。
有一件特别堵心的事,老莫至今羞于跟人提起。
莫小有刚结婚时,住了单位一间宿舍。老莫去市里办事,在那儿住了一夜。莫小有妻子和莫小有一个单位,都是搞统计工作的。莫小有妻子还算热情,炒了几个不错的菜。老莫喝酒时,她不时地拿起酒瓶,给老莫斟酒。受这样的礼遇,老莫有些受宠若惊。
由于天晚,老莫没法回皮县。吃完饭,老莫站起来。屋子里就一张床,老莫得找个住处。莫小有妻子却让老莫在家里住,说有一张钢丝床。外面住肯定自在些,只是莫小有妻子一再挽留,老莫也就不好硬坚持。
睡下没多久,一阵轻微的声音传到老莫耳里。老莫闭着眼,可老莫知道这是什么声音,脸顿时烧红了。老莫生气地想,他们就这么急,一夜工夫都等不及了。老莫真想起来,摔门离开。可他们不顾及老莫的面子,老莫却不能不顾他们的面子。老莫还听见了两人的对话。
莫小有的妻子问,睡着了吗?
莫小有说,肯定睡着了。
莫小有妻子说,小声点儿。
先前,声音还小些,可很快声音就大了,一浪一浪地撞过来。老莫被这声音煎熬着,痛苦万分。说穿了,这并不是莫小有控制不住,而是他无视老莫的存在。五更时分,老莫悄悄地离开了。
老莫是父亲,虽然儿子不拿他当回事儿,他却舍不得儿子。莫小有把他和乔月紧紧地绑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