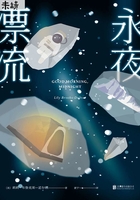他的重重的脚步声消失在沙沙的雨夜里。像一个理直气壮的强盗洗劫之后又招摇而去。
那时柴姑还没有睡,正站在临窗的地方往黑夜里看着什么。她听到了那座草屋里的一切声音,也看到了小喜子大踏步走来又大踏步而去的身影。他让她想起那个从不理睬她的老大,突然从墙上摘下鞭子,狠狠地抽在窗棂上。
她听到草屋里茶的抽泣。
大约就是在那个雨夜,也许是另外一个雨夜。草儿洼发生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事。小喜子回到羊圈时发现栅栏被什么撞得东倒西歪。他急忙燃起一个火把,地上躺着几十头被什么咬死的羊,有的肠子流了一地,到处是血。其余的羊惊恐地拥挤在一个角落里,头羊“撞倒山”和另外几只公羊一反平日的争斗,齐刷刷站在群羊之首,不时愤怒地前腿扒地,也是遍身血迹。显然,它们刚刚联手和入侵者进行了一场殊死搏斗。
小喜子大吃一惊,本能地操起一根棍子环顾四周。他不知道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发生了什么事,更不知是谁干的。小喜子弯腰拍拍几只公羊。“撞倒山”像是受了天大的惊吓和委屈,把角抵在他手掌上轻轻摩擦,发出一阵低低的哀叫。骚动的羊群看到小喜子已渐渐安静下来。小喜子越发不好受。他离开羊栅栏,瞪大了眼往黑夜里搜寻,什么也没发现,气得跺脚一阵狂叫:“狗杂种!……我操你娘!……”
羊栅栏距草儿洼约有半里路,和江伯的大牲口圈靠得很近,当初是为了放牧方便才这样设置的。叫声先是惊动了早已沉睡的江伯,不大会儿柴姑、老佛和一群伙计都赶来了。大家举起火把重新察看羊圈,柴姑一进去就嗅到一股陌生而又熟悉的气味:“狼来过。”
“狼!……”
大伙都惊慌起来,纷纷往里靠拢。
江伯说:“柴姑你弄错了吧?咱这一带已有几百年断了狼迹啦,咋会有狼呢!”
大伙都疑惑地看住柴姑,这可是个很坏的消息。
柴姑又嗅了嗅:“不会错,刚才来了少说有十几条狼!”
她太熟悉狼的气味了。自小在深山里和荒狼打惯了交道,没有荒狼相伴的日子曾让她极为空虚。柴姑对狼的熟悉远远超过对羊的熟悉。
众人骇然,不知她为什么断定是狼而且不下十几头。
柴姑却兴奋得直搓手。被狼咬死那么多羊,她居然一点也不心疼。狼来了,真好!
但柴姑同样纳闷的是,这里绝迹几百年的狼,又从哪里冒出来的呢?
其实最先发现狼群的是白羲。
白羲已在荒原上晃荡了十几天。这是离开老大最长的一次。它觉得无聊极了,没有任何事情要干,和老大守在一起像两个光棍。它不知道老大为什么那么沉默不语。它非常喜欢柴姑,柴姑每次来,它都要摇摇尾巴,走过去卧在她的脚下,任她抚摩,她的手轻轻的,身上有一股好闻的气味。那股好闻的气味让它产生一种不安的骚动。柴姑走了,白羲便站在大堤上目送很远,然后回头看看老大。它希望他把她留下来,可老大头也不抬。渐渐地,白羲便对老大生出一点稀薄的怨气。它并没有表现出什么明显的不满,只是外出的次数增多了。
那晚它卧在一丘荒岗上,无精打采观看闪动的星光,渐渐有些瞌睡。夜风潮水一样涌来,忽然有一股不同于荒原的腥臊味。开始它不曾留意,但那股臊味越来越浓,刺激得鼻子有些发痒。白羲忙抬起头,耸起耳朵四下观望,星光朦胧中,除了随风起伏的荒草,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但它知道肯定有什么事要发生了。它把嘴贴住沙丘,两耳立刻感到大地轻微的震颤。震颤极其细微,就像一大群蚊虫掠过,空气中发出的颤动一样,但不是蚊虫迁徙。蚊虫迁徙多在黄昏。而那声音确凿地从地上传来,那么就只能是兽蹄踏地的声音,凭经验,白羲估计兽群还在十里以外。
白羲不能等闲视之了。它相信荒原今夜潜进了凶猛的野兽,而且很多很多。凭气味,它断定自己遇到了强大的对手。这使它感到恐怖,又令它极其兴奋。白羲多年来并没有遇上过真正的对手,它一直感到不够劲。众多的狐狸、兔子、野狗之类,只是它追逐的对象。在白羲面前,它们都是弱者,而懦弱的对手是不能造就强者的。强者是强大的对手造就的。它似乎一直在等待这一天的到来,它的富有弹性的细腰,它的宽阔的前膀,它的四蹄生风的奔跑速度,它的雄健的体魄,都是为敌人准备的。在这之前的一切追逐、搏斗、潜伏,都不过是一种演练。白羲一跃而起,稳稳地站住了,伸开四条腿,使劲抖了抖毛,身上的沙土射向周围的荒草,打得沙沙响。这有力度的声音让它感到满意。它知道荒原再不会平静,在今后的日子里将有无数次的厮杀在等着它,那将是充满凶险的真正的搏斗。
腥臊味越发浓重了,如毒雾般顺风飘来。白羲本可以暂时躲开,但它没有,它要察看清楚它未来的对手究竟是什么样子,它们究竟有多少。远处的草丛渐渐骚乱起来,躲在里头的兔子、野狐、黄鼠狼以及成群的鸟,显然已经被莫名其妙的臊气弄得惊慌失措,有的已开始顺风逃窜,鸟儿在黑暗中惶然飞起,不时发出一阵阵噪叫。白羲顿时有一种临战的兴奋,它用后腿蹬起一丛沙土,纵身跃下荒丘,迎着腥风涌来的方向悄然奔去,两旁的荒草无声地分开,如鱼儿入水般潜进夜色中。
白羲在草丛中潜行了约有七八里,前头便是漫河。它已清晰地嗅到狼群的气味。白羲不敢弄出一点声音,慢慢爬过一道沟壑,伏在高岗的草丛里往下窥探,下头漫河的情景顿时让它心惊胆战:黑压压一片群狼足有上千头,正静静地坐在草地上举头望星。河坡上一匹花狼人立着,冲狼群发出或长或短的叫声。在它周围,护卫一样站立着十几头看上去十分强健的狼。
花狼显然是匹头狼。
白羲忽然十分伤感。这凶残的异类竟有如此强大的部落,而羲犬家族却年复一年地衰落,以致在荒原上找一个同类都相当困难了。
它终于确认这是一群野狼。
白羲并没有见过狼,它是凭血脉中遗传的记忆识别出它们的。自古至今,羲犬是狼群的天敌,曾经强大得令所有的兽类闻风丧胆。但为什么狼群之类的异兽们没有灭净,自己反倒形单影只了呢?这一刻,白羲突然涌出对羲犬灭绝的恐惧和极大悲哀。
是和人类靠得太近远离荒原失去了野性?
是过于孤高自傲自我封闭自生自灭?
白羲一时还无法找到答案。
但有一点它是清醒的,不论自己多么强大,想战胜这个庞大的狼群是根本不可能的。除了借助人类的力量,还必须有个合适的对策。
这时,狼群突然发出一阵惊天动地的嚎叫,似乎在欢呼什么。然后分成许多小群,从漫河里四散去了,很快消失在荡起的尘土和无边的草丛中。
要不了多少天,整个荒原将是狼的天下。
白羲感到无法言说的失落。
在那之后的好多天,白羲悄悄尾随在花狼后头。它打定主意,就是要跟定这匹头狼,伺机发动攻击。只要干掉它,就会使群狼无首。
但干掉它并不容易。它身边的十几条狼个个体壮凶猛,靠近花狼几乎是不可能的,白羲已经发现,花狼是一条母狼,它率领的十几条公狼,既是护卫,又是性伴和情夫。这实在是一条漂亮的母狼,细腰丰臀,身体长大,跑起来总在狼群前头。十几条公狼几乎跟不上它。它的头总是昂着,左顾右盼,对它身后的狼群则极少回头看一眼。它当然相信,它到哪里,它们就会跟随到哪里。它是它们的女王。
一般地说,狼总在发情时才需要公狼。可花狼不这样。它每天都要和公狼交媾一次。当它选中其中一条公狼交媾时,其余的公狼只能围成一圈观看,或站或卧,眼巴巴地看着它,不能靠近,也不能稍微表现出嫉妒和不满。否则,它会把你咬得遍体鳞伤。
每天的交媾几乎都在黄昏进行,连续十几天都是如此,这已近于仪式。完事后,花狼便在原地卧下睡觉。公狼们围在它的周围。这条风骚而骄傲的年轻母狼,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和近乎奢侈的生活习性。白羲猜想它成为这个庞大狼群的头狼,除了它的凶猛,大概还赖于它的骚情。没有哪条母狼甚至没有哪种兽类,能够在不发情期天天需要交媾。
它们暂时还没有什么目标。只是东游西转,熟悉荒原的气息。
黑马撞上这群狼完全是偶然。
这个令柴姑倾心而又神秘莫测的剽悍的年轻人,从来行踪飘忽,居无定所。没人知道他从哪里来,也没人知道他要干什么。
他似乎对一切都没有兴趣,又好像对什么都有兴趣。全要看他喜欢不喜欢。
他在荒原上到处走动。现在没有谁能比他更熟悉荒原的了。那晚月明星稀,他爬到一棵巨大的歪柳树上露营,这里显然曾是一个村庄,附近还有些断墙石磨什么的。大柳树曾被黄水连根拔起,冲出很远,然后又在这里落地生根。树身几乎平躺在地上,树枝却直着往上长,形成很多枝杈。荒原上所有存活的树都是往一个方向斜着的。
黑马斜躺在树杈上,猎枪挂在一旁。这时他突然坐起身,伸手拿住猎枪。他闻到了狼的臊味。他一下就闻出来了!
他对狼的熟悉决不亚于柴姑。
这时他透过树隙,已经看到狼群正朝树下逼来。
显然,花狼也嗅到了人的气息。但它还弄不清人在哪里。它们全都四肢弯曲,肚皮贴地,匍匐着前行。但还是弄出了声音。黑马看了好笑。他太熟悉狼群的这种伎俩了。他没想到荒原上会突然出现狼群。这让他极为兴奋和惊讶。
往后有活干了。
他并不害怕这群狼。他在树上隐蔽着,而且手里有枪。这是一杆很好的双筒猎枪,十几条狼不是他的对手。
花狼已经意识到潜在的危险。在离大树几十步的地方停住了。它相信这棵茂密的大树上藏着阴谋。花狼发出一个信号,有几条公狼又往前爬去。花狼仍伏在原地观察。
这时火光一闪,枪响了,“咣!”一片火光。枪声在沉寂的荒原之夜如一声惊雷,具有特别的震撼力。
这一枪是空枪,只有火药,没有铁砂。
黑马想和狼群开个玩笑。
爬在前头的几头狼被惊得翻个跟头蹿了回来,后头的狼被恐惧感染,顿时四散奔逃。
花狼却惊人地沉着,伏在地上没动。
白羲在后头远远地都看到了。它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放枪的人是谁呢?
突然黑马跳下大柳树,朝前走去了。
这时狼群又渐渐聚合起来。花狼对它们刚才的惊慌失措有些恼火,突然跃身扑向一条公狼,将它掀翻在地。然后尾随那个人影向黑暗中追去。
黑马似乎并不慌张,在前头走得不紧不慢。他知道它们会追上来。他就是要引它们追上来。他并不担心狼群会围上他。狼的秉性既凶残又多疑,在没有弄清情况之前,是不会贸然进攻的。刚才这一枪够它们吃惊并纳闷一阵子的了。
但黑马也知道它们不会放过他,这近乎戏弄的一枪肯定会惹火它们。这也许是狼群进入荒原头一次碰上人,而且只是一个人。
它们当然不能在一个人面前折了锐气,这很重要。
黑马在前头打了个极富挑逗性的唿哨:
“嘟——”
后半夜,当黑马把狼群引到柴姑的羊圈时,忽然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