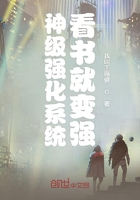八千块钱没能医治好继父,继父还是走了。这个代价太大了,但荞荞不觉得有多冤,反正她终归要嫁人的。杨来喜除了赌,她还看不出他有什么缺点。反过来说,他不赌哪来八千块钱?那些日子,杨来喜常往荞荞这儿跑。荞荞养了十五只鸡,每天至少下七八只蛋,但那一阵子,荞荞一个鸡蛋也没攒下,都被杨来喜吃了。荞荞挺心疼,可想想花了人家八千块钱,便把那种感觉踩在脚下。荞荞出嫁是在冬日,杨来喜要雇一辆四轮车,荞荞觉得奢侈,两村相距不远,她又没什么亲戚,一辆自行车足够了。那时,荞荞一点儿没意识到这么做对自己有什么不好。
婚后,荞荞才发现,杨来喜除了赌博,就是游手好闲,东家出西家进的。杨来喜说他是天生的赌手,完全可以靠赌吃饭。那几年,杨来喜赢的时候多,输的时候少,荞荞的日子确实可以。
杨来喜不是过日子人。输了钱自我安慰,赢了就胡吃海花,每次赌钱回来,杨来喜都让荞荞煮鸡。荞荞没什么嫁妆,那十五只鸡是她唯一的陪送。荞荞心疼,可耐不住杨来喜的软泡硬磨。杨来喜本来就瘦,加之常常熬夜,现在房事上又没有节制,快瘦出骨头了。荞荞怕别人说她放浪,吃鸡好歹也能补一补。杨来喜做的任何一件事,荞荞都要替他找个理由。那个冬天,十五只鸡被杨来喜吃得连毛都没剩。
荞荞从小就孤僻,结婚后,仍然不爱往人堆里钻,除了干活,几乎足不出户。要说交往多的,也就是春喜媳妇了。荞荞觉得春喜媳妇不错,嘴甜,人也热情。可有一件事彻底改变了荞荞的看法。一年春节前,春喜媳妇和荞荞去镇上买布。荞荞一进市场,便吸引了许多目光。荞荞很不自在,那些目光罗着她,走路都绊脚。春喜媳妇打趣道,你可要小心点儿,男人们想活吃你呢。荞荞捶了春喜媳妇一下,脸越发红了。荞荞低头看一块儿布料时,一个妇女小声问春喜媳妇,这是谁呀?上海来的吧?春喜媳妇瞄了荞荞一眼,小声道,是我小叔子买来的,别看脸蛋儿俊,连孩子都生不出来。尽管声音小,可荞荞一字不落地收进了耳朵。荞荞的腿一下抖起来,卖布的人问她什么,她傻子一样。荞荞明白了,不只春喜媳妇这么看她,她代表的是整个围子的看法。在别人眼里,她是卖掉自己的女人,是贱女人。荞荞想起了她出嫁时简简单单的样子,包括乘自行车,都是她贱的证据。荞荞不知自己错在哪里,她变得越发孤僻了。
好在杨来喜不这么看她,包括她生不出孩子,杨来喜都没责怪她。杨来喜从来不提这件事,好像荞荞生不生孩子,与他无关。有一次,荞荞装作无意的样子说,咱们该有个孩子了。杨来喜说,是呀,该有个孩子了。荞荞试探着说,去医院检查一下?杨来喜说,检查啥,不生也好,有你我就知足了。明知是杨来喜油腔滑调,荞荞还是很感动。
杨来喜的新鲜劲儿过了,夜不归宿就成了家常便饭。有一天夜里,刚睡下不久,荞荞就听到了窗外的动静,头皮都乍起来了。荞荞屏息敛气,等待窗外的人离去。外面的人不但没走,竟轻轻地敲起了玻璃。荞荞没敢说话,那个人就执着地敲下去。敲一下,荞荞的心就咚得跳一下。后来,她干脆蒙住头。那一夜,她的冷汗几乎把被子湿透。
次日,荞荞刚吃过早饭,村长来了。村长先问来喜在不在,然后大模大样地坐在椅子上,打量着屋子的摆设。荞荞倚在门框上,很拘束。村长说,荞荞,怎么连杯水也不倒?荞荞忙沏了一杯茶。村长的目光探过来,很放肆地摸着她。荞荞脸红了,问村长找杨来喜有什么事。村开哦了一声,从怀里拽出一张表,让荞荞填。那是一张未生育妇女登记表。荞荞再缺少常识,也知道这种工作该由妇联主任做。荞荞要填,却没笔。村长说我这儿有,给荞荞递补笔时,轻轻碰了碰荞荞的手。荞荞早从春喜媳妇那儿听说了他和二香的事,心存戒备,想急着填完,打发他走。荞荞填完,村长拿在手里,左右端详着,似乎那是一件艺术品,嘴里没忘了啧啧,字还不错,比杨来喜有文化,真是一朵鲜花……村长及时打住,荞荞却听懂了村长的意思,心尖锐地疼了一下。村长出门的时候,不知怎么绊了一下,荞荞下意识地伸出手,村长乘机在她身上抓了一把。荞荞冷了脸,村长哈哈一笑,搓着手走了。
杨来喜回来后,荞荞没敢告诉他。荞荞想把它埋在肚里,悄悄烂掉。可杨来喜不在家的时候,村长又来过几次。村长的屁股像是粘了胶,死坐着不走,说一些不着边际的寡话,瞅机会在荞荞身上揩点儿便宜。荞荞害怕了,便对杨来喜说了。荞荞的本意是让杨来喜留在家里,他在家,村长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没料杨来喜话没听完,火气便从后脑勺冒出来。
杨来喜冲到大街上,村长正在人群里站着。杨来喜奔过去,揪住村长的衣领,骂着极难听的话。幸亏人们把杨来喜和村长拉开了。
荞荞追出来,让杨来喜回家,杨来喜不回。四周无数支利箭往荞荞身上射着,她难堪极了。本来没多大事,杨来喜硬是将它搅和大了,现在整个围子都知道了。荞荞丢下杨来喜,泪汪汪地逃回去。
晚上,杨来喜醉熏熏地回来了。荞荞没理他。杨来喜揽住荞荞说,还生气呢?村长和我说了,也没啥大事嘛,和他这种人,犯不着。荞荞愣了愣,问,你跟他喝酒了?杨来喜说,怎么了?他的酒都是白来的,不喝白不喝。荞荞极力控制着才没吐出来,村长一顿酒就把他俘虏了,杨来喜太没立场了。荞荞一直以为杨来喜很在乎她,现在看来,完全不是,荞荞一下感到无比伤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