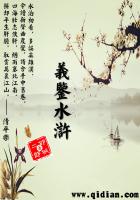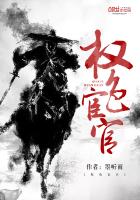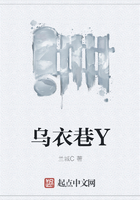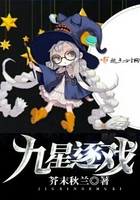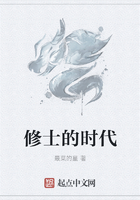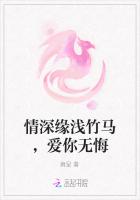钥匙终于从敦煌取来了。时间,从他们来到这里的石窟群算起,已经将近一个月。只是在这时伯希和才被允许进入密室。他写道,“我简直惊得呆若木鸡”。据他粗略地估计,洞内的手稿大约在一万五千至两万之间。如果要打开每一卷而加以适当检查的话,他至少也得花六个月的时间。但是他立刻就作出决定:“一定要把整个书库检查一下,哪怕是粗略的检查也好。”他写道:“至少我必须打开每一件,认识一下它的性质,同时看一看,它是否提供过任何新的东西。”他决定把它分成两堆,一堆是其中的菁华,那是不惜任何代价一定要得到的;另一堆也是需要的,但不是必不可少的。
伯希和凭借着一支蜡烛的微光,蹲伏在斯坦因把大批文物搬走(伯希和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后所留下的小得可怜的一点地方,费去了漫长的、如同被幽闭起来而令人恐怖的三个星期的时间,在积满尘土的一捆捆的手稿里进行挑选。在巴黎吉美博物馆(Musee Guimet)的伯希和陈列室中,有努埃特为他拍摄的一张他在密室中工作的纪念性照片。从这一张照片上可以看到,在蹲伏着的他的后面有堆积如山的、捆扎在一起的手稿。伯希和写给在巴黎的西奈的一封长信中说:“在最初的十天,我每天大约要翻看一千份手卷。这可以说是一个记录……”在谈到当时他的工作速度时,他用多少有些不客气的口吻,把自己说成是可以和竞赛用的汽车相比的一位语言学家。虽则这不过是一种比喻,但他的爱挑剔的批评者却正好抓住这一点不放。
在石窟中每经过一段时间,伯希和就要和他的两个同事聚会一下。过了几年之后,瓦兰回忆说:“他的外套里塞满了他最喜欢的手稿……容光焕发,喜气洋洋。有一天晚上,他拿给我们看的是一份圣约翰斯托里福音;另一次,他拿来一份有八百年历史的描写一个奇异小湖的文稿。该湖位于敦煌之南的很高的沙丘上。再一次是一份有关这个寺院的账目。”伯希和知道,他不可能说服王,把收藏品全部转让给他,因为藏书室的发现,在全地区已为人所共知。瓦兰解释道:“前来朝拜圣地的蒙古人和西藏人以唪诵这种珍贵的文件,作为他们朝圣的一部分内容。”可是伯希和的最大担扰是,深怕撂下了或者还没有注意到一些关键性的文件。他写道:
“然而我并没有放过任何一件主要的东西。我不但接触了每一份手稿,而且还翻阅了每一张纸片——天知道,共有多少断片碎页……”
现在最关键的时刻来到了,即:伯希和必须说服这个小道士,把检出来的放在一边的两堆手稿卖给他。这两人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了会谈。瓦兰在回忆中说:“会谈的结果是,我们自己也必须在极端保守秘密的情况下才能提到有关发现书库的事,即使在我们的信件里也必须如此。”最后,这笔交易以500两白银(约90镑)成交。然后把这批密藏的东西经过小心谨慎的包装之后,经由船舶运往法国。瓦兰接着说:“只是当努埃特带着满装我们的选品的箱子上了轮船之后,伯希和才公开地谈到这些东西,并携带着一箱手稿的样品前往北京。”他接着又说:“对于中国的学者们来说,这完全是意想不到的事。他们简直不相信,在自己的国家里,会有这样重大的发现。”其结果是,北京政府立刻拍发一份电报给敦煌的地方官,责令他对洞内剩余的东西封锁,严禁外运。
瓦兰带着讽刺讥笑的口吻说:“这个善良的道士一定会感到寝食不安,后悔接受了伯希和的钱。”
虽然弄到敦煌手稿是伯希和个人的伟大胜利——至于别人对这种不道德的事情作何看法,先不去管它——但他的两个伙伴在那将近四个月的时间里,也并不是完全袖手旁观,无所事事的。努埃特对于凡是伯希和认为有价值的每一件东西,都已拍摄了数百幅黑白照片。后来把这些照片印出了六大本。虽然伯希和并没有对此花时间与精力写过一份有关的伴随的说明,但今天对于研究那里的壁画与塑像方面来说,这六本照片仍然是主要的参考资料。因为在几年之后,当白俄士兵被拘留在那里时,千佛洞的文化与艺术曾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伯希和最后于1909年10月24日到达巴黎。这时他已经离开那里三年了。在他归来时,尽管人们把他当做一位英雄来欢迎,但同时他也发现还有的人正在给他制造麻烦。这种事后来竟发展成为一种恶性的运动。打击的对象除他自己以外,还有查万斯教授和河内的远东学校。当他不在的时候,他在敦煌第一次看到那些文物而感到无比兴奋时所写给西奈的那封长而生动的信件,发表在远东学校(他仍在这里供职)一份拥有广大读者的刊物上。如果他事先就知道,他的敌人会利用他的信件为资本来反对他的话,他很可能用另外一种写法,而且他也一定会把他的那些公正的、有时甚至是无所顾忌的论点删除掉。我们已经提到过,伯希和的那种知识分子的骄傲——有的人早已看到了这一点——使他怎样在学术界树立了许多敌人。他写给西奈的那封信,正是给他们以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在这次运动中与查万斯的远东学校有牵连的部分,不是我们在这里所要关心的。但是从这件事情的本质上来看,对于查万斯教授的学术水平,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怀疑;另外对于这所有名的学校的全体教职员的工作能力,也同样值得怀疑。在发动这场运动时,最初只是在暗地里进行活动。但是不久这一事件就扩大到报纸和期刊上。尤其是那些和印度支那有关的报刊,更是不惜篇幅,大登特登。伯希和的罪状包括两个方面:作为远东学校的汉文教授,他和其他教职员一样,犯了杰出人物统治论的罪,同时更严重的是,他委托当地的口译人员帮助出版他们的作品,除此而外,作为取得极大胜利的中国中亚远征队的领导人伯希和目空一切,突出个人。这是因为,像他这样一个年轻的人,取得这样大的成绩,对于法国其他的东方学专家来说,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忌妒。他们认为,应当选他们才对。
在主要诽谤他的人之中,有一个是在巴黎国立图书馆东方部里工作的资历很深的图书馆管理学专家。伯希和把敦煌手稿锁在该部的一个房间里,钥匙由他一个人保管着,这无异是不让贬低他的那些人们进去。他们也显然是对此引起极大的愤怒(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这个专家就给法国报纸写了一封极其苛刻而严厉的信。在信里他不但怀疑作为一个汉学家的青年学者伯希和的能力,而且还力图否定伯希和所得的手卷的真实性。这位图书管理学专家以图书馆东方部(被锁在一个房间里的那些东方手稿也要放在该部)管理人的名义,借口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声称对伯希和在敦煌买得的东西,立即放弃保管的责任。与此同时,由远征队带回的其他艺术作品——绘画、塑像、丝织品、木雕和赤陶制品——在罗浮宫
罗浮宫:原为法国王宫,18世纪改为博物馆。
以伯希和为名的大厅中公开展览时,他的诽谤者们对于这些东西,也同样极力加以贬低。有人写道:“人们不禁怀疑,即使罗浮宫里的房间再小,也不应当展出那么少的东西。”
1910年12月,一个法国学者所称作的“这个恶毒的运动”在一期反殖民主义的刊物《地方评论》上,对伯希和、查万斯和远东学校所进行的致命的打击,达到了最高峰。
填满了这份杂志的用了23页篇幅所发表的一篇充满了假情假意和辛辣讽刺的大杂烩,声称要分析伯希和的“丑事”。一个中国老手同时他本人又是一个说中国话的M.费尔南德·法捷耐尔(M.Fernand Farjenel)首先揭发查万斯,说他翻译的东西“即使不是每个单词都错,起码也是每一行都不正确”。不过他的主要目标,则是伯希和。他指责他所反复称做的这个青年的“探险家”浪费了公家许多的钱,在他两年时间的“闲逛”中,并没有取得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他含蓄地指出,在伯希和到达敦煌的时候,由于他是那样拼命地为他的使命来进行辩护,因此也就严重地削弱了他所做出的判断与评价。
为了支持这个论点,法捷耐尔引证了伯希和写给西奈的信里的个别词句。在这封信里伯希和说,当他进到王的密室看到他所看见的东西的时候,不由地“惊得”发呆。法捷耐尔说,他惊得如此的厉害,竟“毫不怀疑地轻信了”道士骗人的鬼话。他显然不知道,不久之前斯坦因已经从这个室内搬走了“二十九箱手稿和绘画”。法捷耐尔争辩说,“这就很可能已经完全搬空了”。
他接下去说,但是伯希和“却满心欢喜,心想他已经发现了无价之宝,以致失去了警惕,也不去核对一下道士的话”。他的明显的结论是,当地的人知道欧洲人喜欢买这些东西,于是把伪造的和那些无价值的手稿重新填进了那个洞穴。他提醒他的读者们要注意,在远东有着许多聪明的流氓。被斯坦因揭穿了的骗子阿克亨即其一例。
一个自己承认在一天的时间里,必须阅读几千份手卷(接照法捷耐尔的计算法就是一分钟阅读两份手卷)的学者,才真正是这些骗子的天生的受害者。事实是,这些手稿现在仍然锁闭在室内而不让别的东方学专家们去接触。这件事情本身就只能增加他和别人的怀疑。鉴于这个远征队“花了那么多钱”,他要求伯希和应当即刻对于批评他的人作出答复。但是伯希和并未予以答复。他深信,诽谤他的那些人,迟早是会收回他们的前言的。
法国的公众,自然无法说明究竟谁是谁非。如果斯坦因当时已经把密室全部搞空了,那么这么多的手稿又从何而来?可是无论怎么说,又为什么把放手稿那间房子的门锁上,而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又不让别的学者们去利用?直到1912年,斯坦因的《中国沙漠中的废墟》一书问世后,才使批评伯希和的那些人销声匿迹。如果法捷耐尔在信心十足地发表他的宏论以前,先把这本书读一下,肯定他是会三思而后行的。首先斯坦因就明确地提到,当时他只能买到敦煌书库中的一小部分,而把大量的手稿仍然留在那里,况且王道士不容许他如同伯希和那样,自由地选择。他所能看到的只限于带给他的那一部分。不但如此,他也不像伯希和那样,因为精通中国文学和图书目录学,而占了很大便宜。他自己则因为不懂汉文,便受到了严重的限制。当斯坦因明白了这次运动是要毁坏他的这个年轻法国同行的声誉时,他就特地出来赞誉伯希和的卓越学识和他的发掘方法。这些都是他在库车地方所亲自看到的。
虽然存心想要破坏伯希和的名誉而在学术领域内所发起的这场运动,终于彻底地失败了;但要知道,类似这样的丑事,也是时有所闻的。但是诽谤伯希和的那些人,真的相信他们所预加在他身上的那些罪名吗?抑或是要把他们所憎恨的或者所妒忌的人置于死地呢?在七十年后的今天,当时的见证人均早已不在人间,他们不可能再站出来说话。但是当时瓦兰所做的评语或者可以作为这一运动的答案。在他们远征期间,他叙述说:“伯希和所做的那些简短的按语和评论在寄回法国后,使收到的人对于这些东西的准确与详细,无不感到惊讶。他们简直不明白,在荒野上和远离图书馆的地方,他怎么还能够详细地回忆起某些论据和原文……他的惊人的记忆力,使他毋需任何参考资料。”这一点也得到了另外一些人的证明,“当伯希和读完一本书的时候,全部内容就留在这个地方。”他的一个同事边说边指着自己的前额。
事实是,他的敌人们不相信他会那样聪明,因此他才受到了冤枉气。直到他们知道他真的是那么聪明(惜为时已晚)时,他们又简单地假定,他不过是一个吹牛大王而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伯希和也要引咎自责。同别的考古学家一样,他不愿意安下心来从事单调乏味的分类和刊行工作。我们知道,他的诽谤者制造了许许多多的事实,说什么这些手稿运到国立图书馆以后,已经过了一整年的时间,可是仍然还藏在箱子里,伯希和甚至连一份目录都不去编制。诽谤者们正好利用这一事实,大肆鼓噪,说他一定是隐藏了什么东西——很可能是隐藏了他那惊人的发现物,要不,就是在敦煌买到的东西都是伪造的。
这并不是他唯一的一次被卷入纠纷中,虽然这是我们所关心的一次。作为法国第一流的汉学家伯希和继续为他自己的光辉事业开辟道路。他再没有到中亚去进行发掘。他是我们主要的四个人当中唯一的没有再回到那里去想搞到更多的文物的一个。但这并不因为他在这一方面缺少兴趣。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北京担任法国使馆馆员时,有一天他对美国的考古学家兰登·华尔纳说,他有几处新的遗址计划去挖掘,但是没有钱。当他有了可以利用的钱时,则为时已晚,因为这时中国人已把西方考古学家拒之于千里之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