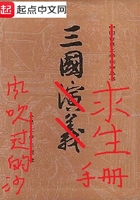在中亚细亚遥远的地方,有一片极大的无边无垠的沙漠海洋。
在这里,中国在实验着它的核武器,同时,还密切地注视着它的俄国邻居。也还是在这里,无数运输队曾经被湮没得无影无踪。一千多年以来,往来旅行者无不把塔克拉玛干沙漠视为畏途,这也是理所当然的。除很少一些人曾经穿过其中有些高达三百尺的危险沙丘以外,自有历史以来,各运输队总是绕过沙漠,沿着它周围的那些孤立的绿洲向前移动。但即使是这样,那些缺乏标志的小道也常被风刮的流沙所湮没。若干世纪以来。许多令人感到凄楚的商人、朝圣者、兵士和其他人所组成的旅行队,由于在绿洲之间迷失了路途而不得不暴尸荒野,骨埋沙漠。
塔克拉玛干的三面环有崇山峻岭,而所余的一面,又被戈壁沙漠所阻挡。这样。即使要接近它的邻近地区,也是非常危险的。
许多旅行者在冰封的关口要隘上,不是冻死,便是因失足而坠入深谷,丧失性命。这是因为从西藏克什米尔、阿富汗和俄国来的人,必须从这些关口要隘下去,然后才能到达塔克拉玛干。在1939年冬的一次灾难中,一个由40人组成的运输队整个被巨大的雪崩所吞食了。而且即使到现在,每年仍然有许多人和牲畜死在这里。
对于塔克拉玛干,没有一个旅行者说过一句好话。曾经穿越这条险路的几个欧洲人中的斯文·海定称它为“世界上最坏和最危险的沙漠”。对它比较熟悉的斯坦因认为,如果拿塔克拉玛干和阿拉伯沙漠作一比较的话,简直可以说后者就不成其为沙漠了。曾一度任英国驻喀什的总领事珀西·赛克斯爵士(Sir Percy Sykes)称它为“一个死亡的地带”。而他的姊妹埃拉,同时也是一个沙漠旅行老手,也把它描绘成“一个十分凄凉寂寞、令人厌恶的地方”。
人们除了迷失路途、口渴欲死这些比较显著的灾难之外,塔克拉玛干还给过往的行人施加特殊的恐怖。范莱考克在他的《中国土耳其斯坦被埋藏的宝藏》这本书中描绘说:“所有运输队无不胆战心惊,唯恐陷入梦魇似的黑色飓风中。”
“天空突然变得黑暗了……刹那间,狂风暴雨猛烈地袭击着运输队。大量沙粒并夹杂着卵石腾空而起,旋转着、呼啸着,猛烈地冲击着人和牲畜;天变得越来越黑暗了。奇怪的碰击声夹杂着暴风雨的呼啸怒号声……来势之猛,犹如天崩地裂,日月无光……任何一个遭受暴风雨猛烈袭击的旅行者,这时已顾不得什么酷热,都把毛毯重重地裹住了全身,借以逃避飞沙走石的猛烈袭击。人和马匹必须躺在地上,忍受着一连持续几个小时的骤雨狂风。”
曾经经历过这种暴风侵袭的其他几个欧洲的行旅,其中包括海定在内,也都作过类似的描述。在这样时刻里,最为重要的是,莫如保持镇静。1905年一个由60个马夫组成的运输队,在接受委托运送一批银元宝到吐鲁番绿洲去的路上,中途因遭到一次飓风的袭击,全部覆没。那次风暴的猛烈竟把满载的马车都弄翻了。范莱考克说:“当时那60个中国马夫全都飞奔到沙漠里。后来在那里找到了几个已经干瘪了的人和牲畜的尸体。其余的都已杳不可寻。这是因为风暴总是要把它的牺牲品埋藏掉的。”这一事件不是由于驾驶者,就是由于马匹惊恐而造成的结果。但是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则认为这样的事件是沙漠中精灵作祟所造成的恶果。他们相信,这些妖魔鬼怪经常出没在沙漠地带,同时还诱引人们,使他们遭受折磨,最后干渴而死。
在公元7世纪,伟大的中国旅行家玄奘,在经由塔克拉玛干前往印度时,也描写过这些精灵。他写道:“当飓风升起的时候,人和牲畜都陷入混乱状态,惊慌失措,不知所从。有时可以听到悲伤和引人哀怜的呼号声。这种沙漠的景象和声音,使人感到心慌意乱,难以自持。因此死于征途者,不胜枚举。但这全是那些精灵和魔鬼干下的事情。”
在20世纪20年代,任英国驻喀什总领事的克拉芒特·斯克林爵士在他的《中国的中亚细亚》一书中,对这块沙漠的面貌,作了生动的描绘:“在清晰的黎明时刻,北方一带呈现出阴森恐怖和令人望而生畏的景象。塔克拉玛干的黄色沙丘像凝固了的海洋中的巨浪一样,无边无际地延伸到遥远的地平线上。到处都有一个巨大的沙丘,拔地而起,犹如鹤立鸡群一样矗立在其他沙丘之上。
它们好像在默默地召唤那些沙丘要像过去已经多次吞噬过的那样,去吞没那些行旅和运输队。”
曾经在中国、俄国和英国英国:这里指英国的殖民地。三个王国交汇的地方,负责这个敏锐的情报收集中心长达两年半的斯克林回忆,在他与一个从“中国本部”出发经由戈壁和塔克拉玛干沙漠最后到达喀什的旅行者的一次谈话时,那个人告诉他说,在这个旅途的荒凉寂寞的地段上,他一共走了50天,但却没有看见过一个人影。
约在40年前,另外一个从北京到喀什走了3500英里路程的旅行者,是副领事兼印度陆军军事情报主任马克·贝尔上校。他作这次旅行的秘密使命是,要正确估计一下,当俄国人经由中亚细亚向印度进犯的时候,中国人是否有能力予以抵抗。他和一个年轻的伙伴扬·哈斯本中尉(后来叫做弗朗西斯爵士)进行一次从北京到印度经由不同路线的比赛,贝尔以早到五周获胜。
后来,贝尔以鄙视的口吻写了一些有关戈壁的一切。他报道说:“水是很容易得到的,而且常常接近地面。旅行者很喜欢夸大越过沙漠的困难与危险。但是困难却是很少很少的。在我们离开喀什以前,我们满有理由地认为,在戈壁的日子远远比在喀什加利亚沙漠的小山和平地要愉快得多……”当然,他所说的后者指的是塔克拉玛干的边缘地带。正如其他大多数旅行者一样,他是小心翼翼地沿着它的边缘行走的。
若干年来,这个中国的、很少有人知道的地区,在当前的地图上或者在旅行者的回忆录中,曾经有过不同的名称。因为在不同时期流行着不同的叫法,如:中国鞑靼、鞑靼高原、中国土耳其斯坦、东土耳其斯坦、中国中亚细亚、喀什加利亚、西域和新疆。尽管这些名称都指的是塔克拉玛干,但是名称使用得越早,它的疆界也越模糊不清。有些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旅行者,把它称为亚细亚高原,但是这种叫法似乎把西藏也包括进去了。而西藏这块地方,正如斯文·海定在一次描绘中所说的那样:“那是在我们行星表面上,所呈现的最大的地壳隆起。”
古代汉朝的记载表明,两千年以前中国人称塔克拉玛干为“流沙”或者“流动的沙”。这是由于沙漠中残酷无情的飓风在不停地吹刮,使得它的黄色沙丘一直在不停地移动着,所以才叫了这样一个名字。当今水文地理学家和气候学家认为:在由于冰川融化的水所造成的河流流入较浅的罗布泊之后,塔克拉玛干已经是比较地驯服了,驯服得犹如塔里木盆地一样。至于塔克拉玛干的明显的神秘性“漫游”,最后将由斯文·海定加以解决。在中国近代地图上,塔克拉玛干(突厥文的意思是:“只有进去,没有出来。”)处于现在被正式称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中心。它是一大块卵形的空白地带。
塔克拉玛干和它的绿洲在四个方面都得到了保护,使它们不受任何具有最大决心的侵入者的进犯。北有高大的天山,西有号称“世界屋脊”的帕米尔高原,南面延伸着喀喇昆仑和昆仑山脉,只有东面没有山脉,但是大自然却在那里布置了两个较大的屏障,即罗布沙漠和戈壁沙漠。大多数英国旅行者(贝尔和扬·哈斯本除外)经由有些地方竟高达一万九千英尺的喀喇昆仑隘口,才从印度进入了中国的中亚细亚。海定把这条荒凉的路线描写为“走向悲哀之路”,因为它夺去了大批人、畜的生命。正如在1950年,一个旅行者所写的那样:“在我们到达平原之前,没有一处看不到死者的白骨。每当我们不能肯定路线的时候,这些连绵不断的骨骼和遗骸便成了我们的可怕的引路者。”在一本探索印度河的历史记载《狮河》一书中,琼·费尔利写道:“喀喇昆仑线路的沿途,什么都不生长,行旅必须为他本人和牲畜携带必需的食物。运送商品的驮畜都以负载过重,无法多运饲料,而结果成百万地饿死在这条路上。”可是在另一方面,斯坦因爵士却轻率地把喀喇昆仑路说成是“一条连太太小姐们都能旅行的坦途”。他的这种说法无异是在开玩笑。
但是在19世纪,这里确实有一种令人不能轻易摆脱的危险。
那就是,随时有被杀害的危险。那时,凡是敢于闯入这个危险山区的外地人,都被当地部落看成是合法的猎物(为此,斯坦因甚至在1906年还随身带着武器)。这个无法无天的做法,使几个欧洲旅行者,其中包括达格利什、海沃德和玛克罗脱在内,都丧失了性命。这威胁并不是对任何个人的,而是中亚细亚所得出的挑战的一个部分。今天,随着越过喀喇昆仑的、新的双向公路的修成,已无须再雇用在中亚旅行所必不可少的骡马、厨子和苦力了,也无须再去攀登那些令人头晕目眩的悬崖绝壁和躲闪坠石与枪弹了。
但是,在这里使我们所关心的那些辉煌成就,都是一些生活在比较早期的人们所创造的(虽然其中的第一个人斯文·海定只是在1952年才死去)。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宁愿忍受最大的困难,冒着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甚至在必要的时候,就葬身在亚洲的这块死气沉沉的地方。是什么东西如此有力地把他们吸引到塔克拉玛干这个寒冬酷暑的地方?要了解这一点,我们有必要回溯一下两千年以前的中国历史。
***
在耶稣基督降生的前一个世纪,一个名叫张骞的胆大而又富于冒险精神的青年中国旅行家,担负着秘密的使命,从中国出发,到当时西方的那个遥远而又神秘的地区去。虽然他的直接目的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但在中国历史上证明,这是一次具有重大和深远意义的旅行,因为这次旅行使中国发现了欧洲,也为丝绸之路的诞生创造了条件。张骞以膂力过人,敢闯敢干而著称。当时汉武帝苦于匈奴进犯,所以才派他作为开路先锋。匈奴原系突厥族,是中国的宿敌。这些好战的匈奴人最后迁到欧洲。这就是我们的历史上所叫的以劫掠蹂躏为生的匈奴。他们最初开始侵略中国是在战国时代(公元前476—前221)。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为了抵挡他们的骚扰才构筑了长城。
汉武帝或如人民所正式称呼的天子,从俘获的匈奴人口中得知,在若干年前,匈奴曾经打败中亚细亚的另一个叫做月氏的民族。匈奴人把被征服的民族首领的头盖骨制成酒器,并把他们赶到塔克拉玛干以西的辽远的地方去。有人告诉他说,月氏人民正在那里静待时机,准备雪耻复仇。但要达到这一目的,首先必须找到一个同盟者。武帝闻讯后,当即决定和月氏进行联系,以便把双方的人马联合起来,从前后两个方向同时向匈奴发动进攻。因此,他要物色一个适当的自告奋勇的人来完成这个具有极大危险性的使命。之所以是危险的,是因为从中国到月氏去的秘密使者,首先要通过匈奴所占领的地区。作为一个皇室官员的张骞,自愿报名参加。皇帝当时接受了他的申请。在公元前138年,他带着由100人组成的誓与匈奴决一雌雄的旅行队出发了。不幸当队伍走到现在甘肃的地方时,他们遭受了袭击。幸存的人都成了囚徒,过了十年的俘虏生活。但是,在这中间,张却得到优待,并且还给他一个妻子。他在长期被监禁期间,始终保藏着武帝给他的那个作为使者标志的一条牦牛尾巴。目的是一有机会,就持此潜逃,继续西征。他们所期待的日子终于到来了。那就是在监视者对他们的看管日益松弛以后的某一天,他带着剩下来的人,悄悄地溜走,再一次踏上征途。
当他们最终到达了月氏(后来月氏成为印度北部的印度—塞西亚的统治者)的领土时,万万没有料想到在月氏人被匈奴打败以后的许多岁月里,竟变得繁荣昌盛,生活安定。这时他们对于复仇雪耻早已不感兴趣了。张骞在那里和月氏人相处了一年。
这期间,他尽可能收集当地和当时中亚细亚其他部落和国家的情报。不幸在回国途中,行经匈奴领土的时候,他又一次被俘了。碰巧,那时匈奴各酋长之间发生了内讧,于是他在兵荒马乱之际又一次设法逃走了。他自去国远征,即杳无音信,人们都认为他早已身死异地;不料在十三年以后,他终于又回到了汉朝的京城长安,向皇帝作了汇报。当时在他们的一伙人中,生还的除了张本人以外,只剩下了一个。
张骞带回来的有关军事、政治、经济和地理的情报,在当时的大汉朝廷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因为汉皇从他这一秘密使者的报告中,知道了前所未闻的、富饶的王国,如大宛、撒马尔罕、布哈拉(现在都属于苏维埃中亚细亚)和巴尔赫(现在在阿富汗)。同时也使中国人第一次知道还有波斯和另一个遥远的、被叫做里琴(Li-jien)的地方。这后一个,今天的学者们认为,很可能就是罗马。但是,这中间最最重要的则是在大宛发现的一种惊人的新型战马。据张的报告说,是“天马”的后代。这种马高大善跑而又强壮有力。这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是一种新的发现。
因为那时,中国的马是今天人们所熟知的泼里奇伐尔斯基马的品种。
这种马身躯矮小,行走迟缓,现在只有在动物园里才可以看到。
武帝认为这种大宛马是对犯上作乱的匈奴进行骑兵作战时最合乎理想的马。他决定用这种马来重新装备他的军队,并派了一个使团到大宛去,想能再得到一些。但是这个使团在途中被消灭了。后来派去的使团也接二连三地遭到了同样的命运。最后,他派遣一支强大的军队,并且带着兽医,把大宛包围起来。但是当地居民把马匹都圈在城里,并且恫吓说,如果再前进一步,他们将同所有的马同归于尽。后来他们接受了大宛人所安排的光荣的投降,带着战马回国。虽然这种“天马”现在早已绝种,但是它的形象在汉、唐雕刻家和艺术家的手下则并未磨灭。其中最精彩的摹拟品,是1969年在曾经一度是汉武帝的京城西安附近的丝绸之路上不在西安附近,而在甘肃的武威县(现为武威市——编辑注)雷台。,被中国考古学家所挖掘出来的闻名世界的青铜飞马。这是两千年前,一个不知名的雕塑家所塑造的杰作。
武帝对于他的秘密使者以极其坚强的决心所作出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贡献,大为赞赏,并赐以博望侯这样的光荣称号。这时由于武帝决心要向西开拓他的版图,先后又进行了多次的远征。
其中一次是仍由张骞率领的于公元前115年派往乌孙的远征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