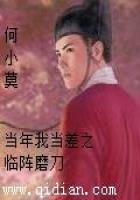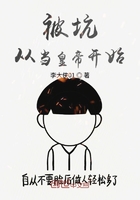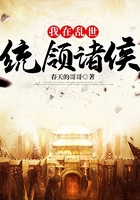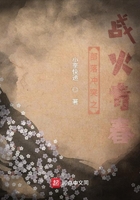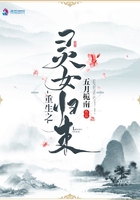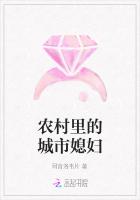经过了十一天旅程之后,到达了房倒屋塌、鬼蜮似的丹丹乌利克。其中最后的六天,他们是在冰冻的塔克拉玛干上走的。在白天,温度从来就没有升到零度以上,而在夜间,有时却降到零下十度。即使在生了火的帐篷里,当水银柱下降到零下六度的时候,斯坦因已经感到无法再继续工作了。睡眠也成了问题。他写道:“一觉醒来,发现被子被呼出的热气冻得硬邦邦的。真令人感到很不舒服。”最后,他采用了这样的办法:就是把皮大衣盖在头上,然后通过袖管来进行呼吸。
在塔克拉玛干边缘的最后一个绿洲亚脱拔西(Atbashi)村镇上,他征募了三十个劳力,每个人都带有自己的一把锄头。这些人都不愿冒险进入沙漠,因为他们最害怕的是魔鬼。他们的这种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由于他们头儿的压力,工资的诱惑和斯坦因所带领的特尔迪及其他两名富于经验的老手对沙漠情况的再三保证,斯坦因终于使他们转变了念头。但是在出发之前,斯坦因给每人发了一件当地所能买到的最厚的冬衣。
正当运输队越来越深入沙漠时,人和骆驼的脚也在松软的沙中陷得越来越深,这就使得行进迟缓,消耗体力,同时也影响了身上背着重担的队伍的前进速度。结果每小时只能走一英里半,很少能每天超过十英里。但是在圣诞节的前一个星期,他们终于到达了这个“环境特殊、充满着死亡与荒凉”的丹丹乌利克。斯坦因一眼就看出,那些觅宝者早就到过这里。看得见的破坏到处都是(他估计,很可能海定也是其中的一个。虽然他由于老练和圆滑而并不这样说)。特尔迪承认他自己来过多次,虽然他还有待于去寻找他真正希望的东西黄金。但这一点儿都没能阻止斯坦因去进行挖掘的决心。因为他知道,他的这个小小的挖掘队没有在这样一个被上帝舍弃了的地方,一次能住上一两天以上的物力和人力。他们只是在露出地面的建筑物中随意挖掘。而把那些被沙丘埋没的遗址则一概留下不动。在这里,从特尔迪能够向斯坦因指出的那些还没有遭到劫掠的建筑物一事来看,可见他对于遗址是了如指掌的。这一点是极可宝贵的。
斯坦因最关切的问题是,要使他的人们在零度以下的夜间不致因受冻而死亡,尽管他们都穿了厚厚的衣服,他还要到处找寻生火的木材。幸而他在附近的果园里找到了一些。这些木材原先都是这个死城里曾经一度开得繁花似锦的果树,然而中经几百年的漫长岁月,现在都已成了不可雕琢的朽木了。他搭起了帐篷之后,就把骆驼队派到距离这里有三天路程的凯利亚河去。因为在那里有骆驼吃的饲料,可以使它们变得膘肥体壮,准备将来继续走路。
因为时间宝贵,在次日早晨就开始了他们的挖掘。这是斯坦因多年来一直在等待和计划的一刻。他的理论、知识和技能要在这里,他的第一个在塔克拉玛干的遗址丹丹乌利克,接受考验。最初,他在靠近他营帐南边的一所矮小方形建筑物的残留部分开始工作。这里,在很早以前,就被特尔迪所发掘过。他告诉斯坦因说,这是一所“偶像的房子”。然而斯坦因所关心的并不是在这第一所建筑物内去寻找文物,而是要使自己熟悉这些圣祠的布局和结构。
他的自传的作者珍尼特·米尔斯基解释道:“丹丹乌利克是一座课堂。在这里,斯坦因学习了古代的被沙子湮没了的圣祠和房屋的基础知识:它们典型的场地设计、建筑和装点,它们的艺术和佛教徒对它们的礼拜仪式等等。另外他也想用这个遗址作为他的实验室,去找出最合适的方法,用以发掘被像水一样淌着的沙子所湮没的废墟。因为这种水似的沙子的流速之快是很惊人的,挖掘人刚把沙子抛出来,它就又流进去了。在这方面斯坦因没有先例可循,也没有经过训练的劳动力以及在考古学上所应当注意的事情、目的和方法……他的方法是,从易到难,从他知道他所能发现的东西一直到他连想都不敢想的发现物。他的方法既是小心谨慎的,又是试验性的。”
虽然他在挖掘时因小心谨慎,又因这座庙宇以前已遭过劫掠而进度缓慢,可是在第一天的发掘中却找到了许多古代佛教壁画和灰泥粉刷的浮雕。每一件发现物在运走之前,都在原处小心地拍成照片,并用标签详细标明出处。就这样把总共115件文物经过艰难险阻的漫长路途而运往了英国博物馆。次日,斯坦因又转移工作地点,对沙底下八英尺深的一小群建筑物进行挖掘。在这里,同样也找到了一些壁画。不过多数易碎,无法搬走。但是到此为止,除了一小片碎纸外,并没有发现任何手写文稿。可是斯坦因所最最渴望要找到的东西却正是那些带有文字的手稿。因此,他决定像海定那样,对于第一个能发现一份手稿的人,以白银作为奖赏。于是在不到一小时的时间里,只听一声激动的欢呼声“卡特”——突厥语“文件”。
这份手稿是一张椭圆形的古老纸片,上面写着一种非印度语言的文字。证明是一种独特的印度手写文稿形式上的一张单页。这种形式可以把这样的许多单页叠在一起,打上圆孔,然后用线串上。从这个时候开始,手写稿不断有所发现,都是佛教宗教法规的梵文经典。其中的一些是在5世纪至6世纪写的。斯坦因很快认识到,他们所正在挖掘的这所建筑物可能是一座佛教的寺庙,其中有过一个完整的图书馆。
令人费解的是,这些手写稿怎么会放在一间从其他遗物看来是作厨房用的地方,并且还是在离原来地板有几英尺高的松散的沙子里发现的?这里唯一可能的解释是:它们一定是从上一层的房间——一座小寺庙的图书室——掉落在底层的厨房之内的。而所有上层建筑的种种遗迹,则由于长时间的风沙的侵蚀早已化为尘土。
公元1900年圣诞节,他开始在他的帐篷东北有半英里地的一群显然是综合庙宇但却充满着沙子的建筑物中工作。这里虽然表现出曾经遭受过觅宝者破坏的痕迹,但是直觉告诉他,如果仔细地发掘,仍然可能会有重要的发现。事情也诚然是这样。首先出现的是木板上的两张画像。几个月之后在英国博物馆把其中较大的一个上面的沙土小心地剥掉之后,可以看出上面所画的是人的形象。可是却把他的头画成戴着王冠的鼠头,坐在两个侍奉者中间。
这很清楚,画的是曾经拯救过和田的圣鼠之王。
第二个发掘到的东西是两张碎纸片,上面带着的文字,斯坦因立刻就辨认出来,是在赫伦勒博士的收藏品里他早已见到过的用婆罗门文字所写的一种特殊的草写体。同样的碎片也很快就在干沙子中间挖了出来。他用冻僵了的手打开这些被弄绉了的文件。
经过粗略地考查,所发现的这些手稿和加尔各答收藏所中所存的与此相似的一种,有着明显的联系。后来,赫伦勒博士也肯定了这一点。斯坦因认为,加尔各答收藏所所存的很可能是特尔迪早年在丹丹乌利克的时候所发现的。后来他对这些褪了色的脆薄的纸张经过详细的检查,证明这是些8世纪官方的和私人的契约记录,其中包括借据和征调令。
圣诞节那天,也有许多使人惊异的发现,中文文件的发现就是其中之一。后来由麦卡纳把它翻译出来,证明这是一份要求归还一头驴子的请求书。驴是出租给两个人的,可是经过了十个月以后,他们不但没有归还,反而连人影都不见了。但是更重要的是,请求书上面有着精确的日期——大历十六年二月六日,即当时的公元781年公元781年为唐德宗建中二年。,至于请求书上面的地名,可能有各种不同的读法,但可以肯定的是,都指的是丹丹乌利克的原始名称。其他带着同样名称的与此类似的文件早就带到了加尔各答。那些东西,很有可能也是特尔迪发掘出来的。因为至今他还清楚地记得,在若干年之前,他在这里曾经找到上有汉文的、看起来和现在的十分相似的东西。当时他都卖给和田的一个买卖人了。
在那个圣诞节日,要是没有特尔迪,斯坦因的最后一次冒险很可能以悲剧而告终。那是因为,在那天傍晚时分,斯坦因和他的雇工一起步行返回营帐。在一个沙丘的脚下,他拾到一枚中国的钱币,从上面的日期看,是1200年左右的古钱。当时他在那里流连忘返,希望找到更多一些的时候,他们人都朝前走了。后来他追述当时的情况时写道:“过了一会儿,当我在暮色苍茫中开始返回的时候,我迷失了路途。后来我在低矮的沙丘中踏着沉重的脚步,大约走了一英里的路程,结果还是没有找到我的营帐。那里既没有声音,也没有任何标记能够给我指路。”当时他意识到了,他完全有可能因为在黑暗中迷失方向而在夜间冻死在那里。一想到这些,趁着还能辨认自己的脚印时,便立即往回走,突然他认出了,在他的帐篷东北有相当一段距离的地方,从沙子中间露出来在几天以前他所见到的古墙遗迹。他写道:“凭我记忆中的这些遗迹的有关位置,我转向右方,沿着我所知道的主要是由西北向东南延伸的沙丘顶峰线,慢慢地向前移动,一直到听见我的喊叫声的人回答我为止。”特尔迪对于他的失踪,感到十分不安。
所以他就把队里的人分成几个小队,每队两个人,出去找他。“在这次小小的事故之后,我能回到我的帐篷并能喝到热茶,我感到加倍的高兴。”斯坦因以十分含蓄的笔调,写出他的宽慰与感谢。
第二天,他开始挖掘前一个夜间曾经救过他生命的那些废弃的建筑物。第一个要清除沙子的建筑物是一座小庙。不但在那里找到一些手写稿的碎片,而且还获得许多饶有趣味的壁画和画着图的木板。然而更重要的则是,他们在第二座建筑物底层室内所挖掘出来的文物。这里,他们从干沙中挖出一个小窖,其中充满着很整洁的用汉文写的手稿。一部分手稿由于以前若干年来的湿气,已经腐朽不堪。可以想象,在这个市镇的水源于最后干涸之前,这些东西,一定是遭到由屋里的泥地所渗出来的湿气的破坏。
幸而其余的还保存得很好。这些都由当时的两位著名汉学家爱德华多·查万斯(Edouard Chavannes)和罗伯特·道格拉斯爵士(Sir Robert Douglas)译成了汉文。其中两份是私人的小借据——一份是借钱,另一份是借粮——从文字上看,是一个护国寺的僧人名叫秦英的立下的。上面都写着借的人和担保人的姓名。同时附加申明说,愿以他们的家庭、财产和牲口作为抵押品,两张文契写着相同的年代:782年。
正如斯坦因所指出的那样,这座寺庙的中国名称(“护国”二字是保护国家之意)和记录在第三个文件上的主持僧的中国姓名来看,“该寺庙是属于哪个国家的,一望便知”。可是紧接着他又附加一句说:“但从借东西的人和担保人的名字来看,支持和资助该寺庙的人们,却并不是汉人,这是很明显的。”对斯坦因来说,这些文件的价值,是在于它们记录了一些细微的琐事。他解释道:
“这些在性质上并不重要、在尺寸和内容上亦无重大意义的文件,绝不可能在上述建筑物最后被废弃以前很长的一段时期里就存在的。”所有文件的日期都是从782年到787年。这样就可以推测,大约是在8世纪的末叶,丹丹乌利克才陷入沙漠的。
就在地窖里发现有一卷文件的那座同一建筑物中,斯坦因还找到了三块画得十分优美的木板,在其中的一块上,画着一个人骑在一匹马上,另外的一个人是跨着腿骑在双峰的骆驼背上。当他擦去上面的沙土之后,他立刻认识到它在艺术史上的重要意义。
诚然,这正是他一向所要找寻的证明他的理论正确性的最清楚不过的证明。不单是它的画法和构图表明了7世纪丝绸之路上的艺术家们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而且这种把印度、波斯和中国的影响十分清楚地“混合”在一起的画法,又提供了西域艺术当它缓缓东进的时候,如何逐渐形成的一个极好的绘画范例。
斯坦因在描绘这幅精致图画时这样写道:“这匹马的骑手,年轻英俊的面孔具有中印两国的混合特征,长长的黑发在头顶上结成一个疏松的抓髻……踏在马蹬上的脚穿着一双毡底高筒黑靴,很像现今在中国土耳其斯坦有钱的人们仍然穿着的那种……腰带上挂着一把几乎是笔直的长刀,刀的式样看起来很像早年在东方的波斯和其他****国家所使用的那样。”在谈到马具和服饰时,他说:“在公元八世纪的土耳其斯坦和一直到今天还流行的马饰中,再也没有比这张画上画得更准确的了。”
斯坦因在丹丹乌利克将近三个星期的时间里,共发掘了14所建筑物。他对该地的地址也作了仔细的调查,并观察了它的幽灵似的花园和有白杨树的林荫道。这些树的瘦削而碎裂的树干有一半湮没在沙漠中间。在这里到处都有古代灌溉渠道的痕迹,“显然,渠道的型式是仿照现今仍在中国流行的那种式样”。他作出结论说,丹丹乌利克并不是由于突然的大灾难而放弃的。对此他作了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可能是由于政治上的****,以致忽略了公共的灌溉系统——没有这个,生活就无法维持——另一种可能是多年来水流枯竭,使得居民们除了离此他去,别无抉择余地。他提出他的看法时说,从所有考古学上所得到的证据来看,都指出这是一种逐渐的衰落,而不是像有些当地的传说那样,说什么这个一度繁荣的运输队市镇是遭受了像所多玛(Sodom)和蛾摩拉(Gomorrah)两城市的命运而被放弃的。Sodom和Gomorrah 二城源出《圣经》,系指罪恶之地。
公元1901年1月6日,在付给了劳工们工资之后,斯坦因带着满载珍宝的队伍,越过沙漠,东往凯利亚河,意欲逆流而上,前往凯利亚绿洲。他长期以来对于塔克拉玛干的丹丹乌利克所怀抱的信念最后终于得到了证实,他写道:“在我向那些我曾经在那里工作过三周的静寂的沙丘告别时,我的心情是很复杂的。在这些沙丘所保存下来的许多奇异的废墟中,已经挖出许多东西,这样它们都回答了有关这方面所提出来的大多数问题。同时在我多次走过这些隆起的沙浪时,我对它们那种单调的景色已发生了喜爱。
在我到此以前,千年以来,丹丹乌利克一直陷入孤单静寂之中,无人过问;在我走后,它仍将一如往昔,默默无闻。”在到达河流以前,他们要越过一系列沙山,其中有的高达150英尺。最后,他们到了河冰耀眼的凯利亚河。由此再转而向南朝着比较现代化的凯利亚绿洲走去。在那里,斯坦因希望能知道邻近的其他废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