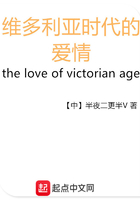有时候我也会和舍友一起出去买衣服,但我不经常买,我不喜欢橱柜里满满的都是东西没有一点多余的空间,而其他人则不以为然,她们在找东西的时候打开橱柜,里面哗哗的衣服往外冒,我看见就觉得要窒息一样,所以一般情况下我只是去看衣服,看颜色款式和布料,舍友们叫上我也只是想找个参考。
“我打算买件小外套,你说是运动风格好还是正式一点的好?”舍友问。
“正式一点的吧,”我建议说,“反正以后工作也要穿,现在提前感受一.下。”
“好,那就去看休闲一点的小西装吧,走,去那边。”我被她拉到一处专卖西服的商场,快速的浏览着各种造型和面料。
“那几件不错,”她指着一排女士花色小西服,“很少有人敢这样穿的。”
我顺眼看去,一系列的白底彩花在暗紫灯光色的包围下向我们招手,那些布在做裙的时候经常用,拿来用在严谨的西装上,也别有一番俏皮可爱的味道。
“走,去试。”我们带着喜悦去试衣间,试了一件又一件,她还是拿不定主意,而我也着实想买一件,但看到标签上的价格有些昂贵便有些犹豫,“到底是红色的好,还是黄色的好?”她一手拿一件衣服,来回对着镜子比对。
“干脆两件都要啦,”我说。
“去,这么贵,你买不买?”
“不知道。”
“你去试一件黄的,”她把衣服递过来,“你皮肤白,应该好看。”
“等着,”我放下包,拿起衣服去试。果然很漂亮,我看着镜中的自己在素雅的纹样中微笑,心动极了,同时心里一个坚定的声音说,买吧,就是它了。
忽然,“苏诺,你手机响了,”舍友打断我的欣赏念头,“你接不接啊?”
“接,给我,”我拿过手机,一个陌生的号码,“喂”。
“小诺,我是你姐夫。”
“姐夫?我没姐夫啊。”我知道学校经常有一些无聊的男生玩那种类似于真心话大冒险的游戏,输的一方就随便给一个号码打电话,说一些搞怪的东西,因为我们的号码都是学校统一的,去除后四位前面的都一样,宿舍里已经有好几个人撞到过这样的电话了,我就多留了一个心眼。
“小诺,你回来吧,珍珍出了点事情。”那边平静的回答,我恍然意识到对方是孟勇。
“出了点事情?什么事?”我心里不禁一颤,紧张的问。
“她自杀了。”
我脱下身上飞舞的衣服,抓起包往学校跑去,心里好像预料到这样一天似的,但又觉得它来的太仓促,我还没想好怎么面对。宿舍里有些人在聊天洗衣服,我说,颤抖着声音,“钱,谁借我点钱,我没时间了,我马上回家。”
她们放下手中正忙的东西,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我姐,”依旧颤抖不止,“死了,我要回家,回老家一趟。”
“你先别急,我们有钱。”一个舍友安慰说,紧握住我的的手,试图让我稳定一下情绪。
“苏诺,你先去请假,去找导员,我们帮你收拾东西。”卫生间里的舍长走了出来,擦干了手上的水,“会子,你和她一起去。”
平时出门必然化妆的她那天穿着拖鞋和我一起下楼去,一路踏拉着跑到了办公室,虽然平时她很苛刻,但在大事上她还是很有脸色的,我来不及什么感动,刚要进去却被她拉住了,“没事,你先平静一下。”于是我们又在外边的墙上靠了一会儿,等我渐渐恢复后才推开了办公室的门。
“导员,我要请假,不知道请几天,三天大概够了,我家,我姐出了点事,她去世了。”尽管平息了一会还是语无伦次。
“奥,什么时候的事?”她没看我,好像这样的请假她司空见惯了一样,一只脚很有节奏的在地上拍打。
“刚刚我姐夫打电话过来说的。”
“是你的亲姐姐吗?”她问。
“不是,她是我以前的一个同学,我们很要好,就……”
“你明天有课吗?”她没等我说完。
“有,有计算机和工艺。”
“那你这周末回去吧,怎么能不上课呢?”她抬起头,挤出一个虚伪的笑脸。
“啊?不行,”我说,“老师,这。”
“按学校的规定,如果参加一个和你没任何关系的人的丧礼,是不能允许在上课期间的。”
“老师,求您了。”我看着她麻痹的脸好想把桌上的几本书甩过去。
“这是规矩。”
“我必须回去。”
“那你这算是故意不请假离校。”
“我请了你不批准。”
“不如这样吧,”她打开双臂,“你回来时要带死者的死亡医学证明和一张关于你和死者关系的证明,好吧。”
“什么,”我第一次听说请假还需要那些东西,“那我不回去了,行吧。”我瞪了她一眼心想只好不请假了,直接回家倒也省事,于是失望的走了出去。
“批准了没?”会子问。
“没,那个混蛋说要开死亡证明。”
“是哪个导员在值班?张导吗?”她问。
“嗯,是她。”我说。
“她就是那样的,要不你明天再回去吧,明天去找王导请假,他可能会通情达理一点。”
“不行,我今天就得走,”我说,“我要见我姐最后一面吧。”
宿舍里已经帮忙收拾好了东西,三张红色的百元大钞摆在旁边,“怎么样?”舍长问。
“别提了,不批。”会子说。
“那……”
“我不管了,我现在就走,”我拿起钱,“先去买火车票。”
“你干嘛呀你,”舍长抓住我的胳膊,力度大的一阵疼,“你冷静点,不请假就走,查到了是被处分的。”
“我管他狗屁处分,我要回去,必须走。”我挣开她的手。
“你先别急,坐下来大家一起想办法。”她还是硬把我拽到了椅子上。
“晚上查宿舍,我替你担着,白天上课如果老师点名我们就找有一个没课的去替你,”她思考着,“你什么时候回来?”
“舍长,上课不能找别人替她,专业课老师都认识我们,去一个陌生人一下子就露馅了。”有人说。
气氛一下子慌张起来,怎么办,怎么办,就这样不被批准就回去吗?如果回去会有什么处分?那如果不回去,姐怎么办,她不能死,她还那样年轻。
“对了,”会子拍了一下桌子:“你明天去找王导啊,他明天值班,刚才我不是说了吗,去找王导试一下。”
“王导,”我小声地说,脑子里除了慌乱一片空白,“好吧。”
夜,像静止了一样,我躺在床上记忆像电影一样铺陈开来:我和她从小就认识,一直很要好。她小时候很要强,每年都会捧回一张奖状,而我则看她骄傲的把它挂在墙上,羡慕的不行。爸爸去世后,我和妈妈生活一直很窘迫,她常把我带回她们家吃饭,我喜欢他妈妈做的鱼。妈妈再婚那天,我哭着在她床上睡着了,醒来她把她的生日礼物一只毛绒兔子送给我。她退了学,我一直去她的店里,不知拿了多少免费的书,吃了多少不要钱的午餐。我还记得她在集训后陪我战胜了对高度的恐惧一起坐在观赏车里向下面的芸芸众生看去。她在我高考后淡淡地说起梦想,她说她想唱歌,她一边走一边唱着郑钧的三分之一理想,她来看我时变得很漂亮,她说正在学吉他,这一切都离她的梦越来越近,怎么会突然死去呢?孟勇只提了一下吃了好多安眠药,怎么会呢?一切都在变好不是吗?
一阵撕心裂肺的疼痛要把我淹灭,我感到胸中一股焦灼的的火焰在燃烧,紧张与慌乱导致我满头虚汗,这是地狱,这不是人间。听!旁边的魔鬼在歌唱,他们边唱边笑,讽刺着那个死去的追梦人。看!还有一群撒旦圈在一起跳舞,他们狰狞的脸上全是喜悦,围在姐的周围像是在庆祝一个婴儿的诞生。
我忘了是如何度过的那样不安的夜晚,早上像虚脱了一样没有精力做任何事,好心的舍友帮着买了些早餐,安慰了几句后就各自上课去了,我拖着轻飘飘的脚步去导员办公室,一个长头发的女人在檫桌子,擦完后把她随手把手提包放到旁边并坐了下去,我小声地问,“老师,请问王导在吗?”
“王导?他不在。他今天出差了,你有事吗?”她和霭的脸上略过一丝关心。
“噢,我来找他请假。”我说。
“请假去找张导,她就在隔壁。”她指了一下门外,“向右拐就是”。
“好,谢谢老师”没必要再找张导了,那个尖锐的导员总喜欢为难我们。姐,我来看你了,你等着,再坚持一会,我马上就回家了。我留了一张便条放在桌上:舍长,王导不在,我直接回去了,回来时会把钱还给你们。苏诺。2012年4月13日,然后抓起已经收拾好的背包,拦下一辆出租车,直接去了火车站。
从学校到家乡的小城,火车一路驶了三个小时。下火车时刚过正午,路边的小餐馆异常热闹,我肚子也是空荡荡的,但是一点胃口也没有。姐,佳佳,欧洲梦。这三件事物构成了我青春的全部,以前我以为它们永远都不会离开我,那天随着姐的去世它们都消失了,我站在繁华的街头,生出一种什么都抓不住的绝望,那天天气很凉爽,连上帝都在忧伤。
我抬头看了一眼无望的天空,一朵厚重的云彩在流动中迅速闪了一下,变换成一抹血腥的红,然后恍然不见了。这是姐的灵魂吗?她变成一朵云彩,自由的云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