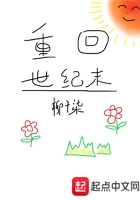终归时间还是散漫的,这样散漫的没有一点生机的日子让我在空虚里一遍遍的呼吁:如何才能让生活有意义?什么样的生活既可以满足内心的的舒适又可以符合自己的价值观?但没人听得见我内心的焦虑,我的焦虑,正在像蔓延的的癌细胞一样疯狂的扩散到每个角落,而我却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它们一步步吞噬我的身体无能为力。
我记得好像是上初中的样子,学校里有一棵树,到了夏天的某个时令会结满鸡蛋大小的果子,它的叶子很宽,树干在浅绿中透着许多白,果子是绿色的上面还有很多细碎的小点,我一直以为那是梨树,一直到我毕业再到我上高中时,可心偶尔说了一句我们初中的核桃树砍到了,我惊讶的问是那棵离办公楼很近的吗,她说是啊砍倒了。要不是她说起来可能我一辈子都不知道它的果子其实是核桃,更不会知道它是梨树,原来那些年我一直活在自己的错觉里。
刚好那时我在一个网站上遇到了一个痴迷中国文化的西班牙男孩Otto,他想学汉语想来中国,由于时差,他午休的时候我刚好吃完晚饭,就借着这段时间聊一会天,他说西班牙其实没有想象的那般美好,和世上所有的国家一样,大城市里的人口庞大,交通拥挤,有处理不完的垃圾和犯罪,富人们骑马,晒太阳,打高尔夫,穷人们忙工作,忙家庭,为生活奔波。
其实我想说的是,西班牙就像那棵心中的梨树一样一直被我错误的看待着,如果不是可心,如果不是Otto,可能我就一直错下去了,可是即使如今我知道了那么多年的误解又有什么用呢,没人知道在那棵“梨树”下我一次次的盼望着它明年能开出白色的花来,没人知道我所谓的语言优势也是出自对马德里的向往。
我和崔明似乎有一种一拍即合的默契,自从那次帮他整理稿件以来,我就在心底默许了他后来频繁的和我共用一张桌子出现在图书馆,只是我们的课表有一些出入,有时候我去自习对面的椅子上完全没他的影子,而我们碰巧都没课时他还会问起来怎么昨天晚上你没有来。
没过多久我们便摸清了对方的自习时间,比如我周一全天都有课就不过去,而他下午没有课就去学习一会,周二晚上我们都没选修就经常碰在一起,双休日时我总是在宿舍睡到昏天暗地,有时候去逛街上网,他一般会去打球或者和一帮男生出去,特别无聊的时候才想到去图书馆坐会,如果桌上的那一摞书被移动了位置就说明他曾去过那里,因为我离开时总是总是把书整理好摆在桌子中央,而他习惯放在左边一角并且在最上面的一层放英语词典。我们碰到一起的时候我告诉他这张桌子原本是我一个人享用的,你如果想平摊一半的话就必须按照我的习惯走,把书放在中间词典放到下面,每次他都信誓旦旦的答应,每次我去的时候桌上就一团糟。
唯一能让我容忍他这个恶习的理由就是我能随心所欲的在他一档广播里点几首我喜欢的歌或者给他一段优美的文字让播音员在夜间读给我听,我的要求简直对他是莫大的帮助每次他都有求必应,但我从没接受他的邀请和他一起吃饭,但有一次还是在整理稿子的时候他买了几只冰淇淋我吃的很开心。
比起没课的时候和舍友们一起出去瞎转,我更喜欢和他一起做点什么来消磨时光,,我总觉得舍友们的叽叽喳喳像一群要关进笼子的麻雀,不是抱怨哪个老师留的作业多就是为下一顿吃什么发愁,而我和崔明之间的交流恰好跳过了这些生活中琐碎的小事,而是一些电影,音乐完全脱离了物质之外的心灵上的享受。还有一天,我们工艺课要做男子衬衣,班上的女孩都打电话给自己的男友说要亲手做一件衣服,个别几个人量了爸爸的尺寸说第一件衣服要做给爸爸,我第一个人想到的是佳佳,然而手中没有他任何身体的数据只好作罢选择了一个固定的男子原型,一米七五的身高。我买了一匹竖条细纹的浅蓝的棉布把裁片整理好,一片片的熨烫,缝合,在做好之后交给老师检查,老师说成品工艺很好,要给某人穿吗?我说没有,没人要穿,她遗憾的摇摇头,那真是可惜了。
正好崔明顶替了一回播音员在广播里为我选了一首歌《LOVE STORY》,因为先前我提到过TALOR长得真让人羡慕,我听到之后感谢的说,你送了我一首歌我也送你一样东西吧,衬衣一件,上课时做的不知道你能不能穿,他毫不客气的拿了过去并说下次做男士衣服的时候干脆做给他好了,我说你想的真美。可谁都没想到,以后所有的男士服装,我都做给了他。
这样熟悉下来之后一来二去的我也就不介意他那屡次不改的臭毛病了,只是很多情况下,我看到他会想起佳佳,思念一个人的感觉很忧伤但也很美,我正是从那种思念里感受到了常人不曾察觉的美丽所以心甘情愿的让旁边多一个人,尽管他自己不知道,他在我心里只不过是一件能唤起往事的工具而已。
一个晴朗的下午,我们从图书馆出来路过路边的一棵法国梧桐,它繁茂的枝干向四处延伸着,宽大的叶子像一张强壮男人的手掌,我说,那里面有好多青草,去树下坐坐吧,他尾随我踏进那片草坪,我靠在树旁,远处几株斑斓的花朵吸引了一群群蝴蝶在四周翩翩起舞,我轻轻地走过去,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居然看见了家乡熟悉的月季,我惊喜的大喊快来看,是月季,草地上生出了月季。他跑过来蹲下去吓跑了几只蝴蝶然后慢慢嗅了几下说,挺香的,我说我要把它画下来,于是拿出纸和笔坐在了随身携带的一个小本上趴着膝盖认真的勾勒起来,他也坐了下去在一旁静静地看着,就是那样一个安详的傍晚,我仿佛置身于蓝伊公园的那片花海里,在那里,我和佳佳一起徜徉并幻想着以后的甜蜜生活,在天黑之前默默地许下一个愿望,希望永远和他在一起。
我边想边画不一会便混淆了思想和现实差一点就躺在了崔明的腿上,幸好在我快倒下的一瞬间眼前出现了高耸的教学楼,它一下提醒了我这里是繁华的大学生活不是那个日益萧条的小城浪漫,眼下的花也不过就三四朵,不是成片的花世界,我使劲的摇摇头把脑海中的昨日意识转移到今天,收好纸和笔,对他说画好了走不走,他站起来稍微提了一下裤子说,走。
后来的日子依旧如水,我学着没事的时候去操场听广播,去图书馆和崔明一起整理稿件,只是意外的一天姐找到我的学校地址提着一些零食和我爱喝的茶叶来看我,我至今都不明白那几天是如何度过的,也不清楚为什么她会大老远去学校找我一次。
在学校东门,明显瘦了一圈的她在人群里笑靥如花,一颗白色的贝雷帽俏皮的顶在头上,我简直不敢相信她如此美丽。
“姐,”我犹豫的走过去,惊讶的不知说什么好。
“怎么,不认识我了?”她张开双臂,迎来一个大大的拥抱。
“疯丫头,在大学滋润死了吧,”孟勇也亲切的拍拍我的肩膀,“珍珍早就想来看你了。”
我陪他们一起去开房,那天出了一个小笑话,姐执意要两间房,而孟勇觉得一间双人房更合适,姐说,要一间房小诺睡我们中间啊,你别想打扰我和她说说话或者联络革命友谊,他听后小声的嘀咕,你又没说和小诺一起,我看着他们一唱一和好像是我不在的时候又偷偷地发展了一步。
带他们参观我们的教学楼和图书馆,教学主楼有十二层,九层以后都是领导的办公室,楼下整齐的停着各类的的轿车,她说学校里的老师真有钱都开着私家车来上课,我说每个学校都是这样的。图书馆建的比较艺术,像是在建好的基础上又调整了一下,因为它每面墙都不对称而且对应着一扇大大的弧形的门,乍一看像个博物馆,而且里面的藏书不是很多,虽然也有五层但是书的种类特别少,好多都是好几年前的了,几乎看不到近两年来新出版的,然而尽管是这样倒也能满足大多数的阅读需求,很少有人在图书馆的建设上提意见。
“你平时经常泡在这里面吧,”她随口说道,“图书馆是一个经常邂逅爱情的地方。”
“我每天都来这,因为没课时我没地方去,”我耸耸肩,很不愿意告诉她事实,“但从未遇到过爱情。”
她转过去,一张张干净的桌子上凌乱的摊着几本书,几个男生围在一起趴着睡觉,还有几对小情侣在监控器下若无其事的缠绵,旁人装作没看见的样子继续来回穿梭。任何一个人,当第一次面对我们敞亮带有浓浓书香的图书馆时都会感到一种知识的召唤和贪婪的渴望,而慢慢习惯之后那召唤的声音越来越微弱,渴望的心态越来越平淡,直到麻木。因为所有的心都会疲惫,当习惯了之后就会疲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