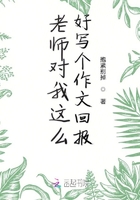月红灿灿一笑,忙回:“奴婢自作聪明了一回,不自量力在贵人面前卖弄贱思了。”月琴不安打量着她,她侧开眸去,月红摆了摆手,示意月红退下,月红这便退下。
月红退下后,月琴上前低声提醒:“奴婢斗胆,也想提醒贵人一件事。”她未语,月红不安续说,“奴婢想贵人去赵宫人那里也是次次碰壁,想来这次即便贵人过去了,这赵宫人也是不愿意见贵人的,何况贵人身子惧热,这来回的折腾别伤了腹中的皇子,到时令陛下更为忧心就不好了。”
她细想了一下,月琴的话有道理,对玉儿道:“玉儿,那你一个人去看望婉清,顺便去一下冯贵人那里,再去一下韩贵人那里,将陛下今日听到赵宫人皇嗣有事时,陛下的紧张无意让两位告诉给各位,如果她们真是为了陛下好,有些事情就该知道各自该怎么做了。”
承制再度欲要说话,最后还是作罢,玉儿点头已是飞快跑开。
月上枝头,清明似水,她让承制搬出凤榻稍歇在院中,辰空璀璨,四处转来夜虫的鸣叫声,在低低的清唱,婉如一首引人入梦的童瑶,引人舒适而又引之遐想,就在乘凉之迹玉儿慢吞吞回来,脸色略有几分不悦恼怒之色。
看玉儿这模样,她自是心下了然,定是没碰到好果子。
玉儿缓了半晌,方才低声委屈道:“小姐放心,婉清的胎保住了,冯贵人说会多留心婉清那里的,韩贵人盯着奴婢看了半晌,冷笑一声就走了,奴婢想婉清的事应是与韩贵人无关。”
她有想过是韩蔓儿,因为除这宫里韩蔓儿最有可能会报复,可现下并不是韩蔓儿,那会是谁?刘灵?不可能,按此前刘灵的态度,那样子与神情实在不像作假,何况刘灵这时也没有必要这般,又见玉儿气鼓鼓的模样,疑惑问:“那你怎么还一脸不舒服?”
玉儿不由得脸色涨得血红,嘀咕着回:“奴婢是没见着婉清,就被她身边的人给骂了一通,那些人还把奴婢给赶了出来。”
月隐出声念道:“这赵宫人身边的人也当真是强悍,竟是这般明目张胆的不将玉儿姑娘放在眼里,也不怕得罪到咱们贵人。”
玉儿脸色不悦说:“哪是她身边的人强悍,这本就是她的主意,她不乐意见就不见,屁颠屁颠的还让我们担心她,真是气人,每每都是这样。”
她握过玉儿的手,不由乐道:“你就嘴里说着气人,心里只怕是念得紧。”玉儿恼得将手抽回,眼睛不由得就红了,她轻叹一声,劝说,“好了,不生气了,气哭了自己可不划算,这可是你自己常说的。”
玉儿抬眸,眼泪汪汪的,方才如实道:“奴婢去的时候太医正好出来,听他们嘀了一句‘按赵宫人这情况下去,这胎只怕是保不住了。’承制说得一点也没有错,奴婢这心里是着急,可她又不让人见,这得怎么整?”
她心下忧,不安问:“太医还有说什么?”
玉儿头疼三分难过七分,擦掉眼泪回:“太医也没有多说,可是奴婢听出那意思,是婉清的安胎药有问题,摆明就是有人在做手脚!”
她了然明白,拍了拍玉儿的肩,转而看向承制,承制灿灿一笑,不安问:“贵人,您别这样瞅着奴才,奴才什么也不知道!”
玉儿不悦吼道:“我看你不是什么也不知道,你是来了我们这里心不在我们这里,知道也不会告诉我们什么!”
承制脸色一白,猛然跪下:“玉儿姑娘这可是冤枉奴才了,奴才虽是此前在韩贵人那里服侍,可是自从奴才过来贵人这里,这自然心也是要向着贵人的,奴才所说的一切都是为了贵人着想,奴才是不想贵人躺这混水,想那赵宫人也是这般想的。”
玉儿咬唇,月琴上前劝说:“是啊,承制的心月琴看得也很明白,赵宫人的态度奴婢们更明白,玉儿姑娘这样说,可当真是要寒了承制的心了。”
玉儿压下怒气,低声抱歉道:“对不起,心里着急就说了这样的话,承制,你见谅点。”
她淡淡道:“你先起来再说,你的心是向着邓绥,邓绥心里清楚,何况你说得没有错。”
承制不敢起来,她示意玉儿去扶,玉儿上前扶承制起身,承制方才敢起身,道:“谢贵人明察。”
玉儿松开承制,走来望着她头疼道:“小姐,婉清这样实在让人头疼,宫里人对她现在都是能避就避,咱们每每去看她,可最后每每都被她赶出来,小姐此前让云荀在婉清耳边提婉莲姐姐与伯母,可这个法子根本一点用处都没有。”
她双手在太阳穴按了按,沉声道:“我也正为这事感到头疼。”
玉儿不安又问:“小姐,有没有什么其它的法子?”
她按了一会还是觉得头疼,续说:“你容我再想想。”
承制犹豫片刻,撑着胆上前劝道:“贵人,承制大胆再说一句,赵宫人也是希望您不要再管她,您这一头热的要管,且先不说管不了,您再多管赵宫人的事,只怕会让不少人怀疑,曾经就是你使了主意,让赵宫人去缠媚陛下,是您与赵宫人在玩花样,宫里不少人看您现在总去找赵——。”
月隐见她眉头微皱,上前低声打断道:“其实奴婢是打心眼里敬佩赵宫人,可是赵宫人看事看得透彻,这才从一开始与贵人摆了这样的态度,想来就是为了贵人好的。”
她凝眉瞅着两人问:“如果你们是婉清,你们换着方式转安了邓绥的处境,最后你们想一死解脱,还不想连累于邓绥,最后邓绥就真的眼睁睁看你们去死?为这样的人做这些,你们难道不觉得悲哀吗?”
月隐正要说话,月琴拉了月隐一下,上前温声笑劝:“贵人您别生气,咱们都知道贵人与赵宫人姐妹情深,承制与月隐是觉得赵宫人如此,咱们也是没有法子,这才不想贵人总为这事忧心。”
她垂下眸宇,不自信喃喃念道:“要说完全没有法子也不是没有,只是这个法子我也不知行不行得通。”
玉儿一喜,欣然就问:“小姐的法子是什么?”
她还未开口,余眼就瞅见刘肇过来,微怔,本是以为刘肇今晚会陪着婉清,瞅着刘肇那暗自隐忍的神情,她忙迎上去屈礼:“陛下。”刘肇神情未动,只是摆了摆手,她小心打量刘肇神色,转而不安问,“陛下是在忧心赵宫人的胎?”
刘肇眸中三分怒火七分不喜,沉声道:“这个婉清当真是不知好歹,朕没怪她此前的过错,她倒转眼责怪起朕的不是,真是胆大包天。”她心中不安,刘肇顿了顿,闷声自问道,“这股风气是什么时候形成的?看来这后宫是得好好治治才行。”
她泛了泛眸,思量着不安问:“不知婉清因何事责怪陛下?”
刘肇瞅着她目露提醒,沉声道:“她说,朕在意的是她肚子里的孩子,还说现下有这么多妃嫔有喜,孩子多她的一个不多,少她的一个不少,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敢拿朕的皇嗣危协朕。”她咬了咬唇,刘肇再次提醒,“你的这个丫头没药可救了,朕也劝你离她远点,免得再次惹祸上身。”
她轻叹一声,垂下眸子幽幽道:“早在她以那媚姿相迎时,陛下就该知道她已经无药可救了。”
刘肇语气一凝,略有几分杀意,出声说:“朕就是现在下令处死她,以敬宫里的不正之风,朕也是足够对得起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