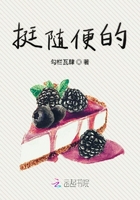蓝沁带着宫女们来到后殿,郑旦已经被阿娘打扮得焕然一新,是夫差喜欢的样子,孔雀蓝色软纱长裙里面只有一袭紫粉色绸缎褒衣护住身子,肩膀和修长的腿若隐若现,两只胳膊如同白玉一般露出来,在早春寒夜里瑟瑟发抖,头上一支粉色芙蓉花娇艳欲滴,只是胸口仍是那枚白玉佩,显得不太协调。
阿娘看蓝沁的目光死死盯着白玉佩看,也发现了不对劲,立刻过去抢夺:“摘下来,这么寒酸的东西怎么配带到大王身边。”
郑旦立刻双手护住胸口,虽然憎恨西施与范蠡,但是她仍旧将玉佩戴在了胸口,这是范蠡的玉佩,仍旧有他的温度。
“阿娘,算了,戴着吧。”蓝沁又看了看,说,“这妮子倒也的确适合素素净净的装扮,给她换几件浅色衣服。”她走过去摘下粉色芙蓉,拿了一支素馨花给郑旦插在头上,左右端详,“不错,这个玉佩虽然寒酸了些,可是戴在你脖子上却格外有一番风韵。”
郑旦闻言得知玉佩仍旧可以戴着,放松下来,宫女们不等她自己动手早就把轻纱宫装和粉色褒衣脱个干净,她就这样****着在这些人面前被迫失掉一个少女最珍贵的与童贞一样重要的尊严。
白嫩如玉的身体刺激了蓝沁即将老去的心情,周围都是虎视眈眈的威胁,她急需郑旦这样年轻白皙柔软的身体填补夫差身边自己空出来的床榻,又不会威胁自己的位置,她瞬间捕捉到郑旦最美的样子,挥挥手阻止宫女们给她穿衣服:“不用穿了,就拿我那件素锦寝衣给她披上,待会儿用暖轿直接送到大王的锦衾里。”她走到郑旦面前,“这样儿好看,大王喜欢,这玉佩是你妈妈给的吧,很衬你这样空谷幽兰的女子。”
郑旦低头不语,她的尊严已经麻木了,自从进了吴国,先是息泗践踏了她国家的尊严,继而是三番五次被人脱去衣服在这些宫女嬷嬷面前被敌意地摆弄,唯一能够温暖她的是这块玉佩,范蠡曾经珍藏在身边的玉佩,他一定带着无比温存的心情抚摩着它,可以感受到他手指冰凉的温度,却只是冰冷的告知她,爱情无处安放,她有一种冲动,毁灭一切的冲动,忽然抬起头:“君夫人,我有话说。”
“什么事儿啊?”蓝沁不以为意。
“如果是关于细作的呢?”
果然这个话题撩拨起蓝沁的兴趣,她摆摆手,宫女们都退下了,说:“说罢,我想听。”
郑旦却不知道该如何说起,说出西施与盈姬的身份,换取自己的痛快,看她们人头落地,看越国灰飞烟灭,可是自己呢,自己要到哪里去,死了殉葬给范蠡,还是怎样,她无语了。
“郑旦,你是不是知道什么呢?”蓝沁逼问。
“我不是奸细。”郑旦被范蠡的玉佩温润着,凉却是暖的,她在一瞬间选择了保护他,纵然多情被薄情辜负。
蓝沁笑着挥挥手,阿娘端着一盘金子进来,她轻轻嗓子,说:“这个是给你的。”
“我不要,要了也没有地方去用。”
“宫里当然没有地方去花,可是将来出了宫总有地方可以花的。”蓝沁笑了笑。
郑旦听到“出宫”眼睛亮了亮,说:“君夫人说我还可以出宫?”
蓝沁走过去,拍拍郑旦的肩膀:“当然可以出宫,还可以送你回越国,本宫是通情达理的人,我也可怜你们这些个越国的贡女,国破家亡颠沛流离到这里来受人凌辱,没有尊严没有地位,如今年轻有个身子能让大王开心,将来老了当然是出宫去最好,这些年凡是听话的越女我都会赏些钱,等到大王不喜欢了想不来了就悄悄把她们送走了,或者,如果你的心上人还在,你就可以和他在一起。”
这一句话沉甸甸落在郑旦心上,或者,如果可以出宫,如果没有西施,如果没有吴越之战,或者,范蠡可以不遇到西施,自己可以嫁给范蠡,一切的绝望从这一念而起。
蓝沁步步紧逼:“郑旦啊,我是实心实意对你,你不是大王喜欢的样貌性格,在吴宫里出头不那么容易的,不过,如果你能够帮到我,我也是可以保证你后半生无忧无虑的,来吴国之前有没有喜欢的人啊?过上个三年五载,我就放你回去了。”
郑旦是公侯家里长大的女孩子,她知道蓝沁这种贴心贴肺的样子是假的,但是心底的爱恋强烈地暗示她,或者用西施与盈姬,可以换来半世安稳与范蠡的相守。
蓝沁从郑旦的眼睛里看到了游离与抉择,乘热打铁:“我的需要非常简单,只要你把一起来吴国贡女的底细告诉我,保证她们不会做出通敌卖国的事儿,替我看住她们的一言一行,我答应你三年之后就可以出宫,你今年十四岁,那时候也才十七岁啊,花骨朵一样的年华。”
郑旦在心里纠结,蓝沁的话起了作用,她的确艳羡这样的收梢,一句话就让西施或者消失与无形,自己就是天地间唯一陪伴范蠡的那个人,她的手微微颤抖着,忽然抬起头,说:“君夫人,我是有事情要告诉您的。”在这一瞬间她决定背叛,从来都是被安排的生活,被安排作贡女,被安排失去爱情,今天她可以自己选择。
蓝沁满意地点点头,说:“好,慢慢说。”
郑旦正要张口,宫女来报大王已经看完了奏折就要睡了,蓝沁打断了她:“先去侍奉大王,回来慢慢说。”话音才落阿娘与几个嬷嬷熟练地将郑旦裹进被子顺势放进了暖轿里,蓝沁做这一切用爱的名义,为了保有自己的爱,顺理成章。
郑旦打定了主意做一个国家的叛徒,用爱的名义,亦顺理成章。
郑旦裹着锦被抬上夫差的床榻,胸口的玉佩微凉,想到接下来的事情紧紧闭上眼睛,一直在鼓励自己或者可以把这个男人想象成范蠡,但是刚刚过去的一切给了她新的契机,或者,可以保住自己的贞洁,留给范蠡。她不知道如果自己背叛了国家与西施是否就可以和他永远在一起,背叛了这些不应背叛的人范蠡还会要自己吗?范蠡那样爱越国忠于大王,可以把心爱的女子送到吴国供夫差蹂躏以换取复国的目的,他会恨死背叛国家的自己,想到这里郑旦下定了决心,要赌一次,如果赢了就可以天长地久,如果输了也不过是失去本就没有得到的东西。
脚步声轻轻地渐渐近了,一股甜香馥郁渐浓,郑旦不敢乱动,紧闭着眼睛,夫差带着期望深处一支微凉的手掀开锦被,带着夜的味道,他无数次想象能够在自己的床上看到那个叫西施的姑娘,掀开锦被后看到她的脸,紧紧把她放进生命里自此好好珍藏,但是每一次都如今天这般失望,他积蓄的怜香惜玉无处释放,又变成那个孤傲的吴王,淡然被子,离开床榻,背对着郑旦,说:“起来给孤王宽衣。”
郑旦连忙掀开被子轻手轻脚下床,寝衣只有一根丝带系着,稍稍动一下就春光四泄,只好动作小心的左右虚掩住身体,不敢大动作,偷眼抬头,夫差没有想象中那样的老,那样的鲁莽,反而像一个斯文的诗人,带着一点点忧郁,还有一种属于王的烦躁,冷而难以接近,她慢慢地为夫差脱衣服,思索该如何说出属于自己的秘密,换取可能的胜利。
夫差心不在焉,任由面前的女子侍奉衣服一点点褪下,寝衣根本遮掩不住她的身体,随便一个动作就春光咋泻,身体里那种属于本能的冲动就被调动了出来,他一把撕去郑旦的薄薄的寝衣,捏着她光滑白嫩的肩头,另一只手抬起郑旦的下巴,修长的拇指掠过朱唇,说:“亲我。”
郑旦木木地没有任何反应,此时此刻她一个心里全是范蠡,如何与范蠡相见,如何与范蠡相守。
如果这个女子是西施,夫差一定有千种温柔引导她与自己共赴缠绵,偏偏就不是,面对一个又一个女子,夫差的怜香惜玉早就被消耗殆尽,郑旦的木讷让夫差觉得很没有意趣,他期待多时而不得的烦躁变成只有君王才有的暴戾,这种暴戾被男人的本能驱使着让他有一种摧残面前这个女子的欲望,夫差反手拉住郑旦的头发将她丢在了龙床上,一把分开她的身体。
“啊。”郑旦吃痛,惨叫一声,连忙拉过被子盖住身体。
夫差一把掀掉被子,掐住郑旦的脖子,问:“文种范蠡就是这样训练你们?不解风情不知进退?”
“大王容秉,奴婢有隐情呈报。”郑旦咬咬牙,她在衣服被再一次剥光的瞬间打定主意,即使没有范蠡的爱情,即使万劫不复,也要保住自己最贞洁的身体,这样纵然有一天黄泉路上与范蠡相见,也是有资格与他相爱相守的。
夫差的兴致一下子没了,拿起地上的寝衣劈头盖脸丢过去,冷冷地说:“你倒是给孤王一个好好的解释,否则孤王就要勾践来解释。”
郑旦咬着下嘴唇,穿上寝衣,寝衣只有一根腰带,无论怎么系都遮不住身体,她只好匍匐在地上,尽量掩盖住身体,低着头,慢慢地说:“我们十个越国贡女中有奸细。”
“奸细,孤王已经知道了,息泗不是处死了一个吗?是同胞姐妹的死吓住了你吧,好好陪孤王,你不会死的。”夫差拿起酒樽一饮而尽。
郑旦想起花祭的惨死,瑟瑟发抖,顺着夫差的话回答:“的确,花祭的死亡让奴婢兢兢战战,可是奴婢知道花祭并不是奸细,物伤其类,奴婢也怕被人妄加猜测横遭不幸。”
“说得有些道理,然后呢,你就不好好侍奉孤王,以证明你不是奸细。”夫差饶有兴味,“其他的越女可是都巴不得好好侍奉,以证明自己对孤王,对吴国的忠心呢。”
郑旦沉了沉,恭恭敬敬地说:“息将军让奴婢与同来的姐妹彼此监视,奴婢为此日夜悬心,今天大王传召侍寝,奴婢万分荣幸,可是刚才忽然想到同来一位姐姐的行事作为,很是狐疑,是以走了神,大王赎罪。”
夫差的眼里闪过一丝冷光:“我就知道勾践这个匹夫不会善罢甘休,我留着他一条狗命就是看他会如何兴风作浪,你说罢,把你知道的全说出来。”
郑旦稳了稳心神,说:“同来的一位姐妹,西施形迹可疑。”
“西施?”夫差眼里的寒冷杀气变成一泓温润,“那个浣纱西施?”
“西施早已不是浣纱女,文种大夫看重她美貌机制,收了她作义女,这一路上她不惊不慌沉着冷静,一心教导我们不能忘记自己是越国人,要想着国破家亡的深仇大恨。”郑旦想着先制西施与死地,但是也不能说得太实在,否则自己也撇不清干系,她明白一点点暗示就足够了,先是除去西施,而后再接受蓝沁的条件作三年卧底,而后出宫回越国,与范蠡长相厮守,人算得准一切,却算不出天意,郑旦千算万算的小算盘里就是没有夫差的爱情。
夫差闻言大怒,他好恼,自己一直不肯指明要西施进宫就是生怕文种与范蠡将她训练成奸细,所有人都可以是,唯独她不要是一场战争两个国家的牺牲品,她只要仍旧是那个最纯洁的女子,让他遇到、珍爱、携手白发永生永世即可,为了保护这份纯洁,他足足等待了三年,每年都有大批的越国女子被源源不断地送进吴王宫,他从不说足够了,因为他总是盼望着能有一天西施就在她们中间,直到作为一个年轻情郎所有的期待都变成一种黯然失色的时候,她仍旧被人一身污浊地送来,可是如今他太失望了,夫差愤怒地拍案而起:“不杀勾践、文种、范蠡,难以平孤王心头之恨。”
“大王赎罪。”郑旦忽然就迷茫了,她一个小小女子的心里装不下这样复杂的权谋,她只是知道西施是奸细就杀死西施,没有想到其中还有范蠡的干系,连忙解释,“大王,奴婢也不知道西施是不是奸细,只是觉得她行迹可疑,常常说些思念家乡,讨厌征战的话。”
夫差闻言稍稍宽慰,没有人喜欢背井离乡,没有人喜欢连年战争,何况还是战败的国家,还要做敌国最卑贱的贡品,他从愤怒里游离出来,清醒地意识到西施终于来到了自己的身边,这是一件多么令人快乐的事情,他要,早早地,与她相见,说罢他起身就要往外走,看到了匍匐在脚下的郑旦,用鞋尖勾起她的脸,冷冷地说:“今天的话不许对旁人提起,西施是不是奸细,孤王自有定论,如果有流言危及她的生命,拿你治罪。”
“是。”郑旦为了这场风波的平息长吁了一口气,保住范蠡就是保住自己的爱情,但是也有一股醋意,西施竟然这样好,连夫差都会维护她,不过她又产生了另一种希望,如果夫差爱上了西施把她长长久久地留下,那么自己仍旧是胜利的,正在想着,早有宫人拿着衣服过来扔给她,监督着她尽快离开夫差的寝殿,在她们眼里,纵然是被大王临幸过,也是卑贱的越国贡女。
夫差的世界里早就不再有一切,只有一腔奔赴西施身边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