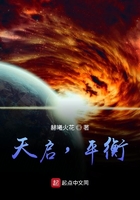猛然回头,见桌几旁坐着一个女子,姣好面容。在这样的情景里,依然是面善至极,眉目间任是那样的温顺柔情。
“候你多时了。”床榻上的男子轰然做起,一直臂膀裹着厚厚的白纱布,妠容断定他定是宴越之。
妠容阴冷的目光狠狠的扫了扫两人,依旧没有一句言语。
妁慈站起身来缓缓朝妠容走去,那股少有的霸气瞬间涌出:“你是谁?你为何来宴府。”
妠容双目直射着眼前的女子,一个华丽的转身,紧紧的将妁慈圈在了自己臂中,小铡刀稳稳的扣在了妁慈的颈边。
“放开她。”宴越之从床榻上跳了下来,焦急万分。妁慈望着宴越之,蹙眉转动了一下眸,宴越之却又像泄气的皮囊,缓和了下来。
“为何不叫?”妠容刻意抖动了一下手中的铡刀,使得刀尖离妁慈雪白的颈部又近了一点。听是个女子的声音,宴越之越加迷惑,焦急万分,却见妁慈给自己的示意,莫轻举妄动。
妁慈脸颊因怯怕微微发热起来,佯作镇定的回道:“我知道你定不会杀我。”
听了妁慈的言语,妠容放下了手中的铡刀。再看妁慈之时,其眸中的坚毅和倔强同当年再长春宫里与自己抗衡的小宫女一模一样。妠容在桌几旁静静的坐了下来,捻起桌上的茶杯把玩起来。
妁慈和宴越之相视一笑,显然是意料之中的。
妁慈和宴越之也随机坐了下来,妠容这才看清宴越之的容貌,青丝未绾,俊俏飘逸,神态稳重,气质沉静。眉眼似墨画之出,鼻唇如雕刻之物。
宴越之伸手要摘妠容蒙面黑布,却被妠容挡在了腕间。妠容看似轻巧地扭动了一下手腕,猛地将其手臂朝后一推,宴越之受伤的臂膀为之一震,剧烈疼痛起来,忙按住了伤处。
“越之!”妁慈忙立起跳到了宴越之身旁,满脸的怜爱。
妠容任然不爱多言,肆意的瞟了两人一眼,连一个多余的字眼也不愿言出。
妁慈泫然之态着实让妠容诧异了一把,宴越之不过是区区小伤,就惹得她这般柔肠泣泪的。
蓦地,妁慈大步走到了妠容身旁,语气硬冷道:“我想知道是谁派你来的。”
“太子!”妠容冷冷回应,如霜似冰,语气里不夹杂一丝情感。
妁慈眼眶瞬间噙满泪水,脑海中本残留着的最后一丝期盼都消纵即逝:“果真是他!”
“我是邵妁慈,拿我回去复命。要杀要剐悉听尊便。”妁慈怒火四气,心底的噪杂终于发泄了出来,更不想连累宴府众人。
宴越之忙接过话尾:“她是妁慈不假,但她失忆已久,至今未愈。”宴越之极力挽救爆破的局面,哪怕没有任何一丝的希望。
妠容黛眉轻轻一颤,双眼略弯若月,说道:“今夜,我不曾见过邵妁慈。”随后摘下蒙面黑布,笔直伫立在宴越之面前,轻吟冷笑:“你欠我一个人情,改日再讨。”
说罢,便打开房门,潇洒而去。
摘下面纱的那一刻,妁慈才知,所谓奉太子之命,绝不是信口雌黄。且除了她,何人能这么洒脱的去讨这样一个人情。
“姚妠容!”妁慈默念了一遍她的名字,既知,紫禁城里一场腥风血雨又要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