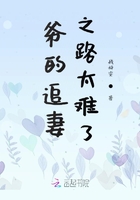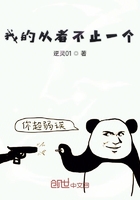“宸妃?”朱见潾轰然从凳子上站起,一脸惊愕。
“妁慈!”宴越之怔住,见妁慈脸色苍白,万想不到她这般虚弱却来这里。心中有一丝喜悦,可更多的却是恐惧。
妁慈静静的注视宴越之不安的脸,焮了焮干裂的唇,哽咽的问道:“是你做的吗?”
宴越之垂眸不敢再看妁慈的脸庞,缓缓的点了点头。
蓦地,妁慈大步上前,朝着屏风旁走去,伸手拔出了剑架上的长剑。笔直的朝着宴越之的胸前刺了过去。
妁慈的眼中激出了一道道血丝,幽黑的眸如深渊,狂吼了一声:“啊……”
宴越之痴痴的站在那里,任由妁慈手中的剑朝自己刺来。
朱见潾大惊,拾起桌上的折扇朝着妁慈的剑柄上投去。可妁慈手中的力道之猛,将折扇狠狠的弹了出去。剑尖稳稳的插在了宴越之的胸前,宴越之被推怂的退了好几步,猛然撞在墙壁上。腿旁的木凳轰然倒下了一片。
溅着血渍的衣裳,格外显眼。她的手颤抖着,她以为他会解释,至少也会闪躲。
朱见潾忙上前环住妁慈身子,妁慈手中的剑猝然拔出。宴越之闷哼了一声,胸前的疼痛使得他再也直不起腰,轰然倒在了墙角。
妁慈狠狠的咬着唇,所有思绪又回到了那个夜晚,宴越之扯下自己的棉袄斗篷,朝着黑衣人甩去。那一刀划下,漫天飞舞的棉絮。宴越之将自己捂在怀中,挡下了那突如其来的一刀。
暖阁的香薰,熏的妁慈昏昏沉沉,她望着宴越之歘白的脸,心里却是那般撕心裂肺的疼。
“为什么?”妁慈沙哑的问了一句,哽咽的再也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为什么……害死……我的孩子。为……什么?”
宴越之双手撑地,缓缓的站立了起来,冷冷一笑:“我无法容忍,你怀了其他男人的孩子。”再多的解释都是茫然,只有这个答案,最能说服她。那便这么说罢。
妁慈手中的剑划落在地,哐当一声。沾满血渍的剑锋泛着光晕,妁慈能看见剑上反射出了自己的样子,那么扭曲,那么残忍。
巧果捂着嘴,滑步到宴越之身旁,手足无措。只能卷起宴越之的袍角,捂在他拼命冒血的伤口上。
“是他救了你!”朱见潾死死的环住妁慈的身子,害怕自己一松手她便倔强的捡起剑。
妁慈扭头,疑惑的望着朱见潾正气凛然的脸,嗓中哽咽出几个字:“我如今……生不如死。”
她终究不懂这之间的对错,更不懂男人心中的取舍难分。她只是一个女人,一个想保全她腹中小小躯体的母亲。其他的,她再也顾不上。
心乏了,再怎么休憩,也难以康复。
朱见潾只感觉怀中的妁慈,身子越来越僵硬,她拼命的颤抖着。
宴越之又瘫坐在了地上,努力靠着墙壁支撑着身子。巧果的手被鲜血染透,刚放上去堵血的衣裳,瞬间被侵湿。
妁慈妁慈挣脱开朱见潾的怀抱,痴傻的伫立在原地,静静的看着。
许久,她转身一步一步走出了殿门。
她累了!连恨的力气也丧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