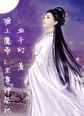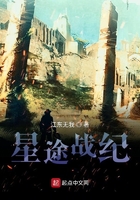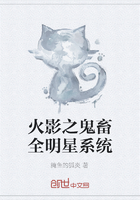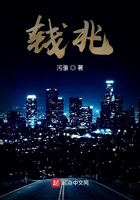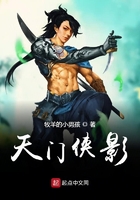但对食兴未尽或正在回味佳肴异馔的人来说,这却不能不是一种灾难:眼缘里闪见一个转过身去的背影,知道他正在剔牙……兴味只能一扫而光。那些用空着的手挡住半边脸的剔客,也无法平息别人的想象,食物……经过……然后……食欲只好倒尽。那些对着餐桌直接干起来的,更加一副生动形态。特别当“叭”的一声,牙物带着腐烂的哨音落在某个无辜的物头上时,你毋需选择,只能走人。
最绝的还是那些拿着牙签把玩的,牙签在他们手里,无异于一颗定时炸弹,不知道他们会在什么时候,什么体态下把牙签戳进什么样的牙缝里去。悬念会一直使你骨鲠在喉,直到脱离那种情境……于是,厌屋及乌,连带对那位奉送牙签盒的年轻人也有所烦厌,觉得他是无事多事。但其实这是冤枉他。因为牙签盒就在桌上摆着,而且还是一位大家都已经多看了几眼的漂亮小姐(按照餐饮规章)送上来的。他不殷勤,别人也会方针既定、主动实施的。为难的是,对付这种自己所不欢迎的局面,却又是只能抵御,无法进攻的。如何抵御?早退?那就十分不礼貌了;不准别人使用?自然也属绝不可能。
不知道别人有没有更拿手的办法,我是如此行事的:第一是抢食,早吃早了,早吃早饱。这样就有了主动权,选择的余地也更大了。当你剔牙时,我已经酒足饭饱,回味隽永过了。第二是加强心理承受能力,对自己的事全神贯注,对别人的事熟视无睹。第三是争取坐到女士们中间去。女士们的干净和文明,是人所共知的。坐在她们中间,除了拘束点和吃不太饱以外,饭菜的真正味道,的确是有条件品味出来的。
除了干净和文明,女士们又确实是机灵和睿智的。如果碰到剔牙的事情发生,除了早退以外(女士们有早退的条件),她们反抗和抗议的水平也很高。她们会天真、不动声色并且谦虚地问:听说剔牙是一个人衰老的开始,是不是这样?
没有人敢于正面回答女士的提问,也没有人会在下一次餐后不顾忌到桌边有女士的存在。女士有一种镇压的力量。进餐时和女士们同桌,无疑是最安全的。
“个体”初记
这些年断断续续接触了一些个体户,大都是见了面一场酒之间即以朋友相称,过后却很难再度相见,绝大绝大多数都是一次性的。他有他的搏斗,我有我的“事业”,隔行如隔山。天涯海角,萍水相逢,即兴投机,分门别类,众生芸芸,苍海一粟,并不要求承担什么。或烦琐地维持着,一次性的结交、收入或者付出,合了商品经济浪潮中新型人际关系的一种,多么轻松而且潇洒呀。偶尔地来了,又偶尔地去了,并不是不留下些微的痕迹的。
四年前我们去一个体户家参观,那家沿街靠路,有一栋三层的楼房,分设餐饮部、住宿部、商品部。后面又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和汽车修理厂。而且这修理厂很快又要与外资联营,将再建一栋大楼,一个大停车场,这家业也够大的了。
交谈间那老板说:摔摔打打十几年过去了,我悟出个道理来:要干小事业你得有一帮朋友,你得靠这帮朋友出力。要干大事业你就得有一帮敌人,事情干大了,敌人自然就多了。敌人多了,就促使你把事情干得更大。这些话我写入一篇小说里去,有时在家间饭桌上谈起一些切身的人和事,自然想起这段话。觉得它是真理,是血汗的经验,在卧室里是想不出来的。
个体的经营者也扮演着双重的或多重的角色。有几个推销药材的,其中一个坐火车到云贵去,行程几千里没有座位,钻在座位底下过了两天两夜;另一个遭到当地痞子的围打,腿上被剌了两刀,钱被抢去三千;再一个女的,大热天带三万块钱上河南做生意,路上不太平,钱捆起来放在裤裆里,到地方钱都腥臊难闻了;又一个,发家初期,每天骑自行车驮四、五百斤货往乡下跑,日晒雨淋,风刀霜剑,三十像四十,面相粗黑,皱纹又深又长。多多少少都发了些,有发得多的。
上个月我们见了一个,他家在县城有一处大宅子,两进院,后院一栋三层楼。楼里装修都是当地最贵的,大理石墙面,水曲柳地坪,红木家具,健身房,电器之类不用说。
酒酣耳热时,他执意要我们从他家打长途电话出去,打到哪里、讲多长时间都行。他家浴室比一个小厅还大,马桶盖部分包金,按摩床是特制的。他又领我们看他的枪,摆在床头的有五支,猎枪、小口径步枪之类,抽屉里有一抽屉子弹,有猎枪子弹,据说一粒就能把人头炸光。有小口径步枪子弹,有手枪子弹,都成包成盒。抽屉里还有自制的手枪,还有刀具,又拉我们到院子里看墙壁上的弹洞。
另有一个也挣得多了,在当地盖了一个四合院式的大楼,里头吃喝玩乐一应俱全,专雇了两个人烧菜做饭,端盘子上碗。出来进去的两个女人,一个年岁大些,是他原配老婆,另一个年岁轻些,粉妆黛眼,关系颇为暧昧。赈灾抗洪他捐了些款,地、县都有纪念物给他。他都放在大大的客厅里的显眼地方。省、地、县的领导来过,他都叫人照相、录像,照片放成巨幅,挂在明摆着的位置。来人就看录像纪实,边看边讲解,颇为自豪踏实。一晚上他输过五万也赢过三万,天南地北他都跑过,名片本有半抽屉,名片有数百上千张,各行各业,各色人等都有。
我见到的这些,其实并不非常特别。据说还有一些,是我们想都想不出来的。到这些“朋友”处,吃了,喝了(我们只有白吃的能耐),说了,走了,年深日久,发现竟也有相当的收益,不是别的,是对社会的感受和了解。
不几天以前到一个县去住了个把星期,突然发现那里挣钱特别容易。见到的每一个农民,都说他家每年收入多少多少,收入五、七千的最多,收入一、两万的也不少,这才知道所谓的“万元户”早成个中性词了。
也可能我是掉进万元户窝里,产生错觉了,也可能现在钱贬值得很了,又可能是社会发展得真快了,不像我们经常埋怨的那样了。
总而言之,往后得常出去跑跑了,见多识广,也好随时调整自己的思路和计划,也好想法子给自己留条后路,也好在出门上街公干行走时心间有个数。别犯了与社会的发展不协调的错误,丢了自个的面子或其它,概言之是得跟上时代走吧。
读书的记忆与联想
人的读书,抛开心情、环境、业务必须不谈,我觉得恐怕都是有阶段性的。年幼时是好奇,年轻时渴求和汲取,过了三十岁是爱好,四十岁以后再坚持读书,那就多半是执着或者固执了。
拿我自己来说,年幼和少年时喜欢读书,跟现在相比,那时候的书有点“少得可怜”。“文革”前“国产”书除中国古典文学和鲁迅外,大都是解放以后的“新作品”。译制品则以“社会主义阵营”的图书为主,不过读起来并不感觉有什么“不足”,也是从中获取了极大的收益。
例如印象很深、现在还能记住的,国产的有《宝葫芦的秘密》、《高玉宝》、《林海雪原》、《李自成》(第一卷)、《青春之歌》、《铁道游击队》、《红岩》等等。
译制品则有高尔基的许多作品,另有一部波兰的长篇小说,叫《前哨》,竟也是给了我极深的印象。暗夜劳动的场面,还颇能激动人心,虽然它看起来那么沉闷,沉闷,沉闷到几乎将人憋毙。
现在回过头去看,之所以认定那时候的文艺作品有这样那样的诸多问题,我觉得与其说主要是作品本身的问题,倒还不如说致命的是图书的结构性的问题。没有参照、对比、竞赛、竞争和相互的影响、渗透,文艺想在读者和观者那里不出“问题”,的确很难。后来到我二十岁左右1976年下放农村插队的时候,图书的结构性问题似乎更“严重”了。与“年轻时渴求和汲取”的欲望相比,那时可看的东西也似乎更少了。但十分矛盾的是,人的“天性”又总是指示人们要自觉不自觉地从纸质上读取一些东西。因此,无论社会上图书的多寡、品相的好坏,书却总还是要看的。
那时究竟能读些什么呢?现在在我的手上,有一份1977年我在“安徽省灵璧县文化馆”办理的“借书证”。从这一年的1月到10月,我从该馆主要借阅了如下一些图书:《列宁选集》、《放歌集》、《锁金峡》、《1871年公社史》、《巴黎公社》、《狱中日记》、《(与苏共论战之)二评、三评、五评、六评》、《放歌长城岭》、《号角集》、《七月槐花香》、《凤凰林》、《马克思传上下》、《论评价历史人物》、《列宁论国家和法》、《论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人间》、《恩格斯传》、《春歌集》、《前进吧》、《庐山颂》、《军垦新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螺号》等等。
那时候的我,或者我觉得那时候的年轻人,主要就读的是这些读物。在某个具体的时代里,你总是只能从身边所能触及的事物里汲取你所需要的、有时候是最低标准的只管不死的营养的,你无法对图书本身进行指责。
除上述书籍以外,我的记忆告诉我,在农村插队的这两三年里,给我影响最大的读物,不是以上例举的图书,也不完全是宿县地委宣传部图书室里的那些外国政治家传记,而是一本“内部发行”的名为《第三帝国的兴亡》的译著的第一部。这是影响了我的一生的一本书,我一直非常庆幸我在年轻的时候就有机运遇到这本书。看起来,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读什么、看什么,对他的一生似乎极为重要。
当然,上一世纪过了七十年代,图书的“结构性”问题有了一定的改观。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物质和科技的发展、介入,也随着传播方式的增扩。“图书”以及文化信息传播的结构性问题面临或者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如果现在还有人诉说接受渠道瘠乏,那他表示的意思一定只是某种“期待”。
但图书太多了就一定不是个问题吗?未及经过时间和观念的筛选与甄别,良莠不齐地“坦然”呈现,这里就真的绝然没有“结构性”的问题吗?只是这种状况的“选择性”会比较舒适一些;这种状况也会使我们中的一些人,有可能进入那种“真正的”读书的状态。这就是我今天坐在电脑前要说的一些话。
秋天以及“春天”
——关于中篇小说《焚烧的春天》
一、写作
1987年的下半年和1988年的上半年,我为了许多事情而疲于奔命:家庭、户口、住房、各种生存和生活的必要的关系和关节。为了保持不辍笔而抛出的数量不少的大部分未经过深思熟虑的小作品(短篇、散文、散文诗及评论文章)等。值得庆幸的是,这些奔命都还很有成效,这样就解除了我面临的和潜在的许多后顾之忧。另外,虽然疲于奔命,经常黔驴技穷,但它们毕竟还是体力上或生存智力内的事,而不是创作上、思想上和情感上的。所以,我并不感到心力衰竭,相反却体会到一种休息的快意。
创作是一种很可怕的耗尽心血的工作,相对于此而言,许多挣钱的、争权的、交际的以及成名的半工作半游戏的行当(或者行为),简直就是太轻松、太享受、太引诱人并且太值得一干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至今仍未死心塌地地决心在文学创作的行当里干一辈子的一个原因。
1988年的7月底、8月初,我从皖西的六安地区回来。在外面跑了半个月,身体很疲劳,但精神却很好。当时,我住在合肥市西北郊四里河的老梁庄,是租住的民房,前后都是大片空地,十分安静。我彻底休息了一段时间,除了半天上班以外,余下的时间我几乎全在床上度过。我每天躺在床上看电视,床上放着许多书,而且都是互不相干的,《凡·高论》、《西方美术史纲》、《动物的建筑艺术》、《世界征服者史》、《第三帝国的兴亡》、《事物的起源》、《战国史》等。
在那样的日子里,我觉得我在某一方面的负担骤然减轻了,世俗的、功利性的、生存的自责感却逐渐加重。我突然产生了抛弃以往的一切作品的强烈念头,这也许是我那段时间睡眠过多所致。以前都是些短作品,唯一的一个中篇《蝗》也才两万字多一点。另外,有一个1985年的长篇初稿被一家出版社压住了,所以,它根本不能算数。我现在想到这一点就感到奇怪:在1988年8月的那段日子之前,我很难把作品写长,它们大多在三五千字、五七千字左右徘徊,好像有一个无形的计量单位在限制我。就像现在的我,写小说,字数大多在两到三万字之间踯躅,很难写短,也很难超过三万。超过三万时,它一定是人工操作的产物。当字数到达2.33万至2.4万字左右时,那种不可变更的要走向结束的惯性,决无拖延的余地。它能使笔尖改变方向,能使手指酸胀,能使肩背痛苦,能使大脑杂念横生。如果这时能顺应自然走向结尾的话,那结尾往往不错,至少在心理上产生一种创作的愉快,这真是说不清楚的一件事情。也许说明我是一个有惰性、不灵活、顽固和适应性不强的人。
我想,我得另起炉灶,我得抛弃以往的全部作品。我立刻决定在温软的秋天里再写几部中篇,因为秋天对于我总是最适宜、最彻底、最厚实的季节。于是,我在去年9月中旬动笔了。我开始写一个女孩,淮北农村的一个女孩。我在淮北的城市和农村生活了25年,是纯正的淮北人,我对那里有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宗教般的情绪。
我在那里工作的时候,当宿县地区有三个县划走了的时候,我曾私下里黯然神伤了许多日子。其实关我什么事!那种狭隘的小农式的土地观念也真是要命的事情,但那其实是一种泛国土情感。我认识到,在文学创作中,我需要它们。我的这份情感是土地培养起来的,它们有根茎,而我又很真诚。我想我的大部分根须都在那里,都在濉浍平原的那些地块里。
我开始写那个女孩子了——小瓦,我不认识她,但我知道很多淮北农村的姑娘。我其实也是在写我长年积攒的一些感觉。这些感觉在我以往的许多短诗和一首长诗《还乡》里早已存在。我现在要做的只是把它们具体化、形象化和情节化,这也许就是韵文和非韵文的唯一的和根本的区别。
我开始认识并且熟悉她了,我开始能感觉到她在草甸子上走动和晚间在我的耳边吹气的响动以及声音了,我开始在她看不见我,我却能看见她的地方注视她了。我看见她从杨树下走过时,杨树的最后一片秋叶落下来落在她的肩上,并且有风吹来撩起她的衣襟以及她肩上的秋叶的情景了……这一切都是多么清晰、有趣并且使人惊奇呀!
二、发表
在开始写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单相思式的可笑的认真念头。我一边写一边想:我这一篇是为《上海文学》写的,虽然在这之前,《上海文学》的吴泽蕴已经退了我两年的稿子了。而我为什么非要上《上海文学》?或者为什么要以《上海文学》这个具体的纯文学刊物为我创作的潜在动力的一部分?我说不清楚。也许是它的纯文学的档次(假如有档次的话)?也许是它的台阶作用?也许仅仅是我的本能的占有欲望?但我有一种感觉。我写得很兴奋。这时候,我的“野心”有点大了,我一边写一边想,“小瓦”写好后,我还要再写一个。于是我又有了一个中篇,题目叫《惊慌》。接着,我又写了一个中篇,又写了一个中篇。“小瓦”写完并且抄好的时候,我突然获得了一次到上海出差的机会,这对于我真是再好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