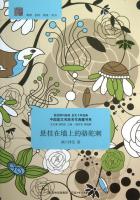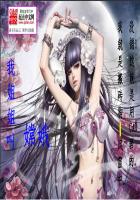这是三个年龄相差很大、彼此生活的主要阶段之环境完全不同,故思想差距很大、性格也大不相同的人。叔叔已经是一个快入土的老头子了,他的形象是这样的:高而瘦,有一般老人常有的使人讨厌的啰嗦话。他经常拄一根棍子,在院里院前颤颤巍巍地走动。晚上睡在黑暗的角落里,不断地唉声叹气。如果有客人来了,便免不了很长的废话,其中自然是不满和埋怨,特别是对他另一个侄儿的不满。他一辈子没结婚,自然也就没有亲生儿女。
男主人也算得上老头子了,身材很魅梧,但不胖。他很喜欢闲谈,而所谈大多是自己的经历或见闻,比如讲六几年跑河南演皮人戏等等。他手上不离小烟袋,装烟丝的是一个小葫芦。他很可能是自私的,但因为他又是比较明智的,所以有可能把私心不声不响地实施,而不是斤斤计较、大张旗鼓地进行。
我们再来看看男主人的女儿。她和她的长辈截然不同,身上有着社会主义时期农村青年女子所特有的朝气,和新的人物、新的事物接触较快,这些新事物占领了她的思想。她是大队文艺宣传队的一员,经常唱一些新的歌子回家。可是鉴于幼稚,她对她的爷爷的不满经常只能用吵嘴的方式发泄出来,外面的事忙于家庭之务。
“现在我们可以来比较一下这三辈人了:第一辈是可以淘汰的了,这是无须多言的;第二辈最多只能算‘中间人’,这样的人物如果能争取过来将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虽然这不大可能);只有第三辈人才是希望,她们是不言而喻的接班人。”
天很热,书房里的温度是33℃,但我又不想开空调,因为我马上就要离去了。我是在写什么吗?或者我是在录入些什么吗?我颇觉恍然。在这样的酷热的盛夏里,谁也不会想起,更不会对以往的某个也许并不真正存在的时代感兴趣,谁会为那些似乎乏味的日子口干舌躁地操心呢?神经!
我要去吃冰镇西瓜去了。天这么干热。窗外一片白灼。
颠狂嗜书者
一生都喜欢书,虽然现在还不是说一生的时候。“文革”期间,父母都被“发”往干校去了,留下我们姐弟几个在城里上学。没有大人在,姐姐们很难树立权威,况且我又是老小,又是独子,平时常被“惯”着,多少有些任性。于是每一个晚上,每一个白天,都抱着在任何地方搜集来的任何一本书读,就这样把眼睛读近视了,也留下了嗜书的“老毛病”。
嗜书有三部曲:上中学前是交换书看。那时候经济不发达,还没有零花钱之说,买书当然没钱买,就只好跟同学、跟邻家的孩子、跟同学和邻家的孩子的哥哥姐姐交换书。其实交换也是买空卖空:利用时间差,从这儿得一本书,看完了拿去跟有书的孩子交换。又看完了,还掉第一本书,再拿第二本书去交换第三本书;如此循环往复,我的一丁点教养和基础中的相当一部分都是这么读野书野读书得来的。
上大学时是借书看。大学里有图书馆,免费提供大量令人眼红的图书。况且大学里人人都倡导读书,读书非常合理合法。
这下我可逮住了,不读白不读,读了不白读,三五天就去换六七本书来,狂嚼暴饮,并且走上了极端。对那些我认为耗时耗力而又味同嚼腊的课程,例如党史(其实党史我们都已经太熟了,谁考来考去没考过二三十遍),例如外语(外语当然有大用,但没有外语的语言环境,还不是学了就忘。
我希望有朝一日在良好的外语语言环境里,能够事半功倍地速成),例如文学概论(都是老八股了,连教我们的老师都说,这些教材和概念五十年代就固定了,三十年过去,社会和文学真的就没有一点改变和前进?)等,我都一概应付。应付不成就拒绝,拒绝不成再应付,目的其实只有一个,就是把省下来的时间,拿去读馆藏的真有魅力的那些图书,我自觉着我上学的机会不会再来,这是一锤子买卖,不嗜读怎么行?!
大学毕业后,读书的途径自然而然转向购买了。购买也是因为自己有了一定的经济能力了,也是因为成了家初步具备了藏书的条件了。书渐买渐多,书架增加了一个又一个。
购书渐渐变成了一种欲望:花钱的欲望?拥有藏书量的欲望?无事时又做了一件事的欲望?可以向别人说我也有某本书的欲望?仅仅为了在书的扉页上记下“许辉×年×月×日购于×地的欲望?或者兼而有之?
购书也有阶段性。记得有一段时间,八十年代中后期,我对书产生了一种很腻的情绪。见到书或者书店,就有一种更年期的烦躁感,就没有胃口。但在大多数时间里,我都有购书狂倾向。
到了一地,不管是大都市或小街小集,甚至长途汽车中途吃饭的路边野店,只要有书有书铺,我立刻就会凑过去(在这种事情上我绝不怕上当)。凑过去的结果大多是买至少一本书或一本杂志,这都成了习惯或毛病了。而且愈是荒僻的小地方,愈有一些想不到买不到的价廉(因滞销的时间长)物美的书出现。那种故知旧交的惊喜惊奇难以描述。对一个地方的记忆也往往就变成了购买一本书的过程的记忆了,数载不灭。
冬日的读书
今年天气冷得早,又冷得深,人对温暖的室舍就有无限的留恋之情。一般的活动都不安排在室外,可有可无的活动也尽量免去,由此可见自然界对人的规范和限制是多么地深刻。
大雪纷扬,零下十几度的难得的低温,室内即使生了取暖炉之类,人也总有一种缩萎的感觉。这时候闲暇的最佳消费,当是读书了。
前人曾经体味出“雪夜闭门读禁书”的快感,现在时代不同,只要手中有自己中意的好书、好刊、好报,甚至好的电视节目,那快感都是一致的,都难能可贵。
大雪封门时节,找什么样的书来读,才好呢?须找那种节季喧哗、心绪骚乱时读不进去的典雅稳沉之作来读,才为最好。
那种稳沉、典雅之作与贴身的飞雪的季节,最为吻合。心室易被触动,人体易于吸收,情操最能陶冶。若换了些杂芜来读,人心为之玷染、搅扰、烦腻顿生,又因囿困于窄狭而粘连倍加,人即膨胀于不良倾向之中而难以自拔。
冬去春来。冬天过去了自然就是春天。春天使人复苏、冲动、想象。春天使人解除禁锢而倾向于行动。得典雅、稳沉之气者,明了世事哲理,就能事半功倍,就获得了行事的能力,日日有丰厚的积累,日积月累,使别人都重视于他。而那困扰于杂芜之间的,则万念纷乱,言行相悖,速于渲泄,急于求成。这样从春至夏,从夏到秋,一年过去了,收获的当然只能是失败或者失意。
所以冬日很是紧要,冬日的大雪也很是紧要。冬日是整肃的时节,冬日包含着得意?如意?失意?甚至杀机?冬日里的读书自然也很是紧要,万勿掉以轻心。世上万事万物,都有它的起源和发展,冬日及冬日里的读书,大约也是其间的一种吧?原来一年的时光和作为,并不是从春日倒是从第一片雪花的飘落开始的!生命、时间和思路的连环扣,竟是这样的相衔无隙!
周日的补偿
许多个星期以来,我们都是过着这样一种有规律的生活的:从周一到周五,我们各自为战:董静每天上班中午不回家,许尔茜上初中在学校吃午饭,一天所有的时间里,只有我空房留守。中午吃一盒快餐,操作、照料自己的事情,晚上三人才能相会。而在不算少的时日里,我往往中午就出门办事,直到深夜才能回来。我回来时,她们早已睡熟,并且把我排挤到另一间屋里的单人床上。我稍事洗漱,看看书报,然后上床休息。第二天早上她们起得较早,我只能朦胧地听到她们的一点响动。待我真正醒来时,室内已经空无一人。
如此再三,她们早出晚归,而我则晚出早归。有时甚至能够连续几天与她们不相谋面,听不到她们的话语(董静的电话除外),感受不到她们的气息。
女儿也会因此而略失平衡,抱怨好几天见不到爸爸了。家庭生活会顿时使人稍感一些倾斜的不安。
家庭生活确实是一种微妙、细致而又充满了磕绊的什物。家庭里的每一个成员都需要别人的认真对待、关心和触及。
比如女儿,她当然最喜欢攀附和缠闹妈妈,但爸爸对她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如果傍晚她放学回来而我在家,她就会围着我喋喋不休地谈论很多关于她、关于学校里的事情,直到她不得不去写作业或弹琴。
如果我出差一段时间回到家,却又没能和她多说话或对她做出到位的关心的表示,她的情绪就会不好。她可能会在当时、当晚或第二天、第三天找个理由生气或发泄出来。那时董静就会提醒我:孩子没跟你亲够。我就赶紧去跟她说话,喊她宝宝,或者关心她,她的情绪立刻就会好转。
晚上睡觉以前,女儿也需要家人的触摸和关心,比如给她掖掖被,摸摸她的小脸道一声晚安,她就能睡得很香,一夜都不醒来,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
在这种情况下,几天不相触及的生活自然是蕴含着一些相对不稳定的因素的。
也许是作为一种补偿,周六和周日,我们会付出共同的时间和注意力来调整有些混乱的生活:周六我会带许尔茜去攀登龙泉山、寻访龙泉寺,下午回家时董静已经把家里的事收拾好了。周日我们一定会去找一个新鲜的地方大吃一顿,当然是我(用自己的私房钱)买单──这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就我来说,我会感觉到我已经具体地为她们做了一些事,我会因此而减少一些歉疚感。而对她们来说,她们会兴高采烈放心大胆地大吃一顿,因为花的不是“自己”的钱,是“别人”的钱,不必心疼和酌量。吃起来自然是有滋有味、轻松愉快和开心的。这种形式,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家庭生活必不可少的交谈、交流和理解的机会。
我至今还记得一个周日我们在一家酒店吃自助火锅的情景。也许就因为是自助,我吃得略为多了些,回来胃难受了一夜。在过后的好几个星期里,她们对那家酒店念念不忘,但我却拒绝再踏进那里的门槛一步。
吃饭是次要的,我们是希望我们的家庭生活能够在一系列不可避免的震荡和磕绊之中,经常达到又一次和再一次的和谐与融通。周六和周日的补偿,是有关的一种手段。
永远的一天
早上是在她们的忙乱中醒来的——相较她们这些上班族或上学族,看起来我似乎痛快多了:不用赶早,不用在街上顶风冒雪,不用拿自己的旧自行车跟别人的新自行车撞架,每天闲卧在家里,吃了喝,喝了睡,在阳台上吹几段无关大局的口哨,碰巧冒出来一篇两篇对人类无害的文字,还能多几次白吃白占的机会……确实,早上我是在她们的忙乱中醒来的。人去屋空。当她们的脚步声在门外悠然而且神秘地消失了的时候,我已经在床上靠了起来。发条立刻就上紧了,在这一秒钟里,我将自己的生命之钟倒退了六个小时,回到了昨晚的时光。
茬口重新接上,那已是另一个世界:小芹的结局一定不好,这未免太残酷了一点……她在新时期的环境里只能选择第三个……那第三个男人却曾……十分钟后准时起床……匆匆一过……然后端坐于桌前。
这是一天里最好的时光,窗外阳光灿烂,百花竞开,百舸争流。吃着碗里望着锅里,这山望着那山高,我毕竟亦属年青,芳心未泯,多么也想去在街头碰上一个小镇来的试图骗城里人钱的妇女。也想去和每天都有的陌生人谈话,也想榨一个来办事的推销员的好烟抽,也想体会一下小金库分红而不向家长汇报的获得了隐私权的快感……电话铃响,一位未曾谋面的朋友派下来一项任务:来一篇有关……虽然我跟……粉……黛……没有关系,虽然要求的是一个……严肃的……情之……外……三千也行,五千也可,高价收购,(亦可)整容另投,后日交货,不得有误。——颇似……放下电话,立即改做新功课:这是初交的朋友,心中更加在意。
午饭有鱼,还有牛肉。极馋,馋虫乱顶,却好歹不敢多吃。根据以往经验,贪食往往遭罪。自个便恼了自个:桌边坐久了,胃动力不足,要是成天在外跑跳,那还不能向广东人学习:除飞机坦克不吃,什么都塞它一肚子!
赶紧离桌而去。下午迷瞪个三五十分钟后的工作依然如故。腰酸背痛。盘算盘算今日、明日、今年、明年的紧张进度,更加自我要求在年轻时一定要把自己当个一般的机器人来使唤,决不可再对自己手软半分。写得入港时心情还挺有点那个:跳。
此时真真怕别人打扰,怕一个豪华酒楼的新饭局,怕一个别人介绍的有漂亮舞伴的晚场舞会,怕一个十载难逢会影响我迁升的跟某高级官员相识的小会……赶紧把电话提溜起来(一概忙音),用家人的话说:酸劲又上来了。没办法,迂嘛。这也太有点少年老成了吧!突然有人敲门,进来两位红光焕发、心绪良好的更年青者。他们双目炯炯有神,言词犀利,思路阔大,社会经验丰富。抵住了一定要我告之文内文外秘诀。我说我对此一窍不通,他们说我谦虚,我说我仅凭经验,他们说我保守,我指着桌子说:在那地方趴上七七四十九天,谁都能成为青年作家(反正这也没有名额限制)。
一个人永远地坐在桌子边。烦?烦!有烦的时候,把桌上不管三七二十一的东西(高成本的除外)一推,然后甩手而去。跑到阳台上,跳?太高了。想?想!想那些为争夺靓女丽星而一掷万金的“款”们;想公费在新、港、泰、马十日游的“贵”们;想露脸一笑扫走一包币的“腕”们;想一本书买一幢别墅捎带一块大草坪还可花天酒地过两个十年的“外”们;……别想了,电话又来了……“稿成了没?”
一天早过去了。——凌晨一点了!
衰老的开始
在饭桌上剔牙是很不雅观的,特别是当你正有一副好胃口,正有一个好牙口,而餐桌上也大器晚成、好菜纷至沓来的时候。恰在此时,一位殷勤得不是时候的年轻人,忽然站起来拿起牙签盒,挨个送到食客们面前,说:请,请。已经进完了食的食客们挨个捏了根牙签在手里,有些是拿着玩玩的,有些转过了身去,有些用空着的手掌挡住了半边脸,还有些干脆面对餐桌,直接干起来。
按理说,选择使用牙签,是一个人的自由,是一个人的习惯,也可能是一个人的痛苦。自由,包括剔牙的自由。这是一个人好生生活在世上的基本证明,没什么可探讨的。
习惯,这是因为剔牙能产生一种快感,特别是剔牙成为习惯的时候。产生快感的东西在没有外力的限制时很难自动中止,而牙,多多少少,拿到身份证的人都剔过。如果必须,那确会产生一种不适之后的大快感。一来二往,放任自流,肯定就会成为习惯。
痛苦,相信这是许多剔牙者的前因:食兴最浓、菜事最盛的关口,素无留客习惯的牙齿,突然被不请自到的外物塞挤住,当事人自然恼羞成怒。另外,牙齿的自然松动、牙病的长期积累可能也是个原因:牙齿经过几十年硬碰硬的不停顿工作,确实会有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想法;避重就轻、绕着困难走,见困难就让,有机会就叫,小病一、三、五,大病二、四、六,都可能在它们之中发生。在这几种情况下,当事人因痛苦而迫不及待要清除异己,铲尽邪恶,也是能够理解的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