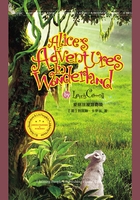娄护在《汉书》中有传,其名为楼护,字君卿。据说他读了不少杂书,能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嘴巴又巧,因此很快讨得上流社会的欢心。这个游走于侯门之间的帮闲,后来也被封了个“息乡侯”,不过不是靠耍嘴皮子。他把躲在自己家中的一个企图和王莽过不去的人,送交这个后来的篡位者处置,于是受到重用。这已经不是烹坛帮闲,而是官场帮忙了。至于娄护或楼护发明五侯鲭的故事,《汉书》则不载,也许是觉得此等小事于国家社稷并无干系。正史之中,一般很少有吃喝帮闲们的事迹,逼得诸多帮闲,只好千方百计到官场上帮忙。帮不上忙继续帮闲的,也得千方百计给自己涂上点官方色彩。
唐朝科考发榜之后,新科进士照例要有一系列的礼仪活动。要拜谢主考,要参谒宰相,更要参加各种名目的宴会,吃吃喝喝。其中有名的就有大相识、次相识、小相识、闻喜、樱桃、月灯、打球、牡丹、看佛牙、关宴等等。这些吃喝活动都有一定之规,而进士们初入仕途,难谙“吃”道,于是,长安城便出现了专门为进士吃喝服务的机构——进士团。
进士团有首领,有帮办——“所由”。“所由”的意思是主管官吏。唐人谓府县官为“所由官”,可见进士团的帮办们自定的级别还不低。这些个假官,比真官还牛。据《北梦琐言》记载,一次,新进士崔昭矩由于所由办事出错,“笞之”。这个所由居然倒打一耙,对诸进士说:“崔十五郎不合于同年前面,瞋决所由,请罚若干。”弄得崔某人反倒说不出话来。帮闲一旦有了实权,可能比帮忙还厉害。
“闲行”三六九
自打吃喝之事从宫廷家庭走向社会后,三百六十行中,便多了勤行与闲行。
“勤行”,是指餐饮从业人员,主要从事物质生产。老北京的“勤行”,讲究“一堂二灶三先生”。堂,指堂头,换了现在的时髦说法就是客户总监。过去饭馆里的好堂头,心里都有一本账,老主顾爱吃点什么,喜酸还是嗜辣,不等你开口便全都给招呼到了。因此堂头一旦跳槽,食客往往跟着挪窝,图的就是个服务周全。灶,是掌灶厨师,即厨师长。先生,则是账房先生的简称,如今大都改叫CFO了。掌柜的选好用好这三个人,便尽可放心回家,躺在炕上乐颠儿颠儿地数现大洋了。只是不要过于乱造,掏空了家底儿。这和现在办企业其实是一个理儿。
“闲行”,是指闲人聚集的行当,主要为食客提供精神服务,让他们吃得开心吃得有趣。“闲行”一词虽属杜撰,却于史有证。南宋时灌圃耐得翁的《都城纪胜》中,便说到当时杭州有“闲人”。其中“有一等是无成子弟失业次,人颇能知书,写字,抚琴,下棋及善音乐。艺俱不精,专陪涉富贵家子弟游宴,及相伴外方官员到都干事。”对闲行的人员构成及工作职责介绍得很是清楚。《梦粱录》中也有近似记载。
如同“勤行”有高下之分一样,“闲行”之中,也有三六九等。一等吃喝帮闲,要有才学,能为贵人解厄济困,而且要认准自己的位置,绝不能自矜高明。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农金冬心先生,便是一闲行高手。据说一次他赴某盐商之宴,席间要行“飞红令”,即行令者引用古今一句诗词,其中要有“飞”“红”二字,说不出便要罚酒。轮到该盐商行令时,他竟胡诌出了一句“柳絮飞来片片红”,简直是岂有此理。正当众人揪住盐商要罚酒时,金冬心却来解围,说此诗句并非臆造,确为元人之作,并当场吟出全诗:廿四桥边廿四风,凭栏犹忆旧江东。夕阳返照桃花渡,柳絮飞来片片红。有“夕阳返照桃花渡”铺垫,“柳絮飞来片片红”不但顺理成章,而且顿出新意。宴会结束后,盐商特地备了一份厚礼送与冬心先生。诗,自然是冬心先生当场拟就,但他却谎称为元诗,这就是一等帮闲的高明之处。
做一等帮闲要有点真本事,多数闲行中人“艺俱不精”,于是只好混饭吃,于是也只好被有帮闲之才而不屑为之的文人所看轻。《红楼梦》中的帮闲,单从名字上看就非正经货色,有什么詹光、单聘仁、卜固修,所对应的是沾光、善骗人、不顾羞。在曹雪芹眼中,这些人的业务能力,实在还不如刘姥姥这样的业余选手。刘姥姥吃饭时还知道兀地大叫一声:“老刘,老刘,食量大似牛,吃一头老母猪不抬头。”哄得贾母等人开怀大笑。
如果说一等帮闲属于“文路”,二等的就算“武行”,其职责是维护餐桌等级秩序,帮主人把该伺候的人伺候好,有无才学倒在其次。宋代的“白席”便是这类人。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曾记载“白席”之行状,说宰相韩琦一次回到家乡安阳,去一亲戚家吃饭,席间便有一“白席”以他为服务对象。韩琦刚想吃荔枝,“白席”便高唱:“资政吃荔枝,请众客同吃荔枝!”韩琦很是恼火,索性放下荔枝,看你怎么办?没想到此“白席”却毫无窘色,接着又高唱:“资政恶发也,请众客放下荔枝!”弄得韩琦再无法“恶发”(生怒),只好一笑了之。此“白席”可谓深得二等帮闲执业之道:管你生气不生气,马屁定要拍到底。
除民间外,宋代朝廷之中也有“白席”。据《武林旧事》记载,南宋皇上过生日,先要由枢密院官员引领军官上寿,再由百官恭进美酒吉言,祝皇上千秋万岁,然后皇上要摆宴招待够级别的大臣。此时,便有閤门官即官方“白席”大声呼喝:“不该赴坐官先退。”那些没资格赴宴的官员,只好一边咽唾沫去了。
閤门官的正规称呼是閤门使,掌供奉乘舆,朝会游幸,大宴引赞,引接亲王宰相百僚藩国朝见,纠弹失仪。官方“白席”多由武将中的外戚勋贵担任,一是出身好政治可靠,二是口号喊得响,因此其工作虽然简单,一般人也够它不着。
一等二等帮闲都没份儿的人,只好如《都门纪胜》所言:“其猥下者,为妓家写简帖取送之类。”混到这个地步,帮闲也就没有多大意思了。
鲁迅先生对帮闲阶层的评价是:“必须有帮闲之志,又有帮闲之才,这才是真正的帮闲。如果有其志而无其才,乱点古书,重抄笑话,吹拍名士,拉扯趣闻,而居然不顾脸皮,大摆架子,反自以为得意,——自然也还有人以为有趣,——但按其实,却不过‘扯淡’而已。”对于吃喝帮闲,亦当作如是观。
文余杂碎儿·续“闲行”三六九
金冬心赋诗为盐商解围之事,张中行等诸名家在诗文中都曾提及,我们家老头儿汪曾祺也写过一篇小说《金冬心》。这是他唯一的一篇以历史人物为题材的小说。他之所以写这么个东西,就是因为对于这一情节印象颇深,并多次兴致勃勃地向我们讲述过这个故事。但此事最初见于何处,却未曾听他提起,大概是觉得跟这些没文化的子女说了也是白搭。
经友人曹鹏兄热心提供线索,如今终于从清人牛应之的《雨窗消意录》卷三中查到了有关记载:“钱塘金寿门农客扬州,鹾商慕其名,竞相延致。一日有某商宴客于平山堂,金首坐。席间以古人诗句飞红为觞政。次至某商,苦思未得,众客将议罚。商曰:‘得之矣,柳絮飞来片片红。’一座哗然,笑其杜撰。金独曰:‘此元人咏平山堂诗也,引用甚切。’众请其全篇,金诵之曰:‘廿四桥边廿四风,凭栏犹忆旧江东。夕阳返照桃花渡,柳絮飞来片片红。’众皆服金博洽。其实乃金口占此诗,为某商解围耳。商大喜,越日,以千金馈之。”这也算是对老头儿有个交代吧。
这么点东西居然能够铺陈成一小说,而且很有看头,也算汪曾祺有本事。文中极有味道的金冬心所赴之宴的菜单:“凉碟是金华竹叶腿、宁波瓦楞明蚶、黑龙江熏鹿脯、四川叙府糟蛋、兴化醉蛏鼻、东台醉泥螺、阳澄湖醉蟹、糟鹌鹑、糟鸭舌、高邮双黄鸭蛋、界首茶干拌荠菜、凉拌枸杞头……热菜也只是蟹白烧乌青菜、鸭肝泥酿怀山药、鲫鱼脑烩豆腐、烩青腿子口蘑、烧鹅掌。甲鱼只用裙边。花鱼不用整条的,只取两块嘴后腮边眼下蒜瓣肉。车螯只取两块瑶柱。炒芙蓉鸡片塞牙,用大兴安岭活捕来的飞龙剁泥、鸽蛋清。烧烤不用乳猪,用果子狸。头菜不用翅唇参燕,清炖杨妃乳——新从江阴运到的河豚鱼。……随饭的炒菜也极素净:素炒蒌蒿苔、素炒金华菜、素炒豌豆苗、素炒紫芽姜、素炒凤尾——只有三片叶子的嫩莴苣尖、素烧黄芽白……”这些当然不是金农当年的吃食,而是老头儿为冬心先生设计的菜单,是他多年所见所闻所尝的饮食精华之荟萃。单从这一点上看,我们也确实不算有文化。
关于白席人的记载陆游之前便有之。《东京梦华录》卷四“筵会假赁”,就提到了这种特殊的职业:“凡民间吉凶筵会,椅桌陈设,器皿合盘,酒檐动使之类,自有茶酒司管赁。吃食下酒,自由厨师。以至托盘、下请书、安排座次、尊前执事、歌说劝酒,谓之‘白席人’。”
清代梁绍壬在《两般秋雨蓭笔记》也有近似描述:“湖南麻阳县某镇,凡红白喜事,戚友不送套礼,只送分金,始于一钱而极于七钱,盖一洋之数也。主人必设宴相待,一钱者只准食一菜,三钱者三菜,五钱者遍肴,七钱者加簋。故宾客一时满堂,少选一菜进,则堂隅有人击小钲而高唱曰:‘一钱之客请退。’于是纷然而散者若干人。三菜进,则又唱曰:‘三钱之客请退。’于是纷然而散者又若干人。五钱以上者不击,而客已寥寥矣。此事未见虚实,而穷荒陋俗,容或有之。余思此堂隅高唱者,或犹是古之白席之风。”文中多说的“一洋之数”,是指一块银元的重量,大约为七钱。这类职业居然历数百年而不衰,可见市场对其确有需求。直到今日,宴席上的白席人虽然绝迹,但在其他领域拍马屁瞎白活的人仍间或有之。
吃喝帮闲中,“其猥下者,为妓家写简帖取送之类”。没本事的人,能为妓家跑跑腿混口饭吃,其实不算跌份儿。因为妓家之中也有文化人。唐朝时,酒宴之上常设有“酒佐”,也称“席纠”,其职责就是让大家吃好喝好玩好。这类角色常由伎女充当。一流的“席纠”必须具备三种本事,一是“善令”,即熟悉各种酒令,会说好话,以便活跃气氛;二是要“知音”,即擅歌舞,能度曲;三是要“大户”,就是有酒量、能豪饮。三种本事兼而有之,往往就能成为名妓(并非名记)。据说妓业名人薛涛,便是一出色的“席纠”。一次,一个附庸风雅的黎州刺使请人喝酒,席间要行《千字文》令,令格为,取《千字文》一句,句中须带有禽鸟鱼兽之名。此刺史带头,说了一句“有虞陶唐”,一开头便闹了笑话,把“虞”硬当作“鱼”了。大家碍着他是当官的,兼之吃了人家嘴短,只好窃笑。轮到薛涛行令时,她有意说了一句“佐时阿衡”。黎州刺史十分渊博地指出,此四字无鱼鸟,遂命罚薛涛酒。薛涛从容答道:“‘衡’字尚有小鱼子,使君‘有虞陶唐’,都无一鱼。”宾客遂大笑。这般帮闲手段,绝非一般人等所能企及。
《千字文》中,沾点鱼腥的只有三个字:“海咸河淡,鳞潜羽翔”中的“鳞”;“孟轲敦素,史鱼秉直”中的“鱼”;“磻溪伊尹,佐时阿衡”中的“衡”。这几句话中,除了海咸河淡是大白话甚至是大废话外,其余都有典故。史鱼不是鱼,而是人,是春秋时卫国的大夫,以正直敢谏闻名。阿衡原本是商朝的官名,因为著名宰相伊尹曾任此职,阿衡便引申为辅导帝王主持国政。蟠溪指的是周朝的开国元勋姜子牙,因他在未发达之前曾经在此处垂钓。说来惭愧,过去读书人的启蒙读物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本人从未通读过,这史鱼、阿衡之类的词儿还是翻阅《辞源》才弄明白的,属于现上轿现扎耳朵眼。说是没文化,一点也不假。
薛涛是有名的才女,充当这种低档次的帮闲,自然是游刃有余,虽然内心未必愿意。她的诗本来就写得十分出色。如《送友人》:水国蒹葭夜有霜,月寒山色共苍苍。谁言千里自今夕,离梦杳入关塞长。确实当得“工绝句,无雌声”的评价。给这样的人“写简帖取送之类”,恐怕现实诸多“文人”及其领导者未必够格,本人自然包括在内。
?
扫除看盘
世上人人要吃饭,吃饭规矩各不同。
一般中国老百姓用餐,要等一家老小全部坐定,方能动筷子,不如此便为不懂礼数;外国一些人家,全家坐好之后,还要嘟囔几句:万能的主,感谢你赐予我们饮食,阿门!此类餐前仪式,中国也曾有过。三十多年前在农村插队时,所有知青进食堂先得敬祝“万寿无疆”和“永远健康”,否则不但饭没得吃,还要查你的政治立场。可惜此举未能流行长久,不然中西饮食习俗又多了一点相通之处,岂不妙哉!
至于帝王之家,吃饭时的讲究就更多了。
法国国王的早餐,只有区区一碗汤。不过,这碗汤,喝起来可实在不是简单的事情。每天早上,国王传膳之后,这碗汤要由两个寝宫侍从在两名弓箭手、一名司肉官、一名餐具总管和一名王室面包房总管的护送下,庄严地从御膳房端出,七转八转之后,才能送到餐桌上。
至于正餐,动静就更大。法王路易十四吃午饭时,人们要列队送膳。御膳运输队由御膳大总管率领,三十六名衣着华丽的宫廷侍卫和十二名手执镀金镶银权杖的仪仗官负责护送他们离开厨房,先穿过一条街,然后进入王宫,再走过迷宫似的过厅、大厅和走廊,最后将御膳送到国王的餐桌上。这样的进餐仪式一直延续到法国大革命兴起,国王上了断头台之时。等到路易十八在拿破仑倒台之后重登王位,立即把这一套又捡了回来,进膳时还要另加一百名瑞士鼓手,敲起军鼓为膳食护送队壮行。那场面,比现在的游行庆典还要热闹。法国历史学家勒诺特尔所写的《法国历史轶闻》中,全是这类故事。
比较起来,中国皇帝吃饭时的仪式要简单些,起码很少用宫廷侍卫和弓箭手送餐。这恐怕是出于安全的考虑。试想,让那么多舞刀弄枪的总在身边转,皇上吃起饭来心里怎么能踏实?即便这些人不敢犯上作乱,在宫闱之中闹出点风流逸事也是麻烦。因此索性斥之不用,让太监来伺候。法国的爱情小说中常把皇后、公主扯进去,中国则绝对不会有。原因无他,就是没有让拈花惹草者进宫送饭,不给他们作案机会。
不过,中国皇帝吃饭也有自己的讲究,除了要有可吃之物,还要有可看之物。这就是看菜,也称看盘。还有一种说法叫“香食”,意思是闻闻香而已,吃是不吃的。
据记载,看盘隋唐时宫中已有之,据《卢氏杂说》记载:“唐御厨进食用九饤食,以牙盘九枚装食于其间,置上前,并谓之‘香食’。”以后,这一习俗逐渐流传到民间。唐中宗时,刚刚拜相的韦巨源在家中设“烧尾宴”宴请中宗,所上的五十八道菜中,有一道“素蒸音声部”。这是由七十个蒸面人组成乐舞场面,其中有弹琴鼓瑟的乐工,也有翩翩起舞的歌伎。这便是看盘。
唐朝官员升迁之后的第一要事,就是请客。宴请亲朋同僚自不必说,当了宰相一类的大官还要请皇上大吃一顿,这就是烧尾宴。传说鲤鱼跳过龙门之后,必经天火烧掉其尾,如此方能成龙。升官就等于鲤鱼跳过了龙门,摆宴庆贺烧掉了尾巴确实应该。不过,吃过烧尾宴,尾巴虽然没有了,脑袋日后保不住的也大有人在。官场上的事情往往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