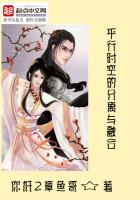天穹,深远的蔚蓝,宁静的日头,虚无的空间,风也如水流行;地面上飘起淡淡缠绵的炊烟,在空中纷纷扬扬地铺成一抹银灰色的梦境,鸟在梦里飞翔着歌子。
近了宁州城,必兴和高老八要分路了。必兴说:“老八,我要进城去,搞把生意。”
高老八说:“我得急着回去,你就自个去吧,愿你顺手牵羊,随意来财。”
必兴心里酥酥的,用极有弹性的舌头舔了舔干裂的嘴唇,瘦黄的脸孔上漾起薄翳似的笑意。必兴说:“快回去吧,迟了嫂子的被洞里就钻野汉子了。”
高老八心里咯噔了一下,他总放心不下他女人,他女人长得丰腴,身子上每块肉都会泼泼地颤动出风风火火的骚情。何七斤常说他女人像一棵鲜嫩茂盛的白菜,人一见心就颤。高老八再没想多的,朝必兴瞪了一眼,转身顺着城北的道儿去了。
必兴得意地晃了下脑袋,眼里闪烁出卑劣的光芒,朝着高老八的背影撇了下嘴,表达了十分的嘲讽。
他望着走在阳光里的高老八,高老八僵硬地昂着头颅,匆匆的步子敲击着起伏的官道,使地皮发出急躁的响声。高老八心里想着什么,必兴却心里好笑,在分路的当儿,只轻轻拍了一下高老八的肩膀,顺手便掏了他的腰包,他竟无一丝感觉,踟蹰了一会儿,便匆匆地去了。
他向高老八奸诈地注视了好一会儿,便吹了几声口哨,踅身向城里走去。
城头像汪在一片淡黄色月光里的孤独怪兽,风在喋喋不休地诉说着世界的广漠。他没有这种感觉,他背了手走进了城门洞。城门洞的地面仍铺着青蓝色的石板,大小不一,无甚一定形体地组合成一片龟裂的整体,走上去脚底有油滑的感觉。风在城门洞就有了寒意,匆匆促促地流荡着凄凉的信息。必兴走在城门洞里,像穿越一个冬天,漫长而阴森。突然一匹马的蹄子从城门洞外敲进来,敲出空洞如鼓的声音。这声音如马蹄踩起的水浪,在城门洞里哗哗四溅,击碎了城门洞里幽秘的阴暗。
必兴以为马背上一定是位绅士风度的老爷子,或是一位风流倜傥的恶少,他转身投去凶恶的视线。他的视线给一个意外的形容击得无丝毫的威力了,像束纷乱的光在空气里溶化尽了。这形容是一个女人俏丽的面孔,浮现着能蛊惑人灵魂的姿色,亮着一双充满梦幻色彩的眸子,笑若阳光般照亮了城门洞。这是满堂的儿媳妇巧巧,于家山弯新一代美女人。马昂耸着头颅,从必兴身边有节奏地敲击着青石板走过的,她飞快地瞟了他一眼,瞟得他整个形体几乎崩塌。她对他没说什么,表现出骄矜的隐藏着冷酷的讥讽,似乎像是唤他贼娃兴子。他感到了极其的耻辱,他的眉头暴怒耸起一座高峰,他要骂她臭婊子。他的嘴唇翕动了一下,但没有骂出声来。
马幅度极大地夸张性地扭动着肥大的屁股,从他身边走过,马尾拂尘一般地甩在他的脸子上,他脸子生出尖锐的疼痛,他眉头上高耸的疙瘩跳动了几下,但他还是没有骂出声来。巧巧回头又向他瞟了一眼,他却向她回了老绵羊一般的苦笑,显得非常拘谨。
马的啼声、铃铛声渐弱地远去,巧巧优美的背影也渐次模糊地隐去,但他的眼前依然重复着巧巧复杂而又玲珑的表情。身边还飘流着她身体里送来的阵阵如花的芳香,使他久久地耸动着鼻子,他爱这女人,更恨这女人,因爱她受了她诱骗的戏弄,那夜他自她家逃出后,他就恨她,发誓要屠死她。可当他见了她,便随和地宽容地向她笑,往往回敬他的是一种冷酷讥讽的目光。之后他又暗里恨恨地骂臭婊子,又发誓非屠死她不可。如此而已。
进了城拐弯就是西关。是集日,街道拥塞满了各种形象的人和各种混乱的噪声。他很兴奋,他和一切行窃的盗贼一样,喜欢在这人潮中挤撞着,贼眼溜溜地搜寻着猎取的对象。他瞅见在他前面磨蹭而行一个老汉,老汉像棵歪脖子桑树,给人群挤得简直是东倒西歪。老汉腋下夹着一匹土布,使他贼胆霍地壮了起来,顺手抽了去,高高举上头顶。老汉慌张地扭过头,睁着红泡儿眼睛,东瞧西瞅,惊呼:“谁拿走了我的布?”“布在哪儿?”“在我胳膊窝夹着。”“唉,你这老汉,像我这样拿着谁能拿去。”老汉抬起红泡眼皮,望着必兴手里高高举起的布匹,凝着神望了好一会儿,低头悲戚地哭去了。必兴正想溜走,一个女人像一堵墙堵住了去路。
她咬咬牙,抖着愤怒的身子,眼里冷冷地闪着亮,很恶。她说:“是我公公的布。”必兴一眼瞅见是她嫖过的那个唱曲儿的小寡妇,他慌了,顿觉无地自容了,盘算着如何地逃走。他向她讪笑了一下,她啪地甩给他一个巴掌,他仓皇地扔了布,像一条狗,钻进人群逃走了。
必兴在人群里冲突着,一阵阵恶骂声海浪似的扑洒在他的身子上。他心里很晦气,如一条游狗。挤出街头,他吸了一口鲜嫩的空气,走到北阳河畔,坐在岸边的石头上想着这两个女人。岸边的嫩草长得细长,在他脚面上拂动,他觉着像小虫子爬着,痒酥酥的。石头坚硬地顶着他的屁股,他感到粗糙的不自在,便挪动一下身子。在挪动身子的瞬间,他在水里发现自己黑色若鬼的影子如蛇晃荡着,随后逐渐地扩散、疏远、模糊,直到全部消失。他心里倏然产生一种轻生的念头,泪水潸潸地在脸孔上奔走下来……
在夜里,必兴窃了无法估计数目的钱,是四捆方方正正的钞票墩和许多的银元,两枚元宝,还有一副质地难辨优劣的黑墨眼镜。行窃是在子夜,山城若一只古旧的船,沉沦在冷寂莫测高深的群山中,暗淡、凋落、憔悴、幽幽冥冥的夜气若低迷的黑雾,顽固的悠荡在这古城之下,蒙上梦的奥秘和含混不清的意义。一切的物体模模糊糊,唯有古老的城墙像庞大的恐龙拱起冗长而又僵硬的脊背,显示出粗糙坚涩的曲线,演示着生存与死亡的奥秘。城内东西方高高低低地耸立着几幢高楼,在黑暗里巨兽似的朝天仰视,向天体探觅着什么,古怪又狰狞。
夜风如黑色的血水,在楼与楼之间流来流去,是个夜游的鬼。他如一个幽魂,或似一只野猫,仗着夜的黑色庇护,翻进拥有一座楼房的院墙,蹿上了楼子。黑色的眼睛贼亮,觅见一间楼房的门上有锁,他喜得心颤,思忖这房里无人,便用钳子轻而易举地摘了黄铜锁子,开了门溜了进去。
凭着盗贼看穿黑夜的眼力,必兴机敏十分地觅见一方坚实的木柜,柜上挂着两把黄铜大锁。他脑里一闪念,眼前蓦然漾起银子的白光和金子的黄光,两种光和两种水溶在一起,便成了太阳一样的光芒,使黑夜溘然成了灿烂的白日。他恢复了理智,眼前的光芒倏然灭了,他依然沉沦在黑色的迷蒙中。他匆忙地拧那两把铜锁,钳子的铁质和铜锁的硬度相触迸发出金属质的声音,在寂死的夜气里锐利地飞溅。隔壁响起来,从含混不清的梦呓里弹出十分不利落的咳嗽声,使他有些惊恐。他凭了贼的机敏,学了两声鼠叫,掩去了隔壁老残的咳嗽声。
必兴终于获得了有生行窃事业里一次最大成就的成功,他喜得癫狂,心若一匹野牛,疯狂地冲撞着他的胸壁。他背着一包沉沉的获物,像一只鸵鸟,在幽暗的夜色里蹿行,夜气在他身边如水浪哗哗流淌。他觉着他的五脏里有浪涌冲突的感觉,似乎血脉也在奔流。
必兴爬上城头,四望辽阔无声,山城黑暗得可怖。天空酿雨的黑云,涌动着向城头压来;远处似乎有黑风如野马沿着山谷咆哮着、奔驰着。他思忖必须在天明之前逃出城去。他躲过慵懒沉眠的城头上的岗哨。躲过冗长凄迷若唤魂的呼更声,蹿到城头拐角处。这里是他早视察过的,城墙倾斜度较大,城墙下有丰茂的野草地。他趴在城墙边向城墙下探视,目光被黑幽幽的夜色淹没,一切都是黑色里高深莫测。
必兴思忖,他跳下摔死了,这么多钱该给哪个龟孙子好哩,真他娘的脚后跟!这思想使他心里忐忑不安,黯然心痛了。他怔怔地望着无法看清的黑暗,有些纳闷和惶惑。蓦然,一声冗长而又尖锐的鸡啼从城外的远处穿越黑暗箭镞一般地射来,他没敢再多想,只好拿命下赌注了,是活着,不然就死亡。他纵身擦着城墙跳下去,跳入了黑海一般的空间。
必兴感到他身子摩擦着粗糙的城墙在柔软的夜气里款款地下沉,冷涩涩的风声在他耳边若鬼的尖厉的鸣叫,惊人心魂,招引他坠陷于迷惑、疑惧,什么形象都模糊于冥冥之中去,怕是鬼蜮阴城。他后悔了,悔之不及地骂自己混蛋!随之而来的感觉是心逆着下沉的身躯向上浮,像要蹦出胸膛和体腔分离开来。他想这大概是死前灵魂早行吧,他又联想到转生,他相信人会有来世的,十八年后又是一条汉子。他心安理得地下沉,不再凄然了。
着地的瞬间,必兴觉到他的身躯像一块石头砸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声响,溅起一束一簇的气浪,或者是尘土飞扬,他还未感到疼痛就昏眩了,陷入了死亡的沼泽中。当夜风唤醒他的时候,他觉着有一种钝器缓慢地刺击着他的躯体,一阵麻木的疼痛从他肋骨内向外放射。他意识到他还活着,心里一阵欣喜,忙用足气力从地上爬了起来,行走了几步,虽觉身子有些痉挛,可腿脚还灵便着,他急匆匆地背了包袱,爬上了城壕,离开了城墙下。
必兴像躺在一片寂灭的墓地,脚下的黑草丛给踏出一串沙沙的响声,在幽静里更响亮地散布着黑幽幽的恐惧。夜是黑沉沉的,在黑云捅挤的空间,有一只乌龟一般的黑月亮,在云浪里钻来钻去,神情很古怪。一阵冷冷的黑风抛过来,撞得几株什么树抖出窸窸窣窣的响声。必兴悚然打了一个冷战忙缩了下脖颈。
必兴走近野地里一座地坑庄院,站在地坑院的庄背上瞅了好一会儿。地坑院里是一片荒凉,院里生长着茂密的山麻,麻丛里隐藏着黑色的谜。院崖上洞开着两只盲人眼睛似的黑窑洞。必兴蹿入黑黑沉沉的门洞,走了十多步黑道,便给一堵胡基墙拦住了。他寻思了一下,匆忙抽掉了几块胡基,亮出了一方苍白的昏蒙,他若老狗钻洞似的钻了进去。
必兴在窑地里燃起了柴火,火焰像鬼的舌头,哗哗啦啦地舔噬着黑色的夜体,吐出一片红亮来。他在一片红亮里点数着钞票,钞票在他颤动的手指间咯咯吧吧地响着。数了好多会儿,怎么也数不清,索性他不数了,捆成原来的墩儿,和了银元、元宝,包在包袱里。他夹了包袱,钻进了麻地,在麻地里挖了坑,像他老祖爷藏埋黑老缸一样埋了。他在埋物前默思了许久,他心里愤愤地骂老祖爷,骂他父亲:你们这些老驴日的,黑老缸传谁了?不传给我于必兴,我操你们老祖宗!瞧吧,我不也是有钱有元宝有银元埋吗!老子还是大财东呀,谁再敢叫我贼娃兴子……
笑从心底涌出,使必兴的脸孔在这一时刻豁亮了起来,闪耀着一种滑稽的乐观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