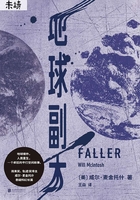北阳河是你流淌记忆的地方,在你难以忘却的年轮里,都是清澈湍急或悠然回转的歌谣。可你的心是不肯深埋于地下的化石,你的心如一只情歌辽远的鸟儿,时而迢迢地飞回终南山下去,那里也有你栖梦的鸟巢。
时午,凄凄地下起一番寒雨,一阵一阵的鸟啼,撩人情怀地透过雨声,透过窗户,催眠曲似的向你飘来,凄凉悲切极了,唤起你心底无限的惆怅。
你顿觉天地变得无边的空虚和死寂,于是悲怆之感从中而来,不禁泪潸然地落了下来。之后,你太倦了,便倚枕悠然入梦。
你梦见你又骑着黑炭色的骡子回了终南山下,那里的物景都荡着一层不真实的影子,看来有些许的迷离、虚幻,也真如梦,你心里有些焦躁。你的骡子走得不动声色,蹄下践起灰黄的尘翳,却无一丝声音。你觉得你和你的骡子都像没重量,纯粹是个影子,在空里悠悠浮荡。这怕是梦的实质。你骑在骡子背上摇晃着,思忖着。走近你家门前,你看见你家门前的大楸树在一片蓝色的光焰里猝然倒了,倒得轰轰烈烈。连同天空的几片云也拽了下来,树上那个黑色的鸟窝里的鸟梦也同样倾倒下了,在地上击得粉碎。老鸟摔死了,只留下一只小鸟在地上扑打着滴血的翅膀……
你极力想,愿这是梦,愿这是梦!
一阵悠然的拨浪鼓声将你从深深的梦里唤了出来,浑身大汗如潮,你静静地想了一会儿,噢,是梦,是梦!你心平静了许多。
拨浪鼓声如撒豆一般地又传了来,你觉这拨浪鼓声多么熟悉、多么亲切。你凄然地想起了终南山下你那个儿子,你有些慌乱地跳下炕跑到大门外去。
大门外仿佛是几十年前的那一幕情景,一伙媳妇、姑娘和娃娃围着个年轻货郎,货郎多像你的那个货郎儿子。你惊得懵懂,木呆呆地站了几分钟。在你懵懂里,那年轻货郎向你轻轻唤了声爷。你非常地惊喜,忙搭声:“噢,是我孙子,是我孙儿!”
村里又起了风,风不大不小,拽着树木、野草怡然地摇着。村子里话传了起来,人们嘴唇匆匆地忙着,都在议论你的孙子和有关你转生的旧事。
你引你孙子回到你家的老窑里。
你见你孙子脸色有些苍白,面容也有些憔悴,使你觉得在亲热之中有一些疏远的气味。
你问起家事,他凄凄地讲说他父亲也就是你儿子,今年春上去伐门前的楸树,说伐了给他做棺木。他和村里的游汉懒二棍扯锯,突然树倒了,端端地压在他身上,那么粗的树压在他身上,压扁了他的身子,压破了他的肚子,五脏六腑全给压挤出来了,花花绿绿一大堆,好惨哟!
你心里暗吃了一惊,梦竟然同现实如此相同,难道现实的事物能通过一种什么样的物质做媒介,将这现实的事物传导到人的感应体里来,用梦的方式。你的惊异上又加上了一层伤悲的阴云,心叶像蚕噬一样,很多的泪流下你的两腮。
你孙子缄默了好一会儿,大概是见你极度悲苦而无言。待你的状态和缓了些,他说:“爷,我大死前常给我说你的故事,说你是个奇人。我说我一定要去看爷哩,我大就给我说了路道儿和地点,我这次来就是顺着我大说的方向和路道儿来的。”
你问你的女儿,你孙子说我小姑的男人到终南山里去挖药材给毒虫咬死了,小姑后来给个当官的做了小妾,随那当官的进了西京城,给家里来过两封信,后来的情况就不知道了。
你和你孙子正谈话间,毛胡的小女人来了。还未待小女人坐定,你家的大门又响了,于是听到一个很熟悉的脚步声,你忙隔门去看,果然是你的小表姨来了。
毛胡小女人和你小表姨面孔上都泛起了醋意,都觉难堪,虽然都笑着问了好,可笑得都很不自然,话也说得很涩巴。不过情敌之间,两个女人都很机警地镇静下来,一场绕花枪的舌战便开始了。
小女人说:“哟,她表姨总该发大洋财了吧,余大牙抢了那么多钱,总不会落到别家女人跟前去!”
你小表姨蝎子蜇了一下似的变了脸色,开口还击:“她姨,脱了两次衣服给余疯子看,总叫看出花来了。土匪都是驴种,越花越弄得凶,你能有命回来,是福大命大哟。”
你孙子觉着两个女人的话不是味儿,便怏怏地到后院窑里去了。
你好尴尬,在这两个女人之间。
你实在无法以任何一种方法制止她们那种轻妄、放肆、互不相容的势态。在你无奈的思忖中,两个女人不文不武、亦战不战的对话还在持续着,你溘然跪在两个女人面前,凄然地说:“两位小姨,你俩饶恕了我吧,我对不起你们,你俩都是为了我才作出那么大的牺牲,委屈了自己,我替你们死都难以报答你俩的恩情。这些事全都怪我,你们都罚我的罪吧!”
两个女人都有些懊悔,忙将你扶了起来,眼里都流了泪。
你小表姨说:“绪儿,都怪我,是我不是,我不该……”
小女人抹了下泪水说:“蓉儿姐,怪我不贤惠,爱争强好胜,其实咱们都是为了绪儿,何必这样呢?”
你说:“两位小姨都是我的恩人,我今生今世忘不了你俩的大恩大德,我对你俩是一眼看待的,以后你俩就别争了。”说着你从柜里拿出一包大洋,你说:“两位小姨为我作出常人难以作出的牺牲,这是无法以任何代价来补偿的,为表我一点心意,就这二百银元,你俩一人一半吧。”
小女人说:“绪儿,这几十年了,你还不晓得我是个啥人,你当我是个坏女人吗?是为几个钱的吗?”
你小表姨也觉你这举动深深刺痛了她的心,努了下嘴巴说:“我是从坟坑里爬了出来的,人不人鬼不鬼的,是你绪儿把我当人,我只图个真情,钱是什么?是狗屎,能污了人的良心。”
你说什么呢?瞬间,你眼前的两个女人变得有些陌生起来,陌生里放射出几十年来你未曾发现的无所比喻的光晕来。你自觉惭愧,愧不如一个女人,你眼里的泪水涌了出来,一串一串地掉在白白的银元上。
银元冷森森的。
好长时间你没去小女人家了,你想。
这一日,天色很蓝很蓝,很蓝的天空浮荡着一堆一堆的白云。白云的形状变变幻幻。有时变得轻淡如薄纱,有蝉翼般的透明,有飘然的感觉;有时变得如一堆棉花,蓬蓬勃勃,厚实而轻松。
你心情很好,如这天空一样晴朗。你约你小表姨到小女人家去吃秋果,你小表姨丰富的脸庞上很快地变幻了几种表情,最终的表情是灿烂的,如开花般的笑容。你小表姨爽然地应诺了你的要求,你自然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你想女人间的奥秘是难以探究的,你不知这两个女人还会有甚相怨的,你忧心忡忡。
小女人家的大门半开着,你推了一下门走进院子。小女人在院子里看树上的秋果,秋果在她的眼里像一颗颗琥珀亮着血质的灿烂,闪耀着流动的光泽,使她陶然沉醉于心灵如化的感觉中。轻柔凉爽的风无声地拂着叶子,使得秋果欲圆不圆,给她又是半残的梦境,她心里又有些凄迷。
你静静地看了一会儿小女人,如读一幅美人图,你见她的手臂裸露在半袖衫处,皮肤温暖滑腻,散发出新果的香气;乳房微微隆起,把衣衫掀起老高,使你瞧见了她白软丰腴的肚皮,你浑身骚动了一下。
闻得声音,小女人如梦初醒,转过头来见是你,向你盈盈地笑,使你在这个时刻感到小院儿豁亮得很,空气流畅得很。
大门外你的小表姨,脚步停留了好一会儿,她不随你进去,是想看看你和小女人见面会出现怎样的景象。她隔门窥了一会儿,见你和她都有种失态的忘形,脸上即刻盘旋起一片酸酸的醋意。她想退去。
你给小女人说:“还有贵客呢。”说着招呼你小表姨进来,你小表姨没回声,还在门外磨蹭。小女人轻盈地走了出来,见是你小表姨,脑中闪电一样迅速思忖了一下,笑在脸上开放了起来,忙说:“哟,当真是贵客,是绝美的美人儿,蓉儿姐,你能来我这穷家小户,真是我的福分。”你小表姨想对付小女人的欲念给小女人的热忱劲儿熄灭了,神色倒有些忸怩了,不好意思地说:“小妹话说哪儿去了,我来了你家怕给你留下穷气,要不然早就进来了。”
小女人立在凳子上,摘了满衣襟的红果子,边招呼声你和你小表姨进窑里,边将几个红果子塞给你和你小表姨。
你和你小表姨还未进门,就给一股浓郁的香烟熏得欲醉。撩起门帘进了窑门,一种令人吃惊异常的景象,使你和你小表姨都懵懂了,窑掌的墙壁上挂着一幅群鼠图,一群鼠们各持神态,精灵活现。鼠图前设着香案,香烟一炷一炷袅袅而上,倒使鼠们有了些许神灵之气。
你问小女人这是怎么回事,小女人的脸孔上即刻飞扬起一种迷人的光彩,她细长的眉毛闪动了几下,眼珠栩栩地转动着,心里有种难以抑制的激动。她说:“这是神鼠,那次狗娘养的那个野脚户黑祥将我装在羊毛口袋里,让骡子驮着进了北山,放在店家槽巷里,是这些神鼠救了我,咬断了口袋口上的绳子,才使我逃了生。我常梦见这些鼠们,它们都是些神灵,它们比猫好得多,侠义得很。猫给人娇惯坏了,整天吃着优好的肉,吃饱了懒得动,装模作样地摆出虎的威武姿态吓人,还口里胡编乱造地哼着什么慈善仁爱之经,蹲得无聊了,便跳下炕去找鼠们的不是,给鼠加上罪恶极大的罪名,将鼠扑杀。哎,你们说是猫好还是鼠好?反正我爱鼠,我敬鼠,它们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供奉它们,是愿它们的神灵惠及人们。我爱鼠,所以恨猫。我见猫就赶,猫见我就远远地躲去,因此,我与猫为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