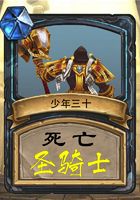日子蛇一样地蠕动着,悄然地爬进夜的黑洞。你以梦的形式在黑夜构思圣洁的白天,把美好的向往,羽化成缥缈的图像。
你梦见你在一座老庙跟一位很古怪的道人谈生存和死亡的奥秘。道人以圣哲的教语给你说了许多,你都能明其理,而无法记下他的话语,都如过眼烟云悠然逝去,给你留下忧郁的空白。你在空白里极力寻找,妄图抓到一丝语言的痕迹……
村子里的狗吠声一阵紧似一阵,从黑得无形的夜空直蹿到你的梦,进而,把你从混沌模糊的界域里拖了出来。你起死回生,坐在炕上,觉得浑身有汗渍的潮湿。你凝神谛听,老窑掌里漾起一阵鼠们求爱的欢叫,你很讨厌。你从黑暗里依稀看得出你的小妻春妹睡得很熟,小儿子丁必成偶尔发出模糊的梦呓。
突然,一种异常的声音从墙外跳入,院里顷刻一片杂乱的混乱情景。你即刻意识到劫难会像噩梦一样开始。这时你想起了你的老狗,你后悔不该药死它,它是个忠诚的卫士。还未待你过多忏悔的时候,你家老窑的门给一种巨大的撞击声轰开了,几柄在黑暗里闪烁着白光的刀刃直直地迫近你。春妹吓得发出极尖锐的号叫,即刻给一种粗糙如石头的喊声喝住了。你给捆绑了起来,一种疼痛死死地勒入你的骨肉,使你呼吸都有些困难。
老油灯给燃亮了。昏昏然的灯光暗淡地散射着狞恶的恐怖,老窑里呈现出坟茔般的死寂,充满一种暴戾的威胁。灯光里站着几个蒙面人,一切都给人模糊的印象,只有暴露出的眼目肆无忌惮地放射出疯狂的光芒。
你没有胆怯,一股怒气幽然地充满你的胸内,但你很理智,没有发作,即刻变戏法一样地装出一副笑脸。
你说:“弟兄们要啥,好说呀!”
为头的说:“要黑老缸!”声音粗硬得像石头。溘然,一种特别的讯息传导,使你脑里闪回四十年前,你偎在母亲羊膻味的老羊皮袄里,去宁州城过堂的路上遇到的那个骑大叫驴的孩子———是他,余疯子。
他一把撕掉蒙面布,粗硬地说:“明人不做暗事,我就是余疯子!今晚来就要黑老缸,兄弟,眼皮抹亮些,土匪的刀是干啥的,你不是不知道。”
你百无聊赖地笑了笑说:“什么黑老缸?只是听人说过我的老祖爷有个黑老缸,隔了几辈人,谁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余疯子狞恶地笑了一下说:“听人说你得了黑老缸想独吞。你要知道谁家银子堆里没有我余疯子的银子。”
你说:“这我知道的,我家柜里就有你的银元。春妹你快开柜给老哥取钱。”
春妹吓得战战兢兢,半瘫在炕上,只感觉一大片恐怖的黑毒气如潮如涌地向她滚来,她想今夜在劫难逃,心里悚然地惧怕。春妹听你唤声,忙爬下炕去打开老油板柜,取出一袋银元,银元在袋里碰撞出玲珑的响声,诱惑着土匪们大发其财的贼心。几个土匪躬身去取,却给余疯子喝住了。
余疯子说:“你于丁绪他妈的真是个两世人,也会骗人。不过,老子你是骗不了的!来,先将你抬举下,吊上大梁!”
几个土匪一阵动作,绳子在老窑的梁木上如蛇爬行,你给一耸一耸地吊上半空,绳子如牙齿一般向你骨肉里钻,使你无法忍耐地发出痛苦的呻吟。余疯子的牛眼向你奸诈地注视,等待你嘴里吐出黑老缸来。
你头颅僵硬地昂着,眼里放出惶悚的乞求,你说:“老哥,家里的东西你爱啥拿啥。”
余疯子冷笑了一下,笑得让人毛骨悚然。他用手托了一下春妹的下巴说:“我爱这美人,给不?”
春妹趔趄地退缩了一下,瘫坐在地上,若有若无地啜泣。
你闭嘴默然着,心里一阵惧怕,怕这土匪伤了春妹。时间在你的黑色恐惧里流淌,你等待一件不寻常的事件的到来。
余疯子又狞恶地冷笑了一下,长满毛胡的大嘴里喷出咄咄迫人的酒腥气味。他不做任何思索地举起马刀,用刀背很有声响地敲击了几下你的踝骨,踝骨即刻有一种坚硬感觉切入,一股冰冷的东西,如一种爬虫,自脚踝向脊梁骨蹿流而上,直涌到脑门。你啊的一声,只觉眼前的物体迅速分裂、解体、分化,化为一片模糊的暗淡。瞬间,你失去了一切控制力,屎节和尿水哗啦地拉了一裤裆……
春妹突然地爆发出无所畏惧的勇敢,她扑到余疯子面前,抱住余疯子的腿,如撼一棵大树一样地摇曳,发疯似的大喊:“你杀了我吧,你饶了他呀;啊,你杀了我……”
隔壁窑里,老油灯也早早地亮着,一个土匪用刀逼持着你的碌碡女人和丫头玉环儿,另一个土匪用刀撬开柜子,在翻腾着。其实,一个肥胖成一个废物的碌碡女人和一个十二岁的弱丫环是无须用刀威逼的,大概是歹人心虚,碌碡女人如大肚佛一般端庄稳实地坐在炕上,一脸下垂的肥肉难以表达出某种恐惧或惶悚的表情;眼睛给肥厚的眼皮挤成细眯的线条,也无法泄露出某种惶恐的神色。她挺着肥大臃肿的大肚,寂寞地坐成一尊弥勒佛的石像。玉环儿怯怯地躲进炕角里,用被子裹着身子,嘴儿咬着被角,眼里透出十分的恐惧,瑟缩成一只受惊吓的羔羊,不时地抽搐着空洞的鼻子。
逼持她们的那个土匪,脸上浮现出超乎刻骨的讥讽,沉默里充满着某种淫恶的歹毒,匪里匪气地觑着碌碡女人衣襟里袒露出来的肥得发白的胸部。他开始骚动了起来,向炕上爬去。这时,那个翻柜的土匪从柜里抬起头,瞪着眼骂道:“你驴日的别骚情,误了大事疯爷割你头喂狗呢!”那土匪乖乖地退下了炕。
几声长长的鸡鸣,穿透寂静得幽深而且无边无涯的黑色夜体,向老窑里传来,夜开始了萎缩。余疯子悟觉天快明了,他们折腾了有半夜,终未能从你口里掏出黑老缸的隐秘,贼心不死地将你押出了你家老窑,押出了你家的大院。
夜色不明不暗,川那边的山影巨兽似的蹲着,俯视着什么。风在树梢上不紧不慢地喧闹,像淫荡的男人。你被挟持而行,你眼里闪烁着土匪白亮的马刀。马刀似乎锋利地切割进夜体里,使夜体流出乌黑乌黑的血水,在地上汇成无边的血的沼泽。你被挟持而强行,走得极其痛苦,一颠一跛。每一颠跛都觉踝骨一阵尖锐的刺痛,像尖利的刺物直接刺入骨里。你弯躬着背,头颅怎么也抬不起来。你思忖着,你想余疯子是个毒虫,今晚你纵然生了翅膀也难逃这灭顶之灾。你不走了,你想走到哪里都是一死。你强行地站立住,浑身剧烈地哆嗦,像抖飞了灵魂,一切都觉得空兮兮的。你说:“疯子,我不走了,你动刀吧。”
余疯子说:“黑老缸是死物,命是活物,银钱去了会来,命丧了再难活过来,你为死物送命值得吗?”
倏然间你怎么忆起梦里那古怪道人说的“生中有死死中有生,死死不灭生生不息”的话来,你说:“疯子,别啰唆,怪烦人的。”
余疯子拍了一下你的肩膀说:“有种,老子的刀不杀好汉,放了你!”
一个土匪忙拽了下余疯子说:“疯爷,放虎归山,必有后患,放不得,这驴日的和县长有交情。”
余疯子没说什么,转身独自去了。几个土匪咕哝了一阵,一个土匪便晃了几下刀,刀刃上跳跃了几道白光,然后白光闪向你的脖颈,这瞬间你的意念闪电似的飞驰了一下———完了!你即刻觉得白光坚硬地切进了你的脖颈,脖颈索性萎缩了一下,一种冰凉的感觉渗入了体里。你倒在黑黑的野地上,身子伛偻起来,全身抽筋似的疼痛。但你马上意识到你没有死,急忙双手将头颅紧紧按在脖颈上,让断裂的生命焊接起来。这时刻,你脑里有一个顽固的信念,你要活着,你的头颅还在脖肩上。你坚持着这个不可动摇的信念,坚持生命的顽固和强悍。你觉得身子轻悠悠的,像浮在地上的一团棉絮,仿佛有一阵风吹来,就会飞起来。你想看一下这世间,可觉得眼皮很重,涩涩巴巴地黏合在一起,怎么用力也睁不开眼。你双手不敢掉以轻心地按着头颅,唯恐生命从脖间断裂。你觉得头颅木木的,像个他物,只是有膨胀的感觉,像个过多充了气的气球要爆裂似的。按在太阳穴上的手指,感觉到有凸突的青筋如蚯蚓一耸一耸地弹跳。你想你一定要活着,一定要雪这仇恨,不雪这仇就不姓于也不姓丁,就誓不为人!
春妹的呼号声凄凄地透过灰白的黎明,切切地传到你的耳里,你不禁心里弥漫出一股苦悲来。你的脑子清醒又似乎迷糊。春妹和村里好多人赶来,毛胡的小女人也风火火地赶来了。见你这景况,村人都骇得懵懂了,不辨死活。春妹忙扯了衫襟和小女人给你缠束脖颈。小女人伸手摸你胸膛,觉你心在腔里怦怦地跳动,她惊呼你活着,春妹也惊呼你活着,说你鼻里有气。
村人帮春妹用门板将你抬了回来,你清醒地觉得你又如生下那时,无可动作地躺在了老窑里的黄土炕上,只是没有母亲产期血尿腥臊气。你想说话,嘴却像是别人的,你无法使它活动起来。于是你只好沉默,只好静静地听辨他人的话语。他人的话语在你耳里,如蜂吟一般,也难辨出意思。你心里很悲很苦,恐你会死去的,但你却要顽固地活着,活着还有新的故事演义……
春妹请来了陆九少。陆九少佝偻着十分老朽的身子,瘦竹节似的手指切了一会儿你的脉说:“脉还好着。”
拐子刘说:“日怪得很,这人头刀砍了咋还能安得长上的?”
毛胡说:“这事多得很,三国的魏延头割掉自己就能安上,要么马岱怎么要在虎土桥上斩魏延,是为了让河水将魏延头冲走……”
陆九少说:“这等时候了还谝屄儿,快想方子弄些刀尖药,伤口才能愈合。”
毛胡说:“哪儿弄去?只有余疯子有刀尖药,谁敢求那土匪种去?”
小女人敢。
小女人领着白骟狗,匆匆行了大半天才来到老爷山下。此刻间,沉重的暮色从沟底冉冉爬起,铜锈般的云片在头空迅疾地漂流,使山野的景物蒙上一层深秘的魔幻色彩。山涧的流溪在石崖间闯荡,发出弯曲的鸣叫。林子里的兽物也以怪狞的叫声开始呼唤黑夜。小女人心里有些恐悚,她从腰里掏出酒瓶,咕咕地喝了几口,呛得她美丽的脸都扭曲了起来。她连连地咳嗽,酒精在肠胃里汩汩鸣叫了一会儿,迅速地深入体里,无法排斥地在体里开始恶性地发作。她有了醉意,白白的脸上漾着红霞一般的红晕,目光迷蒙,心里热辣,骨子酥酥软软,她脸上有了开花般的微笑。她无所畏惧了,晃晃摇摇地在野路上跋行,小小的脚步在弯弯的路上印下美丽的脚印。白狗忠实地尾随着她,用鼻子在黑色的夜气里嗅辨着山野的动静。
半夜时分,小女人的小脚踩破了山寨的梦,她给两个土匪押进了余疯子住的老屋里。余疯子刚穿了衣服,衣襟敞开着,满肚子的黑毛呈现出野性的凶悍和疯狂。他见是小女人,两竖长长的眉毛鸟翅一样地扇动了起来,眼里放射出火辣辣的光芒。他问:“半夜黑天的,你闯这山干啥来?”
小女人醉意未消,酒使她壮起胆了,她说:“疯子,我来求你。”
“求啥求?”
“求你要些刀尖药。”
“要求干啥?”
“绪儿给土匪砍了头,又安上了,要刀尖药才能长好。”
余疯子震颤了一下,两只牛眼睁得更大,他问:“头砍了,还没死?”
“没死,头又安上了。”
“啊!”余疯子急转了几下身子,身子扭曲了又回复原形,“真是大难不死!”
“我求求你行行好,救他一命吧。”小女人溘然跪在地上,“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
余疯子骚野地狂笑一声说:“我要你人,我要和你睡觉。”
这是小女人早已料想到的,她毫不踌躇地站起来说:“有种的就说话算数,睡了觉,就给药,让我走。”
余疯子拍了下毛蓬蓬的胸膛说:“好汉说话算数!”
小女人说:“我信你。”转身走到炕边,动手解开了衣纽。衣裤浪漫地从她身上滑落,裸露出白玉雕一般的裸体来,曲线流畅得有种滑落的感觉,荡漾出难以言喻的奇妙气息,光晕勾人魂魄。余疯子眼里喷射出杏黄色的淫光,灼灼地抚摸着小女人的身子。突然,他的目光僵死了,他的浑身震撼了起来,灵魂似乎飞出了体外。小女人物儿白白光光,突出地亮在他的眼前,使他野牛一样的汉子矜持起来,害怕起来———白虎星,伤主惹祸啊,可招灭顶之灾呢!于丁绪和这女人睡了,招了这杀头之祸,我可不……
余疯子牛吼般喊起来:“滚,滚,快给老子滚!”转身从木柜里拿出个小瓶,“给,给你娘的刀尖药,该他于丁绪阳寿没尽!”
小女人不慌不忙地穿了衣服,拿了药瓶,在余疯子的喝赶声中出了老屋下山去了。余疯子唤了人拿了火把点着,在屋内外燎了半夜,驱邪送瘟似的肃尽小女人留下的不祥的邪气。火把在山头上晃来晃去,明明灭灭,使山夜荡漾着恐悚的深秘。
你得了小女人弄来的刀尖药,伤口奇迹般地愈了,你又神话一样地死而复生,脖颈留下了竹节般的刀痕,呈现出生命焊接的神奇。后来宁州续志,将你这令人难以置信的奇事在《宁州志》的奇闻轶事里作了如下记载:
民国某某年仲秋之一夜,匪人闯入于家山弯乡民于丁绪家宅,捆缚主人,逼索巨银。于不肯,匪人将其挟持于野,刀杀头颅。匪去,于觉自活着,忙将未垂之首接合起来,死而复生,实为千古奇事也。
北阳河依然在不息地律动着,涌动着你不安分的心。你坐在门前老槐树下青色石墩上,觉得石墩坚硬而冰凉,于是你站了起来,走到门畔,望着川道里收割后的秋野,心里酝酿着复仇的毒恶。
你小表姨来了,她虽有了相当的年纪,却丰韵未减,仍能倾倒汉子们。她扭着曲线优美的腰肢姗姗地向你走来。你看见两只花蝴蝶扇动美丽的翼子,飘上飘下忽左忽右地追随着她,你似乎嗅到她身子上漾出明黄的花粉味,空气里充满了温馨的梦幻气氛。你心里说小表姨是朵不凋谢的花。你心里说这话的时刻,你浑身骚动了一下,一连串的往事以幻影的图像闪过你的眼帘,你将遭劫的事儿一扫而光。
你小表姨亭亭地伫立在你对面,她没说什么,心里一阵酸楚,委委屈屈地哭泣,声音像蜂吟一样有催眠的效应。
你小表姨用白白细细的手儿抹了下眼泪,脸上骤然有忧郁和欢悦徘徊。她娓娓地说:“这事儿我昨日才听人说的。你出事的那夜里,我做了个梦。梦见天空闪了一声雷,你家门前的大槐树给殛断了,在一瞬间又恢复了原样,只是断裂处有了节疤。”
你说:“小表姨的梦神了,是给我梦的,你看我脖上不是生了节疤。”你弯腰给你小表姨看。你小表姨用细长的手指抚摸你后脖颈上鼓凸出的节疤,手指像触着了蚯蚓一样弹跳了起来。
你说:“小表姨,你听谁说的?”
你小表姨说:“我男人的堂表哥余大牙说的,余大牙也是个土匪种,和余疯子是远房兄弟,可两人是两个山头,面和心不和,谁都想干掉谁。”
你说:“余大牙常来你家吗?”
你小表姨说:“隔三岔五地常来,常想动我,我一见他那翘得老高的黄板儿大牙,就恶心得像吃了蝇子,肚里的东西都翻腾了起来。”
你脑里闪过一个恶毒的计谋,你在你小表姨耳畔悄悄地咕哝了一会儿,你说:“小表姨,我为难你一次,大事成了,我用一百两银子酬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