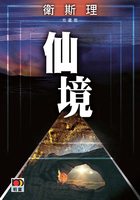忘却了的或说是断了章的故事,穿过十多年时间的距离,如同构思一般地又连接了起来,再度地从荒诞走向现实。
……还是那夜那轮月亮,把女性的温柔和妖媚轻轻斜斜地印封在两扇具有男性坚韧的大门扇上。那时光,一头老牛忧郁地站在门前,扬着头颅长曳曳地哞叫着,哞叫声很亢奋地走进小女人父亲的梦里。小女人的父亲慌忙从梦里爬出来,跑出去开了大门,见老牛独独地立在门前,若有所思的样子。
毛胡呢?他怎的没有回来?疑虑如一团云弥漫了他的脑际,他紧张地构思每一种假设。他扛了镢头,匆匆地赶到野沟里,见牛车孤零零地躺在草地上,像一头残惨的怪兽,蹲在野地上惆怅地望着冷月。小女儿的尸首不见了,毛胡不见了。他想起那些奸尸的传说,他想毛胡是会干那种事的,毛胡一定背了小女儿的尸体到山洞里奸尸去了。他找了好多山洞,空无人迹,他是愤是怨地回去了。谁知多年后,脚户黑祥突然神秘地对他说:“老爷子,我见到了你的女儿,她没有死,她是给毛胡拐跑了。我这回赶脚住在那个村里,是个山塆子,我看得很清楚,是她,没一点错。”小女人的父亲沉了一下脸,心里毒毒地想,不能便宜了你毛胡。对黑祥说:“这事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再不能传给别人。你这次下去把她给我偷偷抓回来,我给你一百块大洋。”黑祥笑眯眯地应了。
在一个黄晕晕的暮辉满山顶上徜徉的黄昏,寂寞叮咚的骡铃声敲着塆道旁的蓝岩崖和蓝岩崖下的北阳河。北阳河运载着金属片似的波光,也发出金属的敲击声。黑祥偏坐在骡子驮鞍上,扯曳开粗野野的嗓子,唱着酸酸的野曲:
羊肉泡子死气了干家哥,
咱俩个臭名出去了干家哥。
怀揣馍馍向外扔干家哥,
狗撵馍馍你进来干家哥……
毛胡小女人正在泉里打水,水桶底刚触及泉水,泉里平静的水面被击起一圈一圈美丽的涟漪,涟漪里扩散着一个漂亮的面影。她正痴痴地看这面影,忽听塆里转过一溜“脚户调”,抬头看,见官道上骑着骡子的黑祥正邪眉邪眼地看她。她知道脚户都是骚熊,野曲是唱给她听的,她用十分的敌意斜瞪了一眼黑脚户,心里恶骂:“叫老娘进来给你喂奶!”她打了水,挑着,姿势很优美地走了。
黑祥把骡子吆进了店,他是住进拐子刘家的。半夜里黑祥就起来折腾,给骡子备上鞍子说要赶路,急急地去了。
黑祥并没有急急地远去,他将骡子拴在小女人家门前的歪脖子桑树上,他如野猫似的翻上墙头,在墙头停留了瞬间,瞬间里是察视院里的景况,他贼眼溜溜地瞅见小女人的门半掩着,他毛脚毛手地跳下墙,蹿进了小女人的窑。
小女人沉溺在脉脉温情的梦里,一阵亲吻,她的冲动如潮涌一样漫上她的唇边,使她嗅到了男子汉粗悍的鼻息和宽阔嘴巴的压力,她开始出神入化地呻吟……
黑祥的眼前是一个绝佳的睡美人,她已蹬掉了被子,裸了全部的身子,在窗外透进来的朦胧夜色里,她玲珑地展示着她能够诱惑天下所有男人的丰美,况且从梦里发出邪迷的呻吟,黑祥看得狂馋,嘴里不住地咕噜着咽口水。他欲动身向她山倾般地压下去,在这错误行动的一刻之前,他顿悟这种行动后果的严重性,忙拿了手帕,塞进小女人淫吟的嘴里,不及小女人走出梦里,他已将小女人的双手用裤带缚捆了起来,而后,将小女人和小女人的残梦一同装进了黑羊毛线口袋,扛出院子,架上骡子的驮鞍驮走了。
小女人伏在骡子背上,作如何的挣扎也难逃脱这场灾难,她觉着她给一种阴森森的不祥之气包围着,心里隐隐约约地害怕。但她只能如此浑浑噩噩地被骡子驮着颠簸着,在悠悠荡荡地颠簸中,她忆起梦中零零碎碎的片断,她极力地连缀这些片断,使它系统化故事化,但是一些场景和人物淡化得隐乎不清了,唯有你趴在她的肚腹上,怎样地吻她弄她,每个细节都如影片一样清晰,生动活泛起来。
天色很灰,云层低低地压向黎明,似乎是要下雨的。黑祥怕人赶来,又怕雨阻路。一切想入非非的事都无可顾及,不断地用鞭子赶着骡子。骡子的蹄声骤骤地叩击着灰灰白白的官道……
野浪汉子毛胡去南塬野逛了十多天,在小女人被黑祥驮去的第二日夜里才回来。他见窑里一片狼藉,不见小女人,以为这懒婆娘一定去了你家逛得没回家,就到你家来找。当时你还在梦里,你梦见你脱光身子睡着,迷糊间一个黑汉向你匪里匪气地走来,撕掉你一条裤腿拿着逃跑了,你想追赶,却怎么也起不了身,你大呼,你的碌碡女人用肘捣了你一下,你才从噩梦里醒了过来,自觉浑身汗津津黏糊糊的,你觉这梦荒诞极了,那黑汉是行盗行劫,为甚只要一条裤腿呢?你正在百思不得其解时,毛胡在大门外呼唤着你。
毛胡进了老窑,问小女人哪去了?你说:“这些天我忙乎了我大的病,没见过她的面。”毛胡一听心里有些毛焦,忙叫你一同去假凤凰家看,假凤凰和拐子刘为了满堂媳妇一出门十多天不回的事正吵架,拐子刘骂假凤凰不施家法,放开满堂媳妇跟野男人胡逛,弄不好叫人拐跑了。假凤凰一拍大腿瞪了下公鸡眼说:“不叫跑哪来孙子,你娃没门你来弄,行吗?”气得拐子刘用拳头直砸脑袋。
你和毛胡进了拐子刘家,问起小女人,假凤凰说:“大前天到我家来过,自后再没见人影儿。”拐子刘有些惊悟,说:“大前天夜里有个黑汉吆了骡子在我家住店,半夜里就走了,第二天我见骡子在你家门前的桑树下屙了几疙瘩粪,怕是在桑树下拴过,你女人怕是被脚户拐走了。”你忙问:“你知道那个脚户是哪里人?”拐子刘说:“不知道,大概是陕北一带的。”
你一夜未睡着。
毛胡一夜也未睡着。
你的眼睛酸楚楚的,直想掉泪。
毛胡的眼眶火辣辣的,像要冒焰。
你和毛胡同睡在毛胡家的土炕上,用各自的抒情方式想象着小女人。你在暗暗祈祷命运之神庇护小女人安然无恙之后,你怅望着窗外那方汹涌着云浪的天空,在雷电里一明一暗,你的思绪随之逶迤起来。你想象出一个荒诞不经的鬼怪故事,这故事是从你梦里被那黑汉抢走的那条裤腿开始的。不知怎的你的两条裤腿一条是你小表姨蓉儿,一条是毛胡的小女人。小女人被那黑汉抢走了。黑汉忽地变成了魔怪头,头上有角,身上有刺,面目狰狞得可怕,像一只黑豹。黑豹将小女人拖进了岩洞……
毛胡也想象出一个故事:小女人给黑汉奸淫了,奸淫得无味了,又将她卖给一家老财做妾,老财已经老朽了,佝偻着干瘦的身子,咳出连串的黄痰,还要搂了她睡觉,她凄凄地哭着……
这时,大门外又响起了急骤的敲门声,你母亲泪兮兮地喊叫你:“绪儿,快,你大病又严重了……”
荞麦花开时节。
满坡满坡的荞麦花红粉粉地全开了,大面积大面积地覆盖土地和人生的贫瘠,描绘乡土的梦恋。
这个时候,你父亲已经奄奄一息了。
你父亲吃了假凤凰端来的诱惑十分香香生津的凉粉鱼子,肚子就开始了疼,到了夜间,你父亲屙了许多血,吐了许多血。你母亲请来了陆九少,陆九少把了下脉,摇了摇头什么都没说就走了。你从毛胡家赶回来时,见你父亲用双手抱着干瘪的肚腹,当年极健壮极有力量的腿已经瘦得如两根竹竿了。你父亲的身子剧烈地抖动着,牙齿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老裂的嘴角流淌着暗红色的血丝,眼睛睁得大圆,有种死难瞑目的意思。
于八举来了。他已经是白须白眉的老者了,他用很白的眼光瞧你父亲,见你父亲难咽下人生最后一口气。八举爷白胡须间抖出白白的话语:“憨二,你还有啥牵心的,说吧,说了就去吧。”你父亲已经不能说话了,他用睁得大圆的眼睛瞅了下八举爷,又瞅你,最后瞅了你的儿子必兴一下,你和八举爷都明白你父亲的意思。
你泪兮兮地说:“大,你就放心地去吧,我定给你养个孙子。”你父亲忽然眼睛亮了一下,又忽然熄灯似的闭了眼睛,他不再看这人世一眼了,他进入了一个幽冥的未知世界。随着你父亲咽下最后一口气,你们全家人轰炸性地暴发了哭声,哭声轰轰烈烈地震动了黑沉沉的老窑。
你母亲孑然地站在哭声里,她没有哭声,只是凄冷凄冷地流泪。她多像黄昏雨之后破篱下独守寂冷的母鸡。你透过蒙眬的泪水,望着你母亲若荒原上独一的一棵古树,在冷萧萧的风中做着冗长的呻吟。你放声号啕大哭,一半哭你父亲,一半哭你母亲。
第二日,你家的亲戚在听到报丧之后都急火火地赶来了,丁四海领了丁家一帮侄男来得很早。丁四海的头须大半都变白了,稀稀疏疏的,像旱塬的草。丁四海被两个侄儿搀扶着走到你父亲的灵榻前,颤巍巍地呼唤着你父亲的名字:“憨二,你咋走在四叔前头去了?四叔来看你来了,憨二,你看得见四叔吗?”他已老泪横生了,一滴一滴地点缀在你父亲的蒙面纸上,开出无什么颜色的菊花来,他用老瘦的手轻轻摸你父亲的脸庞,他感觉到你父亲脸面尽是很突出的棱角,肉像给骨头吃了。
你父亲穿着他一生从未穿过的崭新的衣服,也就是寿衣,旁若无人若无其事地睡在灵榻上,他的生命似乎从他冰凉僵硬的肉体里散发出来,似一种无可视觉的灵光弥漫于灰蓬蓬的烟雾中,潜伏在老窑里的空洞中,神秘而又玄妙。你和你的家人以及丁氏族里来的比你父亲低辈分的侄孙们,都穿了白白的宽绰有余的孝服,如一群白白的绵羊跪在灵榻左右为你父亲守灵。你感觉得出你父亲的存在,你感觉到他诚悫而又憨厚的灵魂就浮动在你的周围,以一种莫可名状的渗透力向你体骨里注入一生唯一的希冀,你渐渐觉着身子丰盈了许多,你感到周围的空气都是鲜活的生命,这生命如藤如蔓顽强地坚毅地延续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