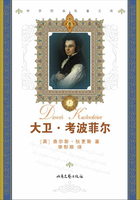秋阳很娇艳。天气酷热,空气里似乎有黏黏的汁液,触在人肉体上黏黏糊糊。繁茂的果丛在风骚的空间涌动着,阳光在累累的果实上雀跃不已。平日里自然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守务一方庄稼,和谐而孤独。
你父亲丁老憨(村里人不再叫他憨二了,他已有了几分年岁)送你去上学堂。这学堂是八举爷义举的村塾。村塾设在三圣庙院里的几间瓦房里,先生自然居上房。走在村塾门外,你父亲突然对你说:“这门是孔夫子的门,教娃成人哩。我没进过这门,一辈子就刨土了。娃呀,你进了这门就要学好的,要学做人上人。”
你父亲的这些朴实得如泥土一般的话,蕴含着庄稼人望子成龙的意义。你很感激你父亲,你应诺他的要求。进了先生的居屋,你看见先生很斯文地正在摇头晃脑地念诵书文。先生的脸方正且宽阔,下巴上有了刮掉胡须的青苍的颜色。先生眼睛很大,目光像在探求什么,专注得很。他的身体结实得让人感到他能驮起一座小山,浑身蓬勃着一种不可遏制的活力。先生身着藏青色的长衫,在酷热的天气里,让人极感闷热,有种近乎滑稽的印象。先生姓罗,人都称罗先生。
罗先生见你和你父亲进屋来,放了手里的诗书,也停止了念诵。你父亲很诚悫地躬着身子说:“罗先生,娃引来了。绪儿,快给先生叩头。”你忙伏下地,给先生行了个大礼———磕头,头低垂于地,而屁股翘得很高。罗先生看了你几眼,问你父亲说:“叫于丁绪吧?”你父亲嗯了一声。罗先生说:“听说这娃聪颖得很,可进了儒门,就要接受教化,遵守村塾里的规矩。犯了规矩,就得受惩。”他用目光指示了一下墙上挂着的足有二尺过五的戒尺。你眺了一眼戒尺,手掌肌突突地跳动了几下,手掌生了一阵疼麻。你给先生点头应诺。先生呼来了也在念村塾的你的堂哥学谦,领了你到学屋里去。这村塾里有十来个学生,大都十五六岁了,你在他们中间如骆驼群里的羔羊,小得可怜。可是你机敏过人,一点也不畏惧他们挑衅的脸色。
没几天,罗先生惊异地发现你能把《百家姓》《三字经》过目成诵,在学生面前称赞你是天才,是神童。先生称赞你的时候,你的堂哥学第很响亮地放了一个屁。先生脸上顿生一片愠怒,取了戒尺,训斥你堂哥学第是愚顽之徒,以屁辱人,不可恕也。先生狠狠用戒尺打了学第的手掌,打得学第袖了手哭泣。你心里很痛快,但你知道这痛快不能露在脸上,你依然装作胆怯的样子。
一日下午,先生背了手去外面游风景,学生念诵诗书的声音渐渐小了。几个年龄大的学生凑在一起,议论着可怕的戒尺。你虽然从心里瞧不起这些愚得如牛的家伙,念了几年书竟然不知子曰是什么意思,但他们都生长得粗粗壮壮,打人凶得很,你不得不去亲近他们。你上前去搭讪。
学第说:“尿激劲儿大得很,给戒尺上撒上尿,戒尺就会变得酥软,先生一打就闪坏了。”
一个年龄大的学生说:“那谁给戒尺上撒尿去?”
你为了讨好这伙年龄大的学生,不知这是你堂哥报复你的阴毒的计谋,就自告奋勇了:“我去。”
学第拍着你的肩膀称赞你是小侠客。学第给你说:“你去撒尿,我们给你看先生。”
你应了声,挺了胸膛,气概昂扬得很,很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侠士气度。你进了先生居室,取下戒尺,拿出你那茁茁壮壮的圣物,给淋了尿。
先生看风景看足了兴,在秋风疾疾地催促中,先生摆着稳健的步子回来了。先生进了屋室,很敏感地发现戒尺哭啼似的掉眼泪,这眼泪一滴一滴掉在地上,摔成花瓣儿。先生顿悟了什么,忙喊学生集合。学生们慌慌跑来,在先生的居室前,雁队一样排列“一”字形。你心里不安了起来。
先生提着戒尺,站在石台上,居高临下地发问:“谁干的?”
学第说:“先生,是丁绪干的,他给上面撒了尿,说撒了尿,板儿就变得酥软了,一下就闪坏了。”
你气恼得几乎暴跳了起来,你心里恶恶地咒骂你堂哥学第是天下最坏的坏种,你也自我忏悔不该中了这家伙的阴毒圈套。可你没容分辩地给先生喝叫了出来。
先生手中的戒尺,在空中画了个弧线,很优美地落在你的手掌上,你嫩嫩的手掌即刻变白又变红,生出尖锐刺激的剧疼,你哇哇地哭了。透过盈满的泪水,你蒙眬地瞧见先生手里的戒尺依然完好无损,你才知这尿激的荒诞和可笑。
先生惩治你之后问学第:“你怎叫他丁绪?”学第说:“他是丁家的种。”先生大怒:“于丁绪是县长赐惠之名,怎么你犬口胡言。”先生喊出学第,用戒尺在学第的嘴巴上重重地打了两下。学第的嘴流出很鲜艳的血来,淌在地上,开出一朵一朵红红的红玫瑰。先生问学第:“他叫啥?”学第支支吾吾地吐出三个血红的字音:“于———丁———绪。”
你瞧见你堂兄学第血糊淋淋的丑相,心里产生了一种超越痛苦的愉悦,你简直有点得意忘形了。
夜里,你难入梦。梦像一抹雾翳,匆匆地离你远去;疼痛、惶惑、悒郁,像洁白的月色笼罩着你的脸,你懊丧而且惘然。手掌肌高高地凸起,火烧火燎地疼痛。你想用什么美好的回忆,冲淡或者代替这种疼。微合眼帘,用迷离恍惚的醉眼眺望夜色里的星斗,星斗故作神秘的诡笑,似乎对你传播一种内容复杂的昭示或者是迷惑。忽然一颗燃烧着的流星拖着一道红亮的弧,滑过幽蓝的夜空,残骸不知坠落在什么冥冥的去处。
你心颤动了一下。不知怎的,你联想到你的小表姨蓉儿,空旷静谧的夜里,你骚动地不安分起来。你想起蓉儿给你讲故事般地叙说她懵懂地从墓穴里爬出来,夜空布满浓重的黑色,黑色里弥漫着恐惧的毒素,天空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只有比夜色更黑更浓重的云在涌动着。她用山里人走惯夜路的感觉寻找出路,几乎是匍匐爬行。突然一阵狼的嚎叫在不远处扬起,她每根发丝陡然硬扎扎地耸起,浑身分裂开来。在这要命的时刻,她的身后走来一只小小的野物,她是凭感觉知道它矮小而机敏,她是山里人熟悉那正是豺狗。
豺狗尖尖地吠叫了一声,吠叫声锐度极强地刺向夜空,狼嚎声溘然消失了。豺狗是山里最厉害的野物,老虎都怕它得很,它能神速地叫兽们无法顾及,从兽们肛门里掏出兽们的肠子。它是人的保卫者,夜里常将夜行者护送到家门,便轻轻吠叫一下,象征着道别,转头就钻进黑夜里去了。豺狗对她很友好,爽爽地在前边给当向导,一直将她护送出山里……
你想入非非地想得到一只豺狗,一只能为你负责全部安全的神兽。你的疼痛在你美好的想象中无有一丝儿了……
村塾院子里,有两棵树的风景。两棵一柏一槐的树,一样高大,一样挺拔,直直地矗立在三圣庙的两旁,总在比试着审美的价值,炫耀生命的伟岸。槐树用叶出叶落标示出分明的四季,而柏树有着常青不谢的性格,给生命赋予色彩永恒独特的意义,四季如一的青翠。于家 人说这是两炷天香,供三圣母享用的。两棵树中间有一石墩,石墩上置一很大的石盆,是过庙会时人们焚香用的。
罗先生每日清早如恋地要抱起石盆在院中行走三圈,脸不改色,口不喘气。之后,他又要去大门外二十步处的石泉中舀水洗脸,冬夏不误。八举爷说罗先生不但一身书卷气,更有武举的豪放风度。
这石泉清冽得很,水自泉底涌出,旱不减少,涝不增多,水味醇香,冬暖夏凉。村里老年人说,这石泉处原是干枯的石窝,自三圣庙建起,一夜之间成了石泉,说这是三圣母的洗脸玉盆。村里有一个传说,说八举爷的娘夜里做梦,梦见她口很渴,一个仙女给她舀了勺石泉水喝了,她顿觉自己肚腹膨大了起来。梦醒后她觉得有了身孕,后来就生了八举爷。
一日中午,罗先生睡午觉,学生们还未来,一种诱惑使你悄悄推开森严的庙门闯进了庙殿,众多缤纷的壁画和众多立体的泥塑,孤独寂寞地以一种审美方式的存在,给你显现了另一种风景。飘游的神话,静止的美,使你和一种精神通融。每一尊女神像犹似如期开放的鲜花,丽质照人。恍惚间,你敏锐地发觉三圣母的模样儿和你的小表姨蓉儿如此的相像,那直棱棱的鼻子,那细长明秀的眸子,那小巧艳美的芳唇……无所不像。遽然,你跨越神与人的分界,走入人神归一的境域,你抱住圣母的脖颈儿,狂狂地吻了起来。
于学第报复你的日子终于来临,他把你的行径在门缝里看得很清楚,加了夸张的创作,动作辅助着言语,形象生动地报告给先生。先生取了戒尺,怒不可遏地骂你:“小牲畜,竟敢淫辱神像……”戒尺炮雨般地在你满身飞落,打得你鬼哭狼嚎。打了之后便是惩罚,先生呵你跪在神像前,头顶香炉,燃了香,向神灵乞恕。
你一丝不动地跪在地上,膝盖骨像钻进一群蚂蚁咬噬般尖疼,你无声地哭着,眼泪有声的在地上叮咚。直到香燃完了,先生才赦免了你。你回首见你堂哥学第脸上飞扬着满足的神色,你心里燃起仇恨的火焰,如黄昏的火烧云燃着了三圣庙。
时光和谷物喂养你的年轮,你在浓烈亲切的阳光里和星星的童话里生长着成熟和智能,年轮里数不清了你伤痕的层次,断裂的童年给你留下记忆的残垣和斑驳的伤痕。
你十岁的那年开花季节的那一日,先生不在了学堂,学堂成了你们学生的自由国土,你顿生了最有玩趣的主意———摆神坛。学生们雀跃了起来,搬了桌凳便在院里搭起了六层高的神坛,仿效村里死了人搭筑法坛为死者祈祷神灵驱除鬼魔的样子,你饰法师,坐在最高的坛首上,摇着先生上课时摇的铜铃铛,吟诵着经文。七八个学生扮了乐师,分坐首坛两旁,敲击着脸盆、铜壶等诸多“乐器”,坛下有许多学生跪拜着焚纸。
你回忆儿时的见闻或者是前生不灭的记忆,你能一字不漏地背诵出《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经》中的《妙法莲花经》。你效仿着何阴阳的声调,摇头晃脑地吟诵着:
我为汝略说,开名及现身。
心念不空过,能灭诸有苦。…………
或在须弥峰,为人所推坠。
念及观音力,如日虚空住。
诵声悠扬,乐声苍凉。坛下纸灰纷然,如一群黑蝴蝶或者黑蝙蝠,蹿上头空,翩翩而飞,又像一群鸦雀,在两棵树的枝杈间或栖息或飞舞。碧悠的苍穹之下,学堂呈现着庄穆、深邃、缥缈、幽寞的氛围。
先生回来了。先生没敢走入村塾大门,他怕学生受惊弄倒神坛伤了学生,便遏制愤怒,站在门外,等待这种天趣的终时。等待是一种灼热的状态。
天趣凋零,你和他们终于走下神坛,先生如期而至。你们惊吓得丧魂落魄,怯怯地站成一排哀鸿,等待先生无可容恕的惩罚。等待是一种冷酷的状态。
先生的戒尺如你想象的,在空里闪烁着白白的光弧,牵引着呼啸的风声,从头至尾地在你们每人的手掌上跳跃了十下。从始至终,先生没说一句话。一句话不说的缄默,是先生最可怕的愤怒。先生罚你们在很旺盛的阳光里站到日落的时候,午间自然的没有吃饭。
你们的野性并没有被训化,逐渐产生了报复的心理。后来有几个年龄大的学生和你住在村塾,晚上夜习。一晚先生出门去了八举爷家,自然是请教八举爷去的。你们找了几件山羊皮袄,翻穿起来,扮成几头怪兽,潜伏在有风景的两棵树下。先生踏着黑漆漆的夜色回来了,刚进村塾大门,见几头黑毛蓬发的怪兽从树下爬起,向他突然攻击过来。先生来不及思辨,转身逃出大门,从门外的土桥上掉下,栽倒在荒草沟里。
你知道闯了滔天大祸,甩掉山羊皮袄,去抬先生,先生已气息奄奄了。先生扶回后,不省人事地睡了好几天,才慢慢醒了过来。他说他可能触犯了神灵,遭了神犬的惊恐。你们觉得好笑,但这笑只在心里,万不可露了秘密。自后罗先生便一蹶不振,神志恍惚起来,不久便辞退回老家去了。村塾一时聘不到先生,也就关门停学了。这便是从学的终日,在你心灵里埋下了对罗先生无限的愧疚。于是,你告别盈满书声飘荡墨香的学堂,走向人生的另一个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