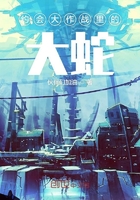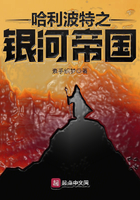那人用难听的日语叽叽咕咕又讲了一大段,听语气是在威胁她。
卫萌咳嗽几声,说:“我不会让步的。”
看不见的人气急败坏用中文说:“你的朋友,将因此而死。”
卫萌淡淡一笑:“随你。不在乎。”
你怒气冲冲瞪着卫萌。卫萌转过视线。那人说:“好吧!今晚24点为止,希望你好好考虑。”于是从上层传来清晰的脚步声。他走了几步,突然又回转过来,补充说道:“对了,新年快乐。”
之后就再也没有说过话。
老周坐在石床上,低垂着脑袋。你站起来,他立即抬起头,用一双黯淡的眸子看你。你只好重新坐在卫萌身边,脱下外套给她穿。
连续这么多天来,卫萌第一次露出忧郁的表情,呆呆看着石壁。
你想好言安慰她几句,又不知从何开口,只说道:“怎、怎么回事……?”
“没怎么。前男友。”
……你脑中浮现刘德华无比喜庆的《恭喜发财》的歌声。
2月3日
“上部呢?”
胖胖的青年回头问道。
随从慌忙递上湿巾:“启禀青年同志,老人家已经上飞机了。”
青年点点头,沉吟半晌:“我爱这个国家。”
随从陪笑说:“没有人像他和您这样,热爱这个国家。”
青年吐了一口烟:“哥哥们呢?”
“也妥善处理好了,请您放心。”
青年轻轻哼了一声,像是在表示满意。他一手夹着烟,一手用湿巾擦了擦胖胖的脸颊,感觉精神好了一些。
“今天,是新年啊,”青年没话找话似的说,“和家人团聚了吗?”
随从手心满是汗,不敢说“陪您上飞机怎么还能和家人团聚”这样的话。只能勉强答应了几声。
青年又说:“很久没和上部一起吃饭了啊。还有哥哥姐姐。我们这是去哪?”
飞机引擎发出呜--嗡的轰鸣声,在跑道上缓缓前进。
青年的脸色不太好。他有些晕机,丢了一块口香糖在嘴里。起飞的时候,青年身体僵直,紧紧靠着椅背,随从和他两个人沉默相对,很久都没有说话。飞机进入巡航阶段后,青年吐出一口长气,松开拳头,重复了之前的问题:“我们这是去哪?”
随从擦擦冷汗:“古巴。”
青年低着头,思考了好久。“传播得很快,是吗?”
“是,同志。和那个国家陆路接壤的国家,都已成为了危险区。我朝人民军英勇抵抗,暂时守住了国境线,但……眼下形势不容乐观……”
青年一屁股站起来,觉得有些头晕,只好坐下:“我要和父亲谈谈。在最后关头,我们也许需要核……”
随从吓得一哆嗦:“您、您是说……核、核、核……”
青年神秘一笑,同他父亲几乎一模一样的冷酷表情在他脸上一闪即逝。他又用湿巾擦擦脸,才把食指竖在唇边:“嘘。”
“真精彩啊。”你坐在地上,对卫萌冷嘲热讽。“比。特。么。的。春。晚。还。给。力。”
卫萌一语不发,披着你的棉外套坐在角落。
老周坐在另一个墙角,脑袋低垂,像是睡着了。……这些丧尸会睡觉么?
依然很冷,但你现在一点儿都不心疼卫萌。换了是几天之前,你肯定要把全身衣服脱光了连裤衩都给她。李伯文对她做了什么?你瞥了一眼她露在外面的修长小腿,腹部涌动,体内产生了反胃的前兆。
卫萌肯定冻坏了,但你铁了心不分衣服给她。该!你心想。沉默了数个小时,你觉得李伯文限定的时间似乎已经到了,到那时你们都得葬身此地。手表在老周腕子上,老周现在可凶着呢,惹不起,你只能冲卫萌发火。
你偷偷瞄了老周一眼,他倒挺老实,坐着一动不动,脸上有什么奇怪的液体往下滴。你气急败坏,质问卫萌:“你到底想做什么?老周死了,百合也不见了,你还在想什么?李伯文到底是谁?他怎么是你的前男友?你不是……那个谁的老婆?到底是怎么搞的?”
你一阵鞭炮似的把心里的问题和不满挨个儿炸给卫萌听。卫萌不动声色,等你说完,看了老周一眼,缓缓道:“你要听?”
你眼睛一横:“听什么?我才懒得听!”
卫萌莞尔:“那就不说了。”
你语气放缓:“……还是说吧。”
故事很无聊。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疯狂的科学家,娶了自己老师的女儿做妻子。科学家很爱自己的妻子,但她并不爱他。
这件事说来话长,和任何老掉牙的家庭婚恋伦理剧没什么两样,无非是你爱我、我不爱你、我爱他,这样的破四旧结构。总而言之,妻子很善于伪装,装作对科学家十分热情,实际上和科学家的助手发生了不伦之恋。这件事隐瞒了很久。她需要他的聪明才智,再说,她也没理由那么早就离开。她本人也是一位优秀的研究人员,全心全意和科学家一起做某个研究项目。
这个项目是这名科学家主持的。有趣的是,它并非是政府许可的项目,只是挂了一个不相干的题目,伪装成民用项目的实验室,占用了大片的地下空间,实际上进行的是非人道的研究:将活体变死,将死体变活。
他们在研究一种病毒,病毒的样本采集于1942年,在缅甸仰光。
病毒被发现后,通过某种难以言喻的渠道,在某些人的手中辗转流通。起初,负责研究病毒的是七三一秘密部队的某几个生化武器专家。他们将这种病毒命名为Orochi-n。战争结束前,他们疯狂对病毒进行研究,企图将它改造成能够毁灭整个国家的终极武器。幸运的是,Orochi-n病毒尽管有着这样那样坚不可摧的特性,却存在这样一个致命的缺陷:感染病毒后的尸体,在相当短的时间内便会完全死亡,并失去传染性。它们的寿命还不足以支撑活死人大军在大陆上旅行,不足以感染更多的人。
日本战败后,这项研究被下令中止,为了毁灭证据,丧心病狂的七三一专家炸毁了整个地下实验室,将不计其数的感染者和圆木(被他们抓来做活体试验的平民)埋葬在地下深处。
Orochi-n病毒却再度奇迹般地大难不死。又一次地,被某人从战区带回日本本土,继续进行不为人知的研究。
随着以Orochi-n病毒做研究对象的科学家的不断暴死,病毒在研究者之间几易其手。样本的流传十分隐秘,为了保证它不为外界所知,他们不惜制造悬案,杀害自己的亲人。
研究的目的并不相同,研究者各怀鬼胎,无论如何,几经波折后,在20世纪60年代,Orochi-n病毒样本,终于落在这名叫做御手洗须弥的生物学家手中。
御手洗须弥入赘资本世家,在科学界拥有极大的权力。通过家族的协助,他巧妙地掩盖了Orochi-n病毒的存在。
御手洗秘密项目团队,共有四人参与:
御手洗须弥,团队的领导人,遗传学方面的专家。
御手洗明子,须弥的妻子,研究方向是生态学和系统生物学。
石井八重,须弥的老师,明子的母亲,研究方向是现代综合进化论。
五十岚明理,同样是石井老师的学生,是须弥的助手。
Orochi-n病毒发现后的二十年间,研究者发现了病毒的各种特性,但它还很脆弱,产生的行尸极易死亡,在扩大病毒的传播范围和制造抗病毒疫苗方面,几乎没有任何进展。
御手洗须弥接手项目后,研究有了重大突破。在吸纳了欧洲和美国最新的分子生物学研究成果之后,御手洗信心满满,着手改造Orochi-n病毒。
数月后,制造出了病毒的两个改良版本:Orochi-nA和Orochi-nB病毒。这两种变种病毒和病毒原型,能够寄生在哺乳动物体内,潜移默化地改变宿主体细胞的DNA结构。在石井财团的暗中支持下,御手洗须弥尝试了数百种动物的活体实验。
nA和nB病毒代表了两个极端:nA病毒不再使动物变为丧尸,同时能够大幅增加动物肌体衰老、受创后的自愈能力。它是御手洗梦寐以求的灵丹妙药。nB病毒则会大幅改造动物的身体结构,使其成为可怕的怪物。通过大量研究,须弥认为,nB病毒是不可控的,由它产生的怪物的形体、能力都无法预测,nB病毒应当尽早销毁。
御手洗还没有得到最终的结论。一切实验都很圆满,证据确凿,但从未进行过任何一次人类实验。御手洗对团队的控制相当严格,即使是作为助理研究员的妻子和岳母,也无权得到最全面的实验数据。
这时候,在团队内部,发生了一件惊人的事:
御手洗明子、石井八重老师和助手五十岚明理,私自注射了Orochi-nB病毒。
“然后呢?”你问道,“后来怎么样了?他们都变成了丧尸?”
卫萌摇摇头:“nB病毒有很长的一段潜伏期。五个月、五年、五十年……谁也说不准。我们掌握的nB病毒的相关资料还很少。我丈夫好像隐瞒了关键的数据。”
你看看不远处的丧尸老周,不确定他和这个变种病毒有什么联系。
卫萌接着说:“我们背叛了他。换句话说,是他背叛了整个组织。他从一开始起,就背叛了家族……背叛了所有人。”
你表示无法理解。
从上层传来尖利的笑声。上面的人说:“背叛?唱得真动听啊,明子。”
你大惊失色:“他一直在偷听!”
卫萌摆摆手:“我知道。他还有什么事不知道呢?我说的对吗,五十岚君?”
那人的喉咙里发出一连串奇怪的咕咕咯咯声,也不知是在笑还是在哭。他说:“我叫李伯文。”
“我们谁也没想到,你不是日本人。”卫萌说。
“他还是很爱你,”李伯文酸溜溜地说,“最后还是给你注射了nA病毒。逼不得已。你们的奸计得逞了。nA病毒果然能够克制nB病毒吗?他还有多少秘密没有告诉我们?”李伯文吞了一口口水,“你先生的遗愿完成了。可惜他长了一颗护士的脑袋,而不是……战略家。”
卫萌说:“我们都以为你死了。”
“你和你妈妈,一样愚蠢。亲爱的明子。时间已经到了。或者说过了很久。我稍微多睡了一会儿,你和你的小朋友一定不耐烦了。”
你大声质问他:“李伯文,你到底想要什么?丧尸病毒就是你让它们传播的?”你大呼小叫,语无伦次。
李伯文不回答你。
卫萌说:“你知道,这个世界上仅存的nA病毒就在我身上。如果你……”
李伯文淫笑道:“如果有机会,还是想尝尝你的身体啊……别担心,如果你坚持不说的话,我们有的是办法解剖你……”
说着像是威胁一般,从上层传来了可怕的金属声。
李伯文喉咙中发出奇怪的咕嘟声。“谁?!”
声音像是从地面附近的通路传来的。起初还很微小,但数十秒后,已经能够清楚地分辨出,那是有人在蜿蜒虬曲的地下墓道中行走的声音。他们走得并不快,但人数很多,金属通道发出嘈杂的摩擦声。
“谁!是谁!”
李伯文惊慌地问。那声音太遥远了,或许是根本不想回应他。你感到身边有个东西迅速向上层蹿去,不由得身体一紧。李伯文怒气冲冲用日文嘶吼了几句,关掉照明系统,拖着脚步走了,沉重的铁门关闭的声音,将他的脚步声与你们隔开。
你摸着黑找到卫萌,拉拉她的胳膊:“他到底想要什么?nA病毒的……制造方法?”
卫萌没有回答你的问题,而是说:“他瞎了。”
“什么?”
“他体内的nB病毒发作,变成了……怪物。nB病毒最明显的症状:双目失明。”
“……”
“一旦有机会,就杀了他。”卫萌握住你的手,把一只软软的棍状物放在你的手掌中。你吓了一跳。
她的手指。
2月4日
可是将来,你也要像这臭货一样
像这令人恐怖的腐尸
我的眼睛的明星,我的心性的太阳
你、我的激情,我的天使!
是的!优美之女王,你也难以避免
在领过临终圣事之后
当你前去那野草繁花之下长眠
在白骨之间归于腐朽。
那时,我的美人,请你告诉它们
那些吻你吃你的蛆子
旧爱虽已分解,可是,我已保存
爱的形姿和爱的神髓!
--《腐尸》,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
搜索这墓穴。
时间不须太久,因为我们,已时日无多。
在腐败,在凋零。
千千万万个组成部分,终将化作尘土。
新鲜的血液,盼不到及时的补充。
被伟大的造物主创造,这本是值得庆幸的一件事。然而,幸福来得太急太快,我们还来不及分享,就开始腐败、变质,失去作为生物的荣耀。
第一批被感染的已经停止了思考。接下来,第二批、第三批将陆续死亡。得知即将死去的消息是那么突然,那些准备死去的同胞,围坐在广场上,等待天命的降临。
突然的死亡导致了通信的混乱。之前,我们彼此熟记了相邻者的特征,以此源源不绝、用固定的频率相互传递信息。第一批同胞死去后,信息传递的长链中出现了空白,我们不知所措,一瞬间,整个族群的智力甚至回复到了有史以来最差的阶段。世界在我们眼前又变得陌生而复杂,所能看到的万事万物保持不变,但心中却感受不到任何思维的波动。
回忆不能。逻辑不能。判断不能。
所幸这样的空白期并没有持续多久。随着我们漫无目的的游荡,同胞们的间距逐渐恢复到正常的范围内。既不过分远,也不过分近;保证了信息传输的效率,同时不至于干扰到彼此的通信。
新死者带走了一部分有效的记忆和经验,使得一切思考几乎都要从头开始,这是最严重的损失。
我是谁?我们是谁?
我不懂。
可是除了我自己之外,还有谁懂?
重新花了很长时间去认识自己,而那些关于前世的记忆,已经无法完整的重现。感觉上像是被感染之前,有一份正当的职业,每天做着同样的事情。这么说来,似乎活着和死了,不存在什么区别。生和死的界线,究竟在哪里呢?
看着眼前的同伴一批有一批的死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尸体。我们还不是尸体,只因为还留有相当勉强的思考能力。
某种使命感压迫着我们,让我们持续前进,但是,谁也说不明白,究竟在何方,有什么样的终极,在等待我们。
消息还在传来,却变得很难让人理解。上千名同伴终于深入南方的墓穴深处,但和我们失去了联系。最后一条传来的信息显示,他们还在缓慢而有节奏地向着地下深处进发。为什么在地下?我们想不起进入地下的理由了。这样做总有个原因,但由于无法回忆,我们始终不能放心。
土壤、砖石和墓道结构隔绝了通信。他们在向下走。走了多远?为什么有猫?猫杀死了我们的同伴吗?两千公里外传来的,是新年的鞭炮声,还是真正的枪声?这个国家还存在吗?还有从感染者大军中逃出的幸存者吗?他们恐惧吗?他们好吃吗?
纷乱无章的念头填满了我们可怜的大脑。我们根本无法同时处理如此多的信息和虚构。自从聚集在一起之后,虚构出来的东西占据了我们绝大部分的思维。这些东西是虚假的、无用的、有害的,只关乎艺术和想象的,它们是族群的毒药。
尽管如此,谣言和讽刺还在疯狂传播,从这颗大脑到下一颗大脑,没人摆脱得了。独特的交流机制让我们无法隐瞒内心的真实想法。内心无需隐瞒,每个同胞只有最简单的几种想法。想法汇聚成了思想的洪流,这种洪流不可阻挡。
随着同伴的死亡,群体的忧虑加重了。开始产生了反对的意见,同伴和同伴之间并且发生了斗争。信息的交流被打断,取而代之的是一连串无意义的表示发怒和惶恐的信号。随着我们之间相对位置的改变,发怒的交互被切断,混乱暂时被掩盖,而更大的危机笼罩在我们每个同胞的心头:
所有同胞都在死亡。
或缓慢、或飞快,每个人身上都在发生不可思议的变化。
旧的细胞被替代,新的细胞失去活力。组织崩毁,骨骼坍塌,蛆虫在我们体内驻留,蚕食剩下的肉体。
我们缺乏能量。
吃光了陆上一切肉类,仍旧感到饥肠辘辘。
为了降低损耗,所有同伴都躺在地上,停止运动。尽管如此,交流从未停止。这块大陆是我们的家。在这个国家之外,在东方,在西方,在南方,在北方,更多的新人加入了我们的组织,进入了伟大的共同体,成为神圣的一员,开始和我们共享唯一的意识。
他们还很远。每一条消息都要经过无数次的转发和改编,发送人和接收人之间横亘着数千公里和数亿同胞,悠远的旅程掩盖了信息的本来面目。
那些新同伴……
临近死亡的恐惧。他们暂时,还不会明白。
卫萌向你充分解释了它的用法。
表面上像是人类的手指,实际上只是仿真度极高的义肢。表面以某种摸起来像极了人类皮肤的材质制成,连内部肌肉的纹理都栩栩如生。骨骼系统则是一套精密的电子设备,你完全搞不懂这东西能有什么用。
“来,试试。”卫萌示意你伸出手来。
你连连摆手:“这么……这么科幻的东西,还是算了吧。”
卫萌突然用它在你胳膊上戳了一下。
尽管隔着厚厚的衣服,你还是猛地哆嗦了一下。电……是电流吗?
你想起之前也被卫萌电过。那时你们在警察的车里,癫狂的警察的脑袋里好像有两个人在打架。那次你无心碰了一下卫萌,却被电流猛地电到,你记得那次的强度比现在高得多,要不是你小子体质强健,没准儿要给她电昏过去。
那时候她为什么要用电……难道是想杀了那警察不成?
你疑虑重重看着卫萌。卫萌把指头递给你,你半晌不敢接。
“这是最后的能量了,”卫萌把它塞在你手里,拍拍你的手背。“我想,与其用来打一次未必能接通的卫星电话,不如给你……”
你瞪大眼睛看着指头,生怕里面有什么妖魔跑出来。“你……你怎么不用?”
卫萌撩起披在身上的棉外套,在黑暗中,露出你看不见的雪白的胴体,温柔地拉起你的手。
我到达坟地。
坟地的中央有一座大型的坟墓建筑,墓碑上写着看不懂的文字。
到现在为止,每一步都很正确。
这里有我们想要的……食物。
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食物。更加强大,更加难以控制。
陆续传来的零零碎碎的消息证明了这一点。
坟墓中关着一只怪物,我们老远就能嗅到它的味道。和我们有着类似的气息,然而它的身体,并没有发生腐烂。
最终的决议是这样的:捕获它,无论用什么方法都要捕获它。在它身上有着至关重要的信息,让我们免于一死的最后秘密。这个家伙在地下隐藏了那么久,却一直奇迹般地活着。我们要他。一定要。
其他四个人类被列为了次要目标。如果能感染他们,也许可以得到同样重要的情报。他们在哪呢?
地下道路错综复杂,传来的断断续续的消息完全打乱了进攻的节奏。找不到自己的同胞,只能在黑暗深处乱闯。我们确认先头部队已经和那个家伙发生了冲突,因为发现了好几处堆积着的同胞的遗体,他们大都被利器割断了脖子,有些则被敲碎了脑壳,还有些则被撕成了碎块。那东西很顽强。在伸手不见指头的巷道中和它进行无声的交战,也许已经弄伤了对方,但丝毫没有被感染的迹象。
我们欢欣鼓舞。自这个族群诞生以来,从来没有这样的情况:被挠伤的哺乳动物没有被病毒感染。从来没有过。
毫无疑问,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要找的。它体内的物质,是终极力量的源泉。我们用了很长的时间去思考。那怪物和我们接触之后,我们的同胞同样没有被它感染,就像我们的病毒没能感染它一样。这就是说,它不具备传染性。那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这样小的缺点被我们快乐地接纳了。在它的家里,在地下深处,一定藏着使人变成那种东西的病毒。它能活很长时间,能做无数我们渴望的事情。在我们纷纷凋零之前,还有……还有不知道多少天可以用来挥霍。
足够了。
战术进行了调整,为了活捉那东西,牺牲在所难免。不断地将同胞送入墓穴,就连我自己也得到许可,深入黑暗之中。
在墓道中,声音的传递变得很困难。某种看不见听不到的系统干扰了我们之间的交流。失误频繁发生,那东西始终在逃跑。我们相信,它逃不掉的。
在一条死路的尽头终于堵住了怪物。据最前线的同胞描述,看不清它的样子,但显然很强大,符合我们所有人的心愿。怀着感激又喜悦的情绪,我们向它涌去,这时却得到了从另外一个方向传来的信息:在坑道的另一边,同样发现了它。
那么,到底有几只它呢?
“你不要死!”
你抓住她的肩,用最严厉的语气命令她。
卫萌握住你的手:“对不起。骗了你这么多。”
你痛哭流涕:“到底是为什么……”
卫萌脸上露出一种难以察觉的喜悦。你看不见她的脸,但你知道……她在笑。她的笑美极了。可是她要死了。你们彼此从没这么接近过,现在你连她的脸都看不见。
你擦掉泪水:“别留我一个人在这……”
卫萌低声说:“她一直在说,人类都是……暴虐的破坏者。不过,我觉得……你这人也挺好的。谢谢你。”
“我……”你泣不成声。
卫萌说:“我的使命终于结束了。有时候我也在想,生命如此短暂,为什么不做些更有趣的事。”
声音微弱,逐渐变成了几乎无声的呢喃。
“她就要来了。”卫萌说,“……你还有机会。杀了李伯文,用这个……”她用力按了按你握着人工手指的手,“用这个向她发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