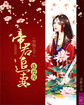喧沸依然在,人群恍然未觉,数百上千里外的高空,接天连山,凡俗血肉之躯即便真的有心,也未必能察觉出异样来。
只是慕尚六人在云爵的愕然间站起了身子,从顶棚下走到了顶棚外缘,一字排开而站,举目而望。
广场上,人群里的老幼大概这会儿回去小作休憩了,留下些青壮男女,几群少年少女。
整个镇加上外来游民,总共约摸一千五百来人口,此时除去老幼,一千人左右正拥闹在广场上。
慕尚负手而立,沉静的面容上古井无波,向来宁静如水的眼神中一丝丝起伏才显露出此时内心的不平静,典庄赵顷五人站在一边,面色深沉。
许若彤乖巧立于慕尚身后侧,没有丝毫惊讶,姣好的俏脸上温婉如水,眼神明亮,随着慕尚几人的视线望去。
云爵悄悄推醒了陷入睡梦的夜修,“嗯......?嗯...”眼帘沉重,夜修揉了揉眼睛,有些迷蒙地看向云爵。
竖起食指,云爵朝着远方大山与天际交界处戳了戳,那片与青天辉映的云霞随着距离的靠近,越发明亮绚丽。云爵不动声色,眼神中多出了几分惊兀,几分期待。
夜修一个激灵,用力搓了搓眼睛,好让自己快速清醒过来,手支着桌子利索地站起,两步便窜到了慕尚等人身后,云爵起身跟上,挨着夜修站定。
许仁几人倒还未有所觉,还以为慕叔他们和两个半大的少年见着了什么有趣的东西,也不在意,瞧了两眼便继续闲聊。
如崖上松柏般立着,慕尚观而不语,灰白色的长衣下摆在膝盖处轻轻摇曳,眼神凝澈,一两息之后,无须白面上嘴唇轻启,淡淡道:“神阁来人。”
开口声云淡风轻,落音之后却是平地起惊雷!云爵夜修在内心茫然不解的同时,猛然感觉到一股强烈到让人心悸的灵力在身周涌起。
甚至不用感知,云爵便能清楚地知悉灵力的涌动来自何处,心生感慨,自己果然修为浅薄,看走了眼。
灵力的涌动只是一瞬,这一瞬对于云爵夜修二人来说,却仿佛在云巅之上被来回抛落下了数次,来自于灵魂的震颤。
而后平静,两人背后湿汗微冒。夜修清亮的星目中微有些悸意,俊秀的脸蛋上再没了随意嬉皮之色。云爵暗咬着牙关,看似毫无反应,默不作声,然而俊邪眸子里闪动着坚挺,维持着面上的平和。
灵力的源头是身边的众位大叔,云爵先前以为凡人身份甚至以灵力目测过的六位朝夕相处了一年的大叔们。
始终抱臂胸前的顾北本就无感的瘦削面容愈发冷硬,胸前环着的双臂抱得更紧了几分,眼中木讷之色渐被凌厉代替,生冷地抬着视线,笔直而望。整个人在棕褐色的紧身皮衣包裹下如一柄寒光浴铁的利刃,待时而动。额角紧束的发髻中荡下了一缕银白的鬓发,无声凛然。
“哼!一群狗东西。”站在负手不语的慕尚左身侧的典庄率先骂出了声,伴着赵顷一声冷笑,而后摇扇声。魁梧的身形更显直挺,典庄毫不掩饰内心的怒意。环形虎目之中怒火雄雄,本就横肉堆挤的一张糙脸上凶狠更甚,宽肩阔背无形中竟显得膨胀了几分,灵力在身体内外翻涌,浓眉团簇,咬牙切齿,怒目圆睁。
赵顷颇有些书生气的儒生冠面上那较之夜修更显风流的悠哉之意早已收起,不宽不狭的一双长眼里泛着荧荧的暗冷色,嘴角冷冷地勾起了一抹弧度,左手随意却又笔直地垂在身侧,手掌后翻,山水墨扇在右手中摇得更缓更轻,韵律骤生,不复平息。
即便温厚如张起,沉稳如刘安,这时也不难看出二人凝重神色中包含的怒态,刘安着了一身算房先生般的青白色长褂,双手插在袖管里捧在腹前,本有些中年晚态的佝偻畏寒身形挺立了起来,眯着眼睛深沉凝望。
一袭鎏金边白裙的许若彤立在慕尚身后侧,清婉的眼里明净澄澈,琼鼻微挺轻轻嗅了嗅,柳叶般细长的眉皱了皱,显然发现了几位叔叔毫不掩饰的怒态,对于乘云而来的“仙人”没了先前的好奇,爱屋及乌以致厌屋及乌一般产生了不喜,白嫩的手指在身侧卷了卷鎏金裙边。
至于云爵夜修,那股带来窒息般压迫感的灵力波动来得快去得也快。此时感受到的不是灵力喷涌带来的心悸,而是如置身于汪洋大海中的浓稠感,凝厚无匹,身如飘舟,沉浮无依。
灵力猛击心神的压迫感消散无形,转化为浸润四周空间的包绕感。
云爵夜修二人自然也不再那么悸动不安,甚至需要以自身识念精神对抗无心而起的灵力外散。
然而,伴随着压迫感的减轻,二人却没能感受到丝毫的闲适。反而,那股大雨欲来风满楼的飘摇与凝重氛围更甚。
云爵黑亮的眸子本就天生蕴养了一股俊邪气,眼波流转间眉头微蹙自成一种风情,视线侧移,想要从六位大叔脸上眼里看出些什么,终究一无所获,除了冷淡便还只剩宁静,微眯的依然微眯,圆睁的此时也收起了不少肉眼可观的怒色,仿若之前的一切所感所知都为泡影,不见声色。
云爵心知绝非如此,但也按捺住心绪和神情,故我地举目远眺,以作少年好奇之状。
身旁有些僵硬的夜修,这时总算从悸动中缓过劲来,合上了灵力喷涌压迫心神前微张的嘴,略显抽搐,揉了揉嘴角,犹有余悸地瞄了瞄六道熟悉又陌生的背影,缩了缩脑袋,视线乖俏异于寻常地望向远天那片越来越近的云霞,黑亮星目中神采奕奕,微昂着脑袋,刚闭上的嘴唇又有了张开的趋势。
“也没听老头说过外面的修士排场这么的大啊。”夜修实则内心腹诽。
云白不曾与之讲过修士如何粉墨登场,夜修也同样不知修士本身便已如何超然凡俗。
不知不畏,不闻无往,因而洒然。
左手边是夜修,云爵右侧隔了一人距离盈盈立着许若彤,这一刻众人皆都沉默不语,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妥当,仿佛这样的反应才是理所应当。
与此同时,不算开阔但也绝不显拥挤的广场另外几处角落也有人自座位缓缓起身。其中自然包括了青年司南三人,这时司南微眯着眼,脸上的云淡风轻之色稍隐。云爵招待过的中年男人和那粉嫩漂亮的少年也赫然在列,中年男人今天依然穿了那件玄色绸衣,面色深凝,眉目之中凌厉之气不怒自威。
而那粉嫩如玉雕琢的秀美少年,今天着了件粉紫色的大衣,包裹得如瓷雕里的小人娃娃,煞是可爱,这时手里托着半块冰梅饼,腮帮子鼓动不停,显然在大快朵颐,乌油油的弯月眼里闪烁着纯澈而明亮的光芒,那只闲着的白净小手牵着中年男子的衣袖,时不时砸吧小嘴,平平静静安然自得。
东北角挨着那座皮影戏台瘫坐着的老乞丐支着手里那根枯黄半人高的竹棒,颤巍巍站起了身子,那身东家西家拼拼凑凑送的大棉袄子被一双褶皱的黑皮老手拽了拽,像是在裹紧些以保温暖,头上还戴着一只开了天窗的棉絮帽子。
老乞丐先前一直坐在那儿,镇上有与之相熟,平常玩闹一块的热心少年刚给他送去了一只瓷碗,新制的,显然是少年瞒着家里人从碗橱里偷拿了出来,顺手还带了只碟子,瓷碗装酒,碟子得摆上吃食。
老乞丐喝得惬意吃得很舒坦,美滋滋边饮边吃边听戏,越听越得意,越听越不想起身。其实在这里瘫坐上百年,也未必不是件自在事。管甚么的仙途大道,长生不死?
唉,可惜......
老乞丐常年歪着的膝盖悄悄直了,混浊却并不浑噩的苍黄老眼里闪过了复杂之色,说不上的留恋,谈不及的不舍,可偏偏着实有些不情愿,不过似乎天不遂人愿?
抬头眯眼瞅了瞅高远不知几许的白云青天,极符合身份形象的一口老痰便从嘴里打在了地上,哼哼唧唧地唱起小曲,那首杏花谣。一瘸一拐便走到了皮影戏台那片区域的西边边缘,向西而立。
身后是一群正津津入味目不转睛的少年,那个刚给他倒满酒的小家伙就在里面啊,这小子的眼里可是亮得很呢,比之自己那会儿,犹有过之。
可惜了,又是可惜。
老乞丐撑着竹竿,抿着干薄缩揪的一张嘴,好整以暇地眯眼打量那片接天连山的七彩云霞,美也美,只是略假。不,太假!
广场南边入口处是一块葫芦口形状的空地,连接着留仙镇南北向的主街道,入口空地的路边常年摆着一间小酒肆,面朝东向着主街开着,整座酒肆都是由许多不规整的破旧木板和几根插入地的椽木拼凑而成。
酒肆右边紧挨着那几根入地的椽木插着一面旗,那面已找不到丝毫白净面目的白旗上歪歪扭扭涂着个大红的酒字,旗杆乌黑,不知名的材料,似金非金似木非木。
酒肆里只有一个跑腿的伙计,也不知有无老板,来这里喝些糟粕酒糠的酒客醉鬼们只管点上几刀子,两碟花生米,最多再加上二两野兔肉,吃干抹净了丢上六七枚铜板便也走了,极少有人找那孤零零一个人的伙计说上几句话,甚至有人觉得这不知年纪的匀称汉子是个哑巴。
但事实不是,曾经也有个外来户,带了些行礼银两,约摸是路上遇见了什么不顺畅的事,进了镇子见着这家破烂酒肆坐下便喝,直至喝到酩酊不醒,烂醉如泥。这家伙计才扶着他落脚了张东家那间云游客栈,期间与张姓东家交流了两句,大概便是“不知此人是谁从哪里来,在我那里喝醉了,我搀了过来”之类,才打消了小镇上人们的猜测。
这种年会时节,显然不会有酒鬼花那二三文的金贵铜板来这里喝两碗烧刀子,伙计倒也落得清闲,穿着那身洗得泛白的小二棉服,头戴高翘的围帽,端坐在最靠围栏北边的桌椅上,小翘着二郎腿,朝着那片欢悦的人群。
伙计相貌普通,年岁看着也不大,大二十的模样,可能三十几也或许差那么一两岁便到了三十,身材中等而匀称。
唯一出奇的地方,是那白皙得胜白雪赛阳春的肌肤,从脸到手,无一不是。如果不是这身伙计服,不是这样一间酒肆。
他或许可能是个书生。
阳春白雪说的是琵琶曲?不知怎的,这会儿笑嘻嘻的伙计嘴角露出了一丝讥诮之色,黑深的眼神由于白皙过分的肌肤的映衬,显得愈加幽远。
二郎腿轻轻抖动,白而细长的手指缓扣着桌面,歪着脑袋低了低头,目光正好挨着酒肆顶棚那块破木板瞧见了那片云彩,讥诮之色更浓,眼神更淡漠。
在这时候,广场上人流如注,醉仙居门口却是门可罗雀,稀疏来往的几个行人要么是往广场去,要么是从广场上回来。
惟有一人,自南门入镇,无人察觉,漫步街上,随性自由。
深冬时节,南门外的稻田无需打理,大雪必定瑞了场丰年,河流冰结,大山沉睡,镇上人们也早已准备了充足的过冬食物,南门自然少有人来往。
这人是个身材高挺的男子,衣饰单薄,白灰色的贴身内衣外敞开着一件麻布大衣,一眼看去叫人心生萧寒。偏偏生相风流,满头灰发披散至肩,只用了支横木微微收束着。然而面容却是白亮纯澈得如同女子,一走一停自带了安然与闲适,面色似是温婉喜笑,双目明净,眼中含着说不尽的绵柔,两鬓垂髫,步态翩翩。
先是背负着双手驻足南门外被积雪覆盖了的青石桥上,抬头注目那“留仙镇”牌匾良久,男子眼里浓郁的沧桑感如数十里外被云雾缭绕的深山,让人心生彷徨,如舟行水,放逐江流。远观远感之,男子如年登古稀的老人一般历经世事浮沉,心绪再无波澜。
注目过后,复杂之色在清亮的眼中闪烁,随着鼻息而出似有一声回挽的叹息萦绕。这男子终于抬足,身子过了那道镇门,眼中沧桑才渐渐如云尽雾敛般消隐不见。
不知年岁似老似少的男子一脚踩在了入镇门之后那块连着主街青石板的坚实硬泥地上,嘴角勾起了一抹笑意。这时候又好像是个贪恋了家门外趣味风光的稚子,误了归家的时辰,一路踩着细碎的夕阳回来,心怀着不知名的惴惴和欢快。
一只手仍然背在身后,而另一只则极随意地应和着轻快的步调在身周轻摇。
当日云爵夜修自孤峰而下直入留仙镇,迈入镇门后入目的第一件事物便是一棵离镇门三四步远的老槐树,得有两个半的夜修合抱那么粗,盘根交错,扎根在镇门口那片黄泥地里,根须如一条条入土即隐的地龙,绕着主根不知通向地底哪里,在这座小镇上称得上一奇。
当时夜修还啧啧称奇过那么一会儿,后来也只把它当做了寻常老树忘在了脑后。
那会儿正值春季,老槐树枝叶繁茂,杂生的枝杈都快垂到了地面上,一丛丛一捧捧的鲜嫩槐叶流淌出说不尽的葱茏盎然。
这会儿被冬雪拍打得只剩下了一身枯老树皮,叶子早已脱落埋在了雪里默默溃烂而后经过泥土回归老槐的主体化作养料。主干还算厚实老重,而那些歪歪扭扭向外伸展的别枝分丫却有些营养不良饱受风雪摧残的意味,低垂着细弱的躯体,枝皮干裂,断的断折的折,也快垂到了地上。整棵老槐形同一个缩水的胖子,瘪小了几分。
这棵老槐事实上也真是棵再普通不过的寻常老树了,当年或许也是外边山林里的一株幼苗,不知怎地就被移栽到了这里,孤零零地独自经受与同伴们无异的风吹日晒雨淋,走过了无数年头,也终于成了一位老人,垂垂老矣。
大雪会把很多东西掩埋起来,比如挨着南门根的那口枯井,这个时候早已找不到那处黑不隆冬,不闻水声的井口,虽然只隔了一堵低矮爬满藤蔓花草的泥墙便与那条环绕小镇的大河为邻,但井里偏偏就是没水。镇上人们虽说感到怪异,然而这座井放在这里本也用途不大,不用跨出镇门就能从大河里打上纯净清冽的大山深处流出的泉水,便也任由这口枯井荒着了。
隐藏了这些已为人知却不在人心的东西,大雪也曝露出一些不为人知随岁月流失的记忆,比如这时才摇了两三步路恰好立在老槐之下的麻衣男子,怔怔望着老槐主干上失去浓密树叶遮掩之后显露出的那幅模糊的图画,显然是不知何时的顽童刻印所留,历经久远。
老槐还得向北七八米远处才开始稀疏有人家,才见灯火。这片还黏连着残雪的黄泥地上再无他物,除了东南角更荒僻处临着墙根被雪掩埋井口的那口枯井之外,方寸天地间只剩下了男子一人,茕茕孑立直面老槐,或者说是那幅原形难辨的刻画。
不远处灯火离离,那一排排高低宽窄的青瓦白墙交叉错落间人影迷迷,雪化水在叮咚,日照远辰生旧景,旧景依稀。
多少年前了......记不得了记不得了......
男子怅然而笑,神色难辨,似喜似悲,那副如女子般的柔美模样已没了温婉神态,孤寂凛冽,眼神凄然,步子早已停了下来,一手托着另一手的手腕背在身后,身子昂挺,然而气态却萧索。
一声叹息,男子曲颈,麻布大衣蓬松地在肩上隆起,脚上那双灰色的棉布鞋底在老槐树下的小雪垛上轻轻摩擦。
“既然斯人已去无人可忆,那也无需再留记了吧。”男子视线垂落盯着被鞋底摩擦得越来越平滑的雪垛,低声喃喃,这呓语只有老槐才能听到,歪扭的一根粗壮旁枝上跌落了一块残雪,贴着略显宽松的麻衣打在了男子身后。
男子抬起了头,怔怔与怅然之色就如脚下那块凸起雪垛一般,被鞋底磨搓平了,消失不见,仿若未曾有,便也未曾失。
温婉的淡淡笑意重回脸上,比女子还显细腻的白净面色此时比雪还显宁静。
这种笑意可以浸染到嘴角,发鬓,眸子里。
于是嘴角被时光勾勒出安宁写意的流线,银灰的鬓发闪烁出那千里之外翻山越岭而来的山泉水在光照下泛起的鱼鳞光泽,深黑好比无星夜幕的眸子里布满了看破放下的洒意。
“走喽。”男子朝老槐和老槐树上的刻画随意笑了笑,像是告别,也像是叮嘱。
弯腰倒走了两步,避开了低垂的枝杈,转身趋步。男子背着双手,笑意雍容地任由敞开的麻布大衣翻向身后两侧,背朝老槐向北而行,三五步后终于踏上了那条青石板主街。
那副模糊的刻画,刻着不知名的人事物,随着男子愈行愈远也终于走完了自刻画完成到最终消失的一生,从老槐上脱落,木屑坠地后与潮湿的黄泥土混在了一块儿。
青石板两边开始由南向北延伸出由低到高的许多户人家,南端较低矮的青砖黛瓦里住的都是些上了年纪的老人,腿脚不便离水源不宜过远,留仙镇上人们便一致商议决定镇南一片给老人们居住,一来老人们聚在一块儿能做伴不至于乏闷,二来离水源南门也近些,方便老人们采水。
晌午将过,年老力衰比不得青壮年精力旺盛的老人们也已从北边广场上相互搀扶着回了屋,这时候炊烟都随风散去了,灶肚里的未烬薪柴火星已冷灭。吃过饭,老人们按照日常作息上床午歇,门户稍掩,一派祥和静谧。
男子独步街上,青石板主街的两边边缘,离各家门户还有点空当的地上不规则地还留着些残雪,兴许是老人们清扫堆积所致,在远阳的温热下还未化尽。
男子颇有兴致地东瞧西看,目带思忆,流淌出温暖。
“这家以前二麻子住过,如今也不知哪家的儿子孙子辈在这里落了脚,嘿,臭小子到死也不知娶没娶妻,生个一儿半女的。咦......这家不是那蛮婆娘占着的嘛?如今倒是住了个温顺媳妇,呵呵~”男子边笑着边摇头,心里一一对比今夕,物是人非,人间难寻不变景。
洒逸一笑,灰发男子收敛了左右游走的视线,嘴角含着笑意向前趋步,身躯自然挺直,如云随风,如星追月般踩步。
至于那一排排青砖黛瓦的小屋,又或者朱漆门户的庭院里,人影摇曳,细声呓语,各自安稳于各自的世界里,吃饭喝水坐立休憩,别样的情意别样的流景。屋里不知门外何人看,门外亦不晓究竟看屋里何人。
往北,街边的木制摊位这时候被规整地收拾摆在青石街两边,拉上了红布帘盖。紧挨路边的两排房屋已不再是独门独户的民居,一家家商铺连在一块儿,店铺之后排列着亭亭院院,里面住着留仙镇上的青壮。
醉仙居已然在望,灰发男子停下了脚步,原地站定,背负双手,外翻的麻布大衣隐隐鼓动,笑意更浓,狭长眸子微眯,一股淡淡的眷情可感地流露在脸上,久游之子今归家。
似有应和,冬日光芒映射在醉仙居的阁楼上,红蓝瓷瓦反照,流光溢彩颇为绚烂。
小镇长街青石板,一人独立未凭栏。
群山高绕,小镇微渺。街上的男子这时却好像凌立青云,气势轩昂。
再两步,鬼魅般跨过了百米远,男子气定神闲地站在了醉仙居的门匾下,颇显雍容地卷了卷麻衣袖边,轻轻呵气。再抬眼时,人已随影散,残雪与水渍里留下了两片脚印,述说原委。
在男子入镇,过老槐,踏青石,而后诡异消隐在醉仙居门口的片刻功夫里,北门广场上人群欢腾依旧,各种花样戏法层出不穷,不见丝毫褪却热情的迹象。
酒肆里的那个白肤小二依然颇有节律地抖动着二郎腿,修长的手指在桌上打着拍。老乞丐端着酒碗站在皮影戏台边慢慢喝着,中间那少年从看台下跑出来又给老乞丐加了酒,老乞丐有些心疼这酒能不能喝完,以至于蓬乱的浓密胡子上都沾上了酒渍。
威严端正的中年男子一只大手拉着那正对各种精美小吃自顾不暇的美嫩少年,另一手握拳背在身后,脸色越发无感。
期间那瓷娃娃般灵秀的少年试图把小手从叔叔大手中抽出来,一只手实在吃得太慢了,来不及啊来不及,然而被中年男子毫无余地地制止,少年哀怨地翻了个白眼,腮帮不停。
槿辰思尔一左一右立于青年司南身后,少年脸上流露出难掩的紧张和炙热的期待,即便淡泊如槿辰这般,此时也是唇瓣轻咬,不难看出内心的起伏情绪。
至于那青年司南,闲散笑意早已不知收敛到了何处,细长凤目中凝色忽隐忽现,双臂垂落,身形挺直。
那片灵力汇聚而成的云霞光团已越过了西边群山之中最高的那座峰头,在云爵众人的瞳孔中越来越大,先前还只是一片,此时虽然尚且隔着相当远的一段距离,但已然能凭肉眼望出异常,有灵力的光泽四溢,看着祥瑞无匹。
慕尚典庄等人昂首而立巍峨不动,立于顶棚之下,排在外围一排,这时候许仁六人也终于发觉了慕叔几人的异样,离开了座位,站在了云爵夜修三人身边,睁着肉眼顺道望去,隐约瞧见了那片正缓速而来的霞云,虽不失温文之态,但也惊诧非常,低声私语。
“那是什么?!”人群中不知从哪里传出一声爆喝,是个中气十足的青壮汉子,接着便是一片骚动,北边广场上此时还剩下的留仙镇主要少青壮们在不大的广场四处各个角落抬起了目光,汇在一处,那片瞧不真切的灵力霞云之上。
有惊愕得张大了嘴巴忘记合上的,有身形瑟瑟发抖不知所措的,有畏惧也有兴奋的,畏惧的多是些已立家室的壮年人,兴奋的自然是那群乳毛尚未退却的青少年郎。
妇们或牵或抱着自家的稚儿,站在靠后的广场东边,有些还在怀里嗷嗷待哺的童子被这突如其来的凝重氛围惊得哇的一声哭出了声来。
广场上顿时肃静一片,鸦雀无声,云霞越飘越近,毫无曲绕地直朝留仙镇而来。
越来越近,越发光彩夺目,凭肉眼隐约已能看出那上面竟立着一群人!
广场上的镇民在猛地一阵寂静之后,开始窃窃私语起来,淳朴心性俱认为是仙人下凡而来赐降祥瑞,便要跪拜。这时,一声宏音遥遥传来,威严无比,响彻附近山林,直达留仙镇,如仙人口谕。
“吾等,天渊门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