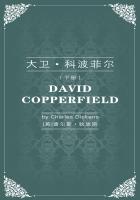我们来到一处古旧的建筑前,那门边立着一块“省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这就是“飞将军祠”。张校长告诉我们,后来在修整时发现,正殿大梁的背面刻有“仁寿元年,岁在辛酉,八月望日,上梁大吉”的字样。“仁寿”是隋文帝杨坚的第二个年号,仁寿元年是公元六百零一年,距今已经一千三百余年,这样的古建筑现在全世界也非常少有了。李家沟里还有着这样珍贵的古迹,真不愧是中华民族的发祥之地!因为没有找到管理人员,我们没能进去参观和瞻仰。我很想进去看一看李江玉老师当年居住的地方,但是张校长说,那些偏屋早已拆除了。我们只能望着那巍峨的门楼兴叹。这时我忽然想起,这是一个会让张校长触景生情的地方,还是不进去的好。
张校长特意带我们向下村边上的一堵土墙走去。在四周新建的楼房环绕中,这堵土墙显得很是特殊。它周围是一片青草地,一圈铁栏杆护卫着它。走到跟前,不需她做解说,我们马上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土墙是加固过的,但还尽力保存原来的风貌。那上面至今依旧赫然显现着一行大字:“将革命进行到底!”当年王良先生一到李家沟就见到这条解放军写下的标语,今天我们又见到它。张校长说,她的学校每年新生入学都要到这里来,听李山梁爷爷讲解放战争的故事。县城里,甚至省城里的青年人入党入团,都喜欢到这里来宣誓。这也是李家沟值得骄傲的一处文物。
伫立这堵土墙前,身在青山绿水的李家沟中,想起这块土地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我感到,我们伟大祖国的翻天覆地的革命事业,的确是在克服一切的困难和曲折坚持不懈地向前进,而且必定能够进行到底!
这天晚上,我们在张校长的书房里谈起这堵土墙,不觉又谈起李家沟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抚今追昔,感慨万端。感慨之余,我不禁又幻想起来。我说:
“李家沟有这样悠久的历史传统和革命传统,有这样珍贵的文物古迹,现在又发现巨大的金矿,风景还这样优美,真应该再大大地发展一下!”
张校长说:“我们是有一个很好的远景发展计划,不过还需要一些资金。”想不到小王马上说:
“我回来以前,有几个很有些财力的美国朋友托我为他们寻找在中国大陆投资的方向。我马上给他们写信,请他们来这里。像李家沟这样的条件,他们会有钱可赚,我们也利用他们的资金来发展我们的事业。我要陪他们一起来具体落实。”
临行这天的上午,我和小王专程去张家洼向李秀秀致谢和告别。回到张秋眉校长家里,她为我们设酒送行。
她把餐桌设在她的卧室里,意思是让我们更多地了解她的生活。我没有注意她房间里的彩电冰箱,却一眼看见了她床头的一把红麻线扎花的高粱穗子炕笤帚。我马上指给小王看。他告诉我和张校长,他爸爸的那只在奔波流离中丢失了,爸爸为此多次慨叹过。小王说:“要不我们这次也就带来了。”
张校长请来了李七姑。我们四人围坐在卧室里的一张小方台边。我们好像是四个亲人。我们确实是四个亲人。
下午二时的火车,张秋眉校长已经安排好学校的车子送我们去牛庄。我们再说到几件必须说到的事:关于墓碑,张校长说这由她一手经办,小王写下了父亲的生卒年月,以便刻在碑上。这时,张校长从她的抽屉里拿出一页纸来,稍稍迟疑了一下才对小王说:
“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想把这几句话刻在墓碑的背后。是我昨天晚上写的。”她把那张纸递过来。是这些诗句:
昔日有过客,来去何匆匆,身在黄土沟,心在紫微宫。而今永归来,眠此东山东,俯饮乳汁水,仰依慈母峰。一轮皎皎月,伴君挂晴空,与君长相守,灵犀隔世通。青山绿水情,融融我心中,请看妹子沟,今朝沐春风。
见我们两人把她的诗读过一遍又一遍,不肯释手,张校长不好意思起来。她说:“我写得不好。不过你们知道,这是他和李江玉老师兴下的规矩,所以我就学着大胆地写了。”小王和我都十分喜欢她的诗。小王说,这是他所读过的让他最受感动的一首诗。张秋眉校长欣慰地笑了。这时,小王从提包中取出一个厚厚的信封来,态度诚恳地放在桌上。他说,这是一笔钱,他想留下,供张校长和李七姑两位阿姨不时之需,他是代表他父亲这样做的。但是她们二人都坚决不肯接受。她们说,现在她们生活得很好,而且一天会比一天更好,不需要这钱。再三推让以后,张秋眉校长终于望一望李七姑,好像是在取得她的同意,然后对我们说,她建议,用这笔钱在她的学校里设一份奖学金,用来培养李家沟的下一代。小王和我都赞赏这个主意。大家一致主张把这称作“李江玉先生纪念奖学金”。并且一致决定,请李山梁担任奖学金的管理人。
回程的火车上,我和小王在这样交谈:“老师,请恕我直言。你们这一代,你、爸爸和张秋眉阿姨这一代,我指的是中国的一代知识分子,你们吃过多少苦头啊。你们是辛苦的一代,勤劳的一代,奉献的一代,但是我想说,你们也是到老、到死都不够成熟的一代。你们单纯得可爱,你们是理想主义的过渡的一代。不过,这或许正是历史给你们安排的位置吧。”
我对小王突如其来的这番议论缺少应对的准备,所以只听,没有答话。小王却并不在意。他继续说下去:
“我觉得你们这一代人常常在矛盾和苦恼当中求生存,你们活得太累了。也正是因为这样,你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至今都未免太传统了,太闭塞了,不大切合当前的实际。”
在小王稍稍停顿的时候,我忍不住地说:“但是你不觉得你们这一代人,在很多情况下,为自己考虑得太多吗?比如说你当年挥手而去的时候?”小王立刻不假思索地回答我:
“是的,我当年是挥手而去了。但是我现在不是回来了吗?而你不能否认,正是因为我爸爸的过于单纯,才造成了他自己和别人的终生遗憾。我觉得你和他的许许多多同代人,直到现在,做的和想的还都跟我的爸爸一个样。”
我不能说小王说得不对,但是我也不能完全同意他,尤其不能完全同意他对我们这一代人的笼统的评价。我正在考虑如何回答,他又说了:“我不否认我们这一代人有幼稚简单的地方,但是我总觉得我们比你们思想活跃一些,进步也快一些。”
“还是不要作为一代人来下结论吧,如果只谈你爸爸和我,我们的确不如你和许多跟你一样的年轻人。时代不同了啊,现在的世界主要是属于你们的,你说是吗?”我回答道。
小王笑了,他说:
“还是你们老一代的人比我们谦虚谨慎啊!”我想想又说:
“我们不妨这样说:我们这几代中国人都还没能摆脱历史在我们身上打下的烙印。这正是我们至今都还有许多烦恼的根本原因。但愿我们以后的一代代人能够最终摆脱它们!”
小王说:“那就要看我们国家的人民大众是生活在怎样的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的条件下了。”
我很有信心地回答他:“反正会比我们这几代人好!今后的中国人,一定会是一代更比一代幸福啊!”小王真诚而感慨地说:“总的说来,必须承认,和你跟我爸爸这一代人相比,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活得要幸福得多、幸运得多!”“这或许就是我们这代人的所谓‘生不逢辰’的命运吧?”我说。小王立刻回答我:“的确,这是你们这一代人的命运,而不是某一个人的命运。因为这不是由某一个人独自决定,不是由某一个人独自负责,也不是由某一个人独自承担或独自忍受。这是时代,这是历史,这是人世的沧桑。或者也可以说,这是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甚至是整个人类命运的一个方面。老师,你说是吗?”
我还来不及回答,小王又说:“好在许多事情都已经成为过去。我们的国家现在和以前大不相同了。你们这一代人也可以放心地休息了,剩下的事情让我们这一代人来办吧!我们一定能把祖国建设得一天更比一天好,为后来人铺平前进的道路,让以后的一代代人活得更加幸福,更加幸运!”
稍停一会儿,小王又说:“我们一定能够‘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我感到小王真是“青出于蓝”了,有些不敢和他议论,便没有再说什么话。
智量1995年10月金秋于上海1999年至2010年修改补充我不是小说家。当年参加中国作家协会时,是以一个外国文学评论工作者和翻译工作者的身份被接纳的。我之所以写起小说来,是因为实在闲得难受,要找点事情做做,消遣时光。而且这些年来,我的记忆中留存着许许多多难以忘怀的东西,很想把它们写出来留给后来人看。写来写去,我也没想到,竟写出这样一本来。当然,是很笨拙的一本,和文坛许许多多的美妙作品比一下,我不禁汗颜。
不过,我要说,我还是认真写的。我的消遣是认真的消遣。而且,既然写出来了,就让它去享有独立的生命吧。
作为它的创造者,对它的批评就是对我的批评。我虚心地静候着。或许我还会想到继续消遣下去呢。那么,有了批评意见,我就可以消遣得更加便利些。这小说确是小说,其中利用了一些我个人的经历,但也只是作为素材而已。听说好些古今中外的真正的小说家,开始写作的时候也这样做的。有个朋友在读过我的初稿以后写封信给我,称我“王良兄”,他误会了。
几次修改中,我得到许多亲人和朋友的指点和帮助。其中首先是我的妻子。请他们在此接受我由衷的感谢。
好几位中国和外国的作家和评论家,在这本书还没印出来的时候,已经在报刊上发表了他们宝贵的意见,我更是十分感谢他们。十几位年轻朋友帮我打过字和抄写过,也请他们接受我由衷的感谢,我不一一列出他们的名字了。亲爱的读者朋友们,再见!
智量1995年2月10日于上海《饥饿的山村》初版出书以来,得到广泛的反应,国内外报刊上有过几百篇评论,国内有几个盗版,国外有英语译本,上海作协组织过讨论,直到现在还一再被人引用和提起。现在,我参考各方面的意见,对这部小说做了一些必要的修改和增补,感谢北京凤凰联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和张小波先生的帮助,能够再次把它印出来。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意见和批评。同时我也要借这个机会,给许多对作品提出过意见的朋友们表示感谢,他们给予我的帮助和鼓励是极其巨大的。还希望他们把这次修改补充的本子再看一看,再给我提出批评意见。读者也许已经注意到,这一版中,我把已故复旦大学教授、著名作家贾植芳先生的一篇文章放在了卷首,作为序文。我是借此表示我对贾先生的深深的敬意和怀念。这篇文章的来由是这样的:《饥饿的山村》初版印出后,有一天,我收到一封信,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前辈,著名的施蛰存先生写给我的。他老人家对我的这一次写作实践作了极高的评价,给了我非常热情的鼓励。而在信的最后,他老人家写了这样一句语重心长的话:“你写这样一本书出来,是不是还想再当一次右派呀?”收到信的第二天,我为上海比较文学学会工作的事,到贾植芳先生家里去(当时他是上海比较文学学会会长,我是副会长),我把施先生的信给他看了。他老人家反复认真地把那封信看了又看,还把那最后一句话喃喃地重复了几次,好像深有感触。然后抬头问我:“你怕不怕呀?”还不等我回答,他老人家从他那只破藤椅上立起,用他手中的香烟对着我,说了这样两个字:“再写!”几天以后,上海的《解放日报》上就刊出了贾先生的这样一篇文章。我当然知道,贾先生是怀着和施先生同样的心情和意愿,特意写下这篇文章来鼓励和鞭策我的。他的心愿和意见,实际上就是施先生和所有我们的前辈文学家和作家们的共同心愿和意见。他们希望,我们这些后来人和中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对我们伟大的祖国和伟大的人民负责,更加努力地工作,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美好。于是,在《饥饿的山村》这次再版时,我要把贾先生的这篇文章请来,作为序文。
智量
2010年11月
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一村我的蜗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