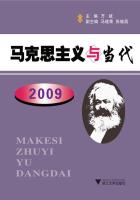首映会结束之后,我从侧门出来,在众人的掩护之下上了阮骁扬的保姆车,记者们跟风而来,我也只适时地留给他们模糊的侧面。
“电影怎么样,****?”阮骁扬兴致勃勃地问道。
“不如你的绯闻精彩。”我慢条斯理地回答,他的经纪人Jessica姐在前面微微一笑,我看得一清二楚。
“****,不要这样说我。你知道的,这绯闻都是炒作,为了新电影造势而已。”他解释地一派诚恳。
“我当然相信你。”我冲他微微一笑。
在外面,戏还是要演好的。
显然这场戏得到了良好的效果,第二天,我就在袁小川手中的报纸上看到了长篇幅的报道,以及巨大的标题:《神秘娇妻出席电影首映会,阮骁扬绯闻传言不攻自破》,其中还附有我依旧模糊不清的侧面。
“我怎么觉得这个人看起来有点眼熟啊?”袁小川指着照片嘀嘀咕咕。
蔚昀泽撇了那照片一眼,未置一词。
“呐,****,你看看,这个女人是不是有点眼熟?”袁小川说着,把报纸递到我面前。
“你不会是想说这个女人像我吧?”我笑嘻嘻地说。
“你?”袁小川挑高眉毛一脸不屑,“阮骁扬的老婆?算了吧!你还是把你那莫须有的老公带给我瞧瞧吧。”
我还想说下去,那边冰山男已经叫住了我:“顾医生你和我去一趟HCU。”
“也就是说这位宋老先生是头部外伤伴有颅骨骨折?”去看完昨天傍晚被直升飞机送来的闭合性脑损伤的患者,我和他走在回诊疗室的路上。
他把片子递给我,我细细看了一遍,心中暗叫不妙。
“果然,有血肿。这么大年纪了,开颅做手术……”我没有再说下去,危险系数是可想而知的了。
年龄大体力也有限,能不能支撑到手术结束本来就是很严重的问题,但是,如何不做手术,血肿在脑中消除不了,也是撑不了多久的。
“而且,颅内压增高,今天还出现了小脑幕裂孔疝综合症。”蔚昀泽的声音和往常一样平静,听不出任何波澜,但是,我却觉得异常沉重。
“最关键的是,从昨天晚上患者被送到医院到现在,他的家人都没有出现过。”
“怎么会?”我也感到十分讶异,“应该是家人不在家或者还没接到通知来不及赶来吧?”
“呵,”他竟然冷笑了起来,“应该是怕支付高额的手术费用,又觉得老人死了也无所谓了吧?反正也活了那么久了。”
“蔚医生你怎么那么说?太过分了!你没有医者之心吗?”我的怒气不禁涌了上来。
“医者之心?不就是器官吗?医生只要技术好,别的东西都是多余的,只会影响判断而已。”他又轻蔑地笑了一笑,从我手中拿走片子。
“蔚医生你不懂亲情吗?你不知道亲情的羁绊是这个世界上最深刻最坚韧的东西吧?你也有父母的吧?”没想到他竟是这样的人,我原本以为他只是冷漠,没想到他根本就是冷血!
“亲情的羁绊是这个世界上最深刻最坚韧的东西?”他突然停下脚步转过身来看我,重复着我说的话,极黑的双眸里看不出一丝波澜,几乎没有一丝温度,像冰冷的湖水令人冷彻心扉。
“怎么?我说错了吗?”我心中有一丝瑟缩,但还是直视着他。
“谁知道呢。我只觉得好笑,你说的那句话。”他不可置否地耸了耸肩膀,“不过有一句话你说错了。”
“哪一句话?”
“我,”他看着我缓缓说道,“没有父母。”
我怔住了,大脑一片混乱,眼看他眼中最后的温度也一点点消失不见了,一转身,他已经进了自己的诊疗室。
没有父母?他说他,没有父母?
“医生,氧设置成3升可以吗?”护士在我耳边说着。
“医者之心?不就是器官吗?医生只要技术好,别的东西都是多余的,只会影响判断而已。”“不过有一句话你说错了。”“我,没有父母。”蔚昀泽的话还一直回响在我耳边。
“医生?顾医生?”
“啊,可以,就设置成3升吧。”回过神来,我慌忙答道。
走过宋老先生的床位,我不禁又想起了蔚昀泽说的话。
已经是第三天了,老先生的家人还是没有见到他的家人,难道真的和蔚昀泽说的一样吗?
没有见到家属,我们也不能贸然动手术,只能先用药物降低颅内压,然而这也不是长久之计。
“顾医生,宋老先生的儿女来了,在你的诊疗室等你。”护士过来传话。
“我马上就过去。”终于来了啊,我心中松了一口气。
推开诊疗室的门,两个坐立不安的人立即站了起来。
看来他们还是担心老人的,我心中想道。
“什么嘛,这么年轻的医生,能治得了老头子吗?”站在那儿的男人怀疑地开口。
“这不是重点,医生我问你,听说爸爸是被直升飞机送来的,那要收取额外的费用吗?”和男人站在一起的女士急急地问道。
原来坐立不安是为了这个,我心里一凉,面上也冷了下来。
“那是免费的。”我冷冷答道。
“原来是免费的,那就好,那就好啊。”那双儿女如释重负地拍着胸口坐了下来。
“下面请听我向两位讲一下宋老先生的病情。”
“那就是说,不管老头子是做手术还是用药物治疗,都活不了多久了?”听完我的讲解,那个男人才平静地开口。
“是。”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
“那,用哪种方法费用低一些?”女士开口问道。
“你说什么?”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是你们的亲生父亲吧?他是怎么抚养你们长大的?你们一点感激之情也没有吗?如果你们以后的儿女也这样对你们,你们会怎么想?你们还知道为人子女的孝心吗?”
两个人再度陷入了沉默。
“你们好好想想吧,你们只有一个父亲。”撇下他们出了诊疗室,我需要透一透气。
刚走到走廊的拐弯处,就看到蔚昀泽和夏雨桐站在那儿说些什么,我立即敏捷地退到墙角。
我发誓我不是有意要偷听他们谈话的,只因为我的耳朵实在是太好了。
“蔚医生?为什么我不可以呢?我是有许多不足的地方,但是只要你说,我会改的。”夏雨桐可怜兮兮地说着。
“不是你不够好,是我自己的问题。”蔚昀泽一脸平静。
“不是的,蔚医生你很好,是我──是我自己……”
“你喜欢我什么?”蔚昀泽突兀地问道。
“呃……”夏雨桐被他突然的询问给怔住了。
“长相?学历?好的工作?”蔚昀泽一一列举着,“你总不会是喜欢我这冷血自傲的性格吧?”
“不是的,我觉得蔚医生是很好的人。”夏雨桐有些嚅嗫。
“很好的人?在你的印象中我是很好的人?”蔚昀泽一反常态地说着,“现在就算我接收你了,你能忍受得了我吗?能一辈子和这样的我生活在一起吗?”
“什么意思?”夏雨桐不解地问着。
“想必你已经听说了,我没有父母,性格孤僻,现在的我是急救医生,每天在医院待的时间超过15小时,你能一直等我吗?能一直等待一个性格冷漠的可能永远也不会向你敞开心扉的人,并且一辈子都没有一丝后悔吗?你能吗?”
这样苛刻的条件,我不禁咋舌。
“永远──”夏雨桐喃喃地说。
“你不能吧?所以说,夏小姐,你根本不认识真正的我,请你回去吧。我还有工作。”
看着蔚昀泽就要走开,我立即跳起来逃走。
诊疗室的门打开,宋老先生的一对儿女走了出来。
“医生,我们准备给父亲做手术。”他们一致说出了这个决定。
“蔚医生,看来老先生的儿女也不是那么不孝,他们还是想救回他的,即使只有一线生机。”我高兴地向蔚昀泽宣布这个消息。
“是吗?”他淡淡反问着,“我去联系脑外科的医生,尽快安排手术。”
“果然,血肿已经影响到周围了,很棘手啊。”脑外科的王医师神情凝重地说。
“还是不行吗?”我站在他身侧,忧心忡忡。
“血压持续下降中,血氧饱和度也在持续下降,无力回天了。”蔚昀泽看着心电监护仪说道。
话音刚落,“滴”的长音,心跳变成了一条直线。
“心脏起搏,快!”
“不行了,恢复不了。”王医师沉重地摇摇头。
手术室里一片沉寂。
“16点36分,确认死亡。”王医师亲自给宋老先生盖上白布。
“顾医生,你写一下死亡记录吧。”
手术室的门打开,宋老先生的儿女已经被通知了死亡消息,低低的压抑的哭声传来。
为什么人总是那样?总是在失去之后才知道后悔。
我心情沉重地走回诊疗室,开始写死亡记录。
这个世界本就是残酷而现实的,只是在医院,这个情况更为突出,生死在这里只不过一线之隔而已。
我拿着死亡记录准备交给王医师签字,刚出门,便听到宋老先生一双儿女在压低声音说着什么。
“我记得你前几年你不是给爸爸买了一份保险吗?”
“那是我买的你又没有出一分钱,现在想要分一杯羹了吗?”
“爸爸这几年在我家吃在我家住,你什么时候又出一分钱了?”
我闭上眼不忍再听,送老先生尸骨未寒,儿女们抹了几滴假惺惺的眼泪之后,便为了钱展开争执。
是我原本就太过天真了吗?还是我一直都把这个世界想象地太过于美好了?
终于走到电梯门口,按下按钮,等待电梯门打开。
“叮”一声,门打开,又正好对上门内那双平静无波的眼睛。
此时此刻的我是多么不想看见那双仿佛看透世事的眼睛,我突然有些恨他,恨他让我看透了那对儿女。
“去找王医师签字?”他背对着我问道。
“是,”我缓缓答道,“蔚医生,我想你是对的,关于宋老先生的那双子女。”
“不用这么沮丧,顾医生,”他的声音仿佛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你已经算是这个世界上幸运的人了,有着疼爱你的父母,所以才会把‘亲情的羁绊是这个世界上最深刻最坚韧的东西’这句话奉为无上的真理。”
他的背依旧挺得很直,仿佛在宣示着即使他一个人也可以扛下极重的负担,即使一个人也能生活得很好,他的声音依旧平静,那么冷漠,仿佛在刻意地拒绝着别人,叫别人不要试图去进入他的世界。
“那么蔚医生,你呢?”我不由自主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
“我?”他终于侧过脸来,“你又想知道什么呢?顾医生?”
我知道自己说了多余的话,但我还是想要说些什么。
“叮”一声,电梯门开了。
“辛苦了。”他朝我示意了一下,稳步走了出去。
长长的走廊上只有他一个人,夕阳的光照在他的身上,把他的背影拉得很长很长,让人没来由地觉得,那长长的影子,竟也那么冰冷和孤独。
电梯门终于关上了,他的身影也消失了。
我想要知道,他那冷漠的心里,到底藏了多么沉重的过往才让他那样的坚硬和冷漠。
我想要知道,冰山蔚昀泽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