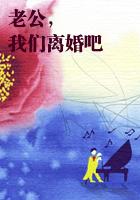工友们喜洋洋地呷喝着,刘叔径直找到工头,把他拽出了人群,开口就对他说:“出事了,要命的。”工头呆了呆,尽管刚才还是一脸喜色,他转头看了一眼刚封顶的大楼,大楼好好的,没有任何要倒塌的迹象,于是他的脸说黑就黑了下来,“么子事呀,你莫吓我。”刘叔说:“那个陆田上次回家时被狗咬了,现在发病了,有点像狂犬病。”工头脸上的喜色褪尽,黑下来的脸稍稍有些缓和。他望着刘叔,刘叔说:“这个病是要命的,冇得治。”
“冇打疫苗吗?”工头问。
刘叔摇摆着头,说:“不晓得呀。”
“那赶紧问呀,如果冇打,就去打呀。”工头跺起脚来,他见过狂犬病,知道它的恐怖。“等等,还是喊人把他送回家。”工头接着说。
没有人愿意送陆田回家,原因很简单,怕他突然狂躁,而自己遭受袭击。工头派工不灵了,大家躲闪着。工地上货车司机也不肯开,有人说:“不如叫他家人来接。”工头狠狠地抽烟,沉默了一会,然后朝那说话的人“呸”了一下,说:“你懂个屁。”
司机一直不同意出这趟车,工头说:“让他坐后边的车厢里,保你冇事。”然后他再派与陆田一个村的两个工友护送,可是这两人死活不愿意。刘叔看不过,便说:“我去吧。”这时强仔也上前,说:“我也去。”大家七搞八搞地把陆田弄上了车,后面车厢是敞篷的,他们把陆田的草席、铺盖、零星的行李都丢进车厢里,陆田用背倚着驾驶室的隔离窗。坐在前边的强仔透过玻璃,只能看到陆田的后脑勺在那摇晃。太阳很毒,强仔就这么被暴晒着,他好像没感觉。待强仔再回头时,陆田已用一件衣服罩住了自己的头,紧紧地拥着自己。一路上,强仔非常不安,不时地回头去看陆田,他有一种犯罪的感觉,自己坐在驾驶室里,而生病的陆田在外边顶着晒人的日头。刘叔不断地抽烟,偶尔也回头去看,看一次,就叹一回气。司机也摇头,说:“这小子命咋就这么薄,太阳还没出山咧。”
陆田是被强仔从房子里扶出来的。坪里的工友后退着,投来的目光有嫌弃与怜悯,陆田闭上眼睛,想挡住这些让他不爽的眼神。也就是在这个混乱中,他被人推到一辆货车车厢里,人还没坐稳,车就开了,工头像送瘟神一样,站在那,举着手,从里朝外地挥摆着,说:“快走吧,快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