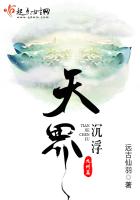因了前些日子修炼的束缚,习洛终得解脱,便如脱缰的野马一般,疯狂地玩闹了几日后,也感腻味,安静下来,打算专心修炼,但总是莫名的心烦意乱,不能专心致志,进境甚是缓慢。
夜风习习,习洛躺在床上,听着屋外的虫鸣声声,辗转反侧,心中想着与老道相识的这些日子里,老道救得习父众人等几件事情,似乎毫无恶意,而且所作所为颇是善良仁慈,想到这些,心中不禁有那么一丝惦念来,猛然想起了老道留给自己的玉牌,从床头上的衣服里翻将出来。
只见玉牌在黑夜里散发着柔和的光芒,反复翻看,只有公孙二字略有些明亮外,并无其他特别之处,遂自言自语道:“老道说当身处险地,淋血其上,玉牌便会自动守护,莫非到时刀枪不入,水火不侵?别是诓骗小爷才好,要不试验一下,看看是否有老道说的那般神奇!”想到此处,玩心骤起,心下莫名兴奋。
但又转念想起老道的告诫,此玉牌仅能使用三次,若效果真如老道所说,那可是增加了三次活命的机会,珍惜至极,无端浪费,实在不该;另外尚需刺破皮肉见血,习洛本就惧怕疼痛,摇摇头,只好作罢!
既然无眠,不如修炼,习洛便盘膝打坐起来,随着功法修炼的愈加娴熟,纳入的灵气从原来的星星点点,变的浓郁了许多,而且在体内运转的周期越来越短,最后聚集在丹田之中,更加充盈膨胀……
直到天色渐亮,习洛才疲惫的睡去。中午方才醒转,饭也没吃,寻了肖家兄妹说了会话,索然无味便即离去,向着河边而来,不巧碰见了二愣子,又调侃了几句,心情略有好转!
“啾啾……”一阵急促的鸟鸣入耳,习洛抬头上瞧,只见旁边一棵大树的枝杈上,不知何时多了一个鸟窝,习洛着实惊讶,因为整个村子甚至四周,上至哪棵树上有哪种鸟搭什么窝,下至哪个洞里有老鼠哪个洞里藏蛇,对于这些熟悉的程度,村子里根本无人能习洛……
只见干草编织的鸟窝边缘,一只小的赤羽鸟张着略有些毛羽蓬松的翅膀,身体不住地挣扎着向窝中退去,显是极度惊吓不由得的尖叫连连,再看其身后,似有一只体型略大的火红色的赤羽鸟,毫不理会它的鸣叫凄凄,正在用头部把它不断地拱出窝外,一时竟然僵持在那里,许久,小的赤羽鸟终是身单力薄不敌之下,身子一倾,掉落下来,小鸟拼命的煽动着翅膀,但显然初试飞翔不得其法或是嫩翅无力,不改下跌之势,习洛心下一惊,叫声“不好”,却是猝不及防,已然来不及接下,就在小鸟即将落地的一霎,生死的瞬间,小鸟居然掠过地上的草尖,横飞了出去,而后越飞越高,消失在了树林里……
习洛心中石头落地,擦去头上的冷汗,才想到这是大鸟逼迫小鸟飞翔独立的一幕,只不过做法略有些残忍罢了,但转念一想,大鸟若非如此,小鸟居高视下,胆怯惊怕,恐是很难有翱翔天际的一天。
想到这些,习洛心下释然,可紧接着“倏”地身子一震,猛地想到:“自己也不正是如此吗?外面的大千世界,广阔无边,小小的落云岭,就算是那青阳镇又如何?也仅是那漫天繁星的一点,如是不出去走走转转,就似那窝中的蠢鸟,世界便是树下的一片,又是那井底之蛙,只能看见巴掌大的天。安于村落,终其一生,不是在狩猎中意外的死去,便是百年后枯骨一堆,何其枉然!”
习洛目露茫然,怔怔地望着远处的天空,口中呢喃:“我是做那井底的青蛙,还是翱翔的鸟雀……巴掌大的天空……无边的天际……”
蓦地,习洛朗声大笑,颇为豪壮,而后喊道:“我习洛既得此仙缘,任他前路萧萧,坎坷缥缈,我定披荆斩棘,乘风破浪,走出一番自己的天地,若是山水挡我,开山覆水;人要阻我,我……我让他魂飞魄散,天要灭我,我便逆了这个天,若有……”说道此处,语顿,已是势薄声弱,思索片刻后,才自喊道:“若还是有什么不可逆之事,那老子也是无怨无悔,十八年……十八年后还是条好汉……”说到最后,声音微颤,已是心虚不已。
不过习洛本有些郁闷烦躁的心,豁然敞亮,目光也变的坚定起来,其中还有火热之色。
……
“什么?习洛哥哥你是疯癫还是魔症了?”村外的河边,本席地而坐的肖泉,“忽”地站起,杏眼圆睁,一脸的不可思议,指着习洛,尖声叫道。
“习洛兄弟,那什么修仙法术什么的,都是世俗传说,可是当不得真啊!”肖雄也是与肖泉一般的模样,粗声粗气地劝导。
“嘘,我说你们两个能不能不大呼小叫的。”习洛做了个噤声的手势,眼睛瞪得溜圆,赶紧四下张望,怕是有人听见他们的对话。
“习洛哥哥,此事绝无可能,你知道习叔叔和婶婶定然不会同意,还打算自己偷偷溜走,异想天开的着实令人可恨!”肖泉根本不予理会,眼角一挑,兀自嚷道。
“我说姑奶奶,咱小点声成吗?”习洛拱手作揖,哭丧着脸,乞求道。
“你不去寻那子虚乌有的什么仙人,我自然不会大声!”肖泉听了习洛讨饶的话,嘟着嘴巴,瞬间变的可怜兮兮的模样,挨近习洛身前,摇晃着他的胳膊,柔声道:“好哥哥,求你了,终究还是妹妹舍不得你吗!”
西洛听了肖泉娇滴滴的话语,心中不禁一阵酥麻,但有口难言:总不能告诉二人老道就是位活神仙,救得进山狩猎众人性命,又赠灵草治愈他们的父亲,而且现在万里之外的什么仙云宗,叫自己前去相见。莫说他们二人不能理解,就是自己此番前去寻那老道,也是前途未卜,兀自提心吊胆!但势在必行,又不能与父母叙说,只能不辞而别,而后让他们兄妹事后告知,晓得自己的去处,免得到时父母担心自己的无故失踪来。还有就是此去遥遥无期,母亲体弱多病,随着年龄增长,身子日渐孱弱,而父亲不时进山狩猎,尚需二人平日里多加照看。
习洛正暗自头痛,该如何说服肖家兄妹,忽然头脑中灵光一闪,计上心来,自觉甚妙,随即“哈哈”大笑起来,二人面面相觑,具感莫名其妙。
“看看你们兄妹两个,又被我骗了不是,哈哈……”习洛看着二人似不明其意,接着说道:“我习洛聪明智慧,岂能干那镜中花,水中月,寻仙问道的蠢事儿?”
肖家兄妹终于长吁口气,纷纷指责习洛。
“其实我要暂时离开村子倒是真的。”话一说完,偷眼看着二人不解的神色,又继续说道:“常来咱们村子的老先生,一直劝说我好好读书,将来好考取功名,光宗耀祖,荫庇村落,是也不是?”
习洛所说,确有此事,肖家兄妹与他一起读书识字,自然知晓,便点头回应。
“但我原本不醉心于此,经过此番肖伯伯与我父亲等人进山狩猎遇袭,实是凶险,我方才明悟,若是大家都有钱财购物,能解温饱,想来自不会有人深入险地,是也不是?”习洛贼眉溜眼,接连反问。
兄妹二人去过黑棋岩搬运鹿尸,那血流成河的场面,历历在目,再加上父亲险些丧命,此事虽是已然过去,但每每想起,还是心有余悸。习洛再次提起,话语之中,其情其理,不难理解,二人又是连连点头。
“经商买卖,咱们没那头脑,又无资金,自不用提。剩下只能是考取功名,高官厚禄,福泽村子,才是长远之计!但村子里谁能有这个本事?还不是我习洛吗?”习洛侃侃而谈,一副舍我其谁的模样。
二人先是听了习洛前面的话双双摇头,又因了紧接着后面的一句,又齐齐点头。
习洛看着两人的模样,心里暗笑,轻咳一声,继续道:“佛家有云,‘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逼不得已,我也只好负此重任!唉,但我自知学识浅薄,远远不足,但镇子上的老先生也是学识有限,所以我才要背井离乡四下求学,即使在外漂泊,天地为床,风餐露宿,生活多么辛苦,但我相信,‘有志者,事竟成’。寻得名师,虚心求教,刻苦修……不是……是刻苦学习,以期有成。”习洛一番话语,尽是苦言悲词,最后却差点溜了口舌。
“习洛哥哥,原来你是这般心思,为了村子你甘愿付出这么多……”肖泉话未说完,已然扑到习洛的怀里,泣不成声。
肖雄也是深为感动,眼中噙泪,展臂拥着二人,呜咽着说道:“我身为兄长,本不该让习洛兄弟担此重责,都怪我愚钝,都怪我愚钝……”说话间,不时用拳头锤着自己的脑袋……
习洛本欲煽情求得二人帮助,没想到结果有些出人意料,忙推开二人,嘻笑道:“我是去求学,不时回来,又不是命赴黄泉,永不相见,瞧你二人哭哭啼啼,成了什么样子!你们只等我学业有成,考取功名,说不得将来封侯拜相,也有可能。到时泉妹妹就是官夫人,穿金戴银,出行皆得八抬大轿。至于肖雄哥哥吗!我举荐你做持刀大将军,指挥千军万马,好不威风!”
“谁要做你的官夫人……”肖泉犹在的脸上泛起红晕,啐道。
“我如何做得了大将军,做你的侍卫保镖就是了。”肖雄抓着头,傻笑道。
“做得,做得……但是你们一定要先替我保守秘密,此事万万不能让我父母知晓,要不我此番舍己为人,大公无私的宏图抱负便化为泡影,更不用再提什么官夫人,大将军……”习洛口气悠悠,内心却是焦急盼着二人赶紧答应下来。
兄妹二人低头沉默良久,才勉为其难地点点头。习洛心中石头落地,不禁欢呼。
三人本是懵懂的少年,片刻便打闹起来,但自知相聚时短,皆是满怀心事,实在不能尽兴。
到了最后,习洛才郑重地拜托二人,帮忙照顾母亲时,两人举手发誓,表示会视若亲母一般的对待,习洛心中不禁感动。
又想到自己突然无故失踪,若是肖家兄妹自去相告,定有“知情不报”的后果,免不得遭受牵连受到责罚,实非自己所愿,只好作罢!但却反复叮嘱二人不可泄露此番计划。
天色渐晚,分手之时,肖泉突然问起习洛,何时动身时,习洛含糊地说道‘还未确定,到时相告’后,三人才依依不舍的散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