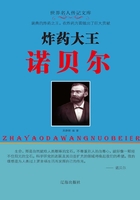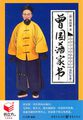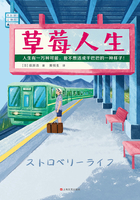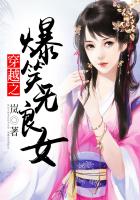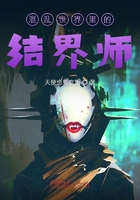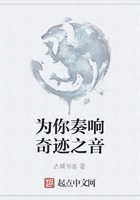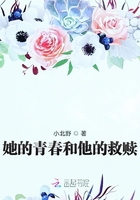提起“四人帮”干的坏事,凡是经历过那个史无前例的大动乱年代的人,常常会引用一句古代成语“罄竹难书”。中国古代没有发明造纸术以前,是把文字写在竹板上的。这句话的意思是,砍光了山上的竹子也写不完他们的坏事和罪恶。何况这一本小册子,更难以把“四人帮”的丑恶罪行说得全面不漏,只好用中国传统的办法,把他们的主要罪行列为十大罪状(即十恶不赦),以昭告于天下。
1. 炮制“黑线专政论”,掌控舆论
所谓“黑线专政论”,出处是前边已经谈到由江青主持毛泽东批准的那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那段著名的话:“文艺界在建国以来,(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却基本上没有执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
请大家不要小看这一段话,它从内容上说非常恶毒,非常厉害;而从政治上说,又是非常阴险的一招。
首先,《纪要》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补充了理论的和现实的依据。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决策者是毛泽东,这是毫无疑问的。“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政治大革命”,只是这一革命以“文化界”为突破口,最先从“文化界”开刀,这是毛泽东毫不隐讳的,也是众所周知的。毛泽东对新中国的文艺界不满意,这也不是秘密。
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毛泽东接连发表两个批示,认为“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因而,要改组文化部,在文艺界搞整风。但他还承认,“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问题也不少”。各种文学艺术协会中,“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还没有一笔抹黑,全盘否定。可是,到江青的这个《纪要》里就大大升级了。
第一,提到了阶级斗争的高度。认为“在我国革命的两个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文化战线上都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文化战线上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这样,一下子就把自己的对立面推到了敌对阶级的地位上,成了胆敢与无产阶级争夺文化战线领导权的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变成了专政对象。
第二,把建国后十七年的文化战线的成绩一笔抹杀,作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样全盘否定的总估计。既然整个文化界的状况这样恶劣和黑暗,那么来一次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的大风暴,也就理所当然的了。从这个角度看,它又是毛泽东文艺批示的补充和延伸。
应该说,从基本估计和基本思路看,江青的《纪要》同毛泽东的批示是一脉相承的。因此,《纪要》就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和肯定。据说,毛泽东前后修改过三遍。第一遍改20处,第二遍改19处,第三遍改5处。又亲自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两处,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同志。”文件的标题中“林彪同志委托”六个字是毛泽东亲自加上的。而在中共中央转发这份《纪要》的同时,转发了林彪给中央军委常委的信。信中,林彪强调,这“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这里说的“极大的现实意义”,恐怕就集中体现在它为“文化大革命”补充了现实和理论的依据吧。
其次,《纪要》为江青出台充当协助毛泽东指挥“文化大革命”的助手、“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成员”,增添了理论色彩和重要依据。前边已经说过,江青出场有两个重要法宝:一是有毛泽东的指示作为尚方宝剑;二是有林彪的支持作为保护的“尊神”,而江青本人的资本却不多。当时只搞了两个样板戏,虽然打起了“文艺革命”的旗子,但在一般人心目中,江青是比较浅薄的。而这时则不同了,《纪要》提出了一套所谓“无产阶级文化路线”的新理论,当然是打着毛泽东的旗号,但同时也为江青自己增添了理论资本。
这样,江青就一手捧着尚方宝剑,一手拿着“无产阶级文化路线”的令牌,两旁有“尊神”保驾,摆出一副正气凛然、神圣不可侵犯的架式,威风凛凛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登台亮相了。
再次,《纪要》大大扩展了“文化革命”的内容和对象。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时间上限于建国以后,范围上只指新中国的文艺界。而《纪要》则把时间和范围都大大扩展了。时间扩展到所谓“三十年代文艺”。
三十年代前期是国内阶级矛盾和斗争非常尖锐激烈的时期。在大江南北,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同蒋介石领导的白军,进行了一次又一次大激战,炮声隆隆,硝烟弥漫。而在国民党统治区,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化工作者,同国民党的反动文化统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毛泽东曾赞扬鲁迅是中国“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可是,江青的《纪要》虽然不敢公开否定鲁迅,却把在他们领导和影响下的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化一笔否定了。《纪要》说:“要破除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那时,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文艺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戏剧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思想,他们是俄国沙皇时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思想。”
关于如何评价这些世界知名的俄国资产阶级文艺家的思想和理论,不是这本小书所能承担的任务。但是,从引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江青是利用这种方法对三十年代左翼文艺一笔否定的。而否定了三十年代左翼文艺,对于当年在左翼文艺中作了贡献的,而六十年代还在担任新中国文化战线领导工作的一大批人,包括周扬、夏衍、田汉等等,给予批判以至打倒,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范围则不限于中国,扩展到了国外。《纪要》中明确提出要点名批判的是苏联著名作家肖洛霍夫。《纪要》说:
文艺上反对外国修正主义的斗争,不能只捉丘赫拉伊之类小人物。要捉大的,捉肖洛霍夫,要敢于碰他。他是修正主义文艺的鼻祖。他的《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一个人的遭遇》对中国的部分作者和读者影响很大。
江青当时把这项批判任务交给解放军,让军队组织一些人“写出有分析的、论据充分的、有说服力的批判文章”。江青的胃口很大,她不仅要批判当时苏联的著名文艺作品,而且提出:“要破除对中外古典文学的迷信。”大家知道,斯大林晚年是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的,包括文艺方面也是“左”得很厉害的。可是,江青却认为斯大林“左”得还不够。她说:“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对资产阶级现代派文艺的批评是很尖锐的,但是,他对俄国和欧洲的所谓经典著作却无批判地继承,后果不好……我们应当接受斯大林的教训。”
江青同斯大林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是两类人,但是她的这一番话却明确无误地表明,她要比斯大林更“左”。
最后,《纪要》的影响绝不仅是限于文艺界或文化界。既然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的文艺界,可以是被“一条黑线专了政”的,那么别的领域也就可以依此类推,扩大到各行各业。事实上也正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黑线专政论”就急骤膨胀。
教育战线毛主席已经说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当然是“黑线专政”;卫生战线,毛主席已批评其领导机构是“城市老爷卫生部”,当然也是“黑线专政”;体育战线主管的副总理贺龙元帅都被批判打倒了,当然也是“黑线专政”,如此等等。开始还主要是意识形态部门,以后又扩展到外交部门、工业部门、商业部门、农业部门了。
“黑线专政论”成了当时各地、各部门的造反派炮轰、火烧的重要理论依据和重型炮弹。虽然周总理一再出面解释,新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毛主席红线的光辉照耀到各行各业,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很难阻止“黑线专政论”的急剧膨胀和扩展。这种谬论的恶果是十分巨大的,造成的损害也是十分严重的。
2. 操纵群众组织,酝酿大阴谋
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种战略设想。毛泽东在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中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
但是,怎么样使天下大乱,又怎么样才能达到天下大治,信中都没有说。不过,江青在毛泽东身边多年,对毛的意图是比别人有更多了解的。她知道毛泽东一生特别钟爱群众运动,于是就下大力气操纵和控制群众组织,通过群众组织制造天下大乱而实现他们的阴谋目的。
这样的事例很多,下边我们只举几件典型的,影响比较大的。
先说一个利用群众的名义投领袖所好的例子。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个人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当时曾被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经毛泽东批准,在中央电台广播、《人民日报》发表,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那么这张大字报是怎么产生的呢?它是聂元梓等人自发地主动地写出来的吗?不是。它是受人指使授意而写出来的。这个指使授意人,就是林彪、“四人帮”的高参、“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康生。
康生善解上意,是极少数比较了解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意图的中央领导干部之一。于是,他就派自己的老婆曹轶欧带几个人到北京大学去了解情况,物色造反的带头人。北京大学地处首都,历史悠久富有革命传统,是“五四”运动的带头人,“一二·九”运动的中坚,是被称为“庙小神灵大”的地方,在国内外都有较高声望。在这里找一个适当的人选,登高一呼,影响自然非同一般。
不过,康生、曹轶欧开始要找的人并不是聂元梓,而是一位当时的地位和声望都比聂高的人,这个人叫陈守一,是北京大学法律系主任、教授,北大党委的常委。陈教授发表一篇回忆文章《历史是公正的》,披露了这段鲜为人知的情节,现摘录如下:
1966年的5月上旬,我在家里,突然电话铃响了。电话听筒里传来一个陌生女人的声音。她自我介绍说,她的名字叫曹轶欧……很快,这位曹轶欧便带着另一位姓张的同志,出现在我的客厅里。……曹轶欧坐定之后,先问了问北大学术批判的进展情况,然后话锋一转,提出北京大学的学术批判有问题、应该给予揭发。我当时一怔,感到有些突然。我问道:“不知道有些什么问题,请向我提出来,以便改正。”她挥挥手:“这不是你的问题!你应该勇于出来揭发陆平和市委领导。”我莫名其妙了:“北大的学术批判是我具体负责组织的。但我还没有感觉到有什么问题。如果有问题,请你提出来,以便于我改正。”她笑了笑,慢慢说:“你不负责。但你要揭发。只要揭发,你什么责任也没有的。”
第一次没有谈拢。
大约三四天后,也就是5月15日左右,曹轶欧的电话又来了。这次是约我到友谊宾馆面谈。我去了,她和高教部副部长刘仰峤在楼上的一个房间里接待了我。她问我考虑得怎么样了?我还是请她先把问题指出来。她犹疑了一下说:“学术批判不得力,你不负责;如果你能出来揭发,你更是什么责任都没有的。”然后,她还进一步暗示:“如果你同意揭发,还会有人和你一同出面的。”
这次又没有谈拢。一直到5月25日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贴出后,“我才终于明白曹轶欧约我两次谈话的意义何在了”。根据已经了解的大量材料证明,就是在曹轶欧找陈守一的第一次谈话之后,身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书记的聂元梓主动找到曹轶欧,并在曹的授意和指使下写出那份大字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