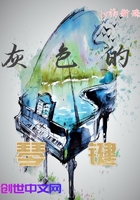宿远看他们年轻人好不容易聚在一处,自己在一旁看着也不好插话,另外也怕他们觉得不自在,于是起身朝闵兰使了个眼色示意她一同先行离开,随后又转头看向林夏,“伯父还有事要处理,就不耽误你们年轻人叙旧了,你父亲的病不必太过担心,我自当尽力而为。”林夏亦起身相送,“宿伯伯乃太医院翘楚,晚辈自是信得过的。”
闵兰微笑着拍了拍他的肩,“留下吃晚饭吧,孩子。”见他并未推辞,也就不再多说什么,随着宿远一同走了出去。
宿安端起桌上的茶杯,隔着氤氲水雾,凝视那张曾经无比熟悉的脸,听他讲述自己在英国求学的所见所闻,泰晤士河畔恢宏的历史建筑,象征胜利意义的纳尔逊海军统帅雕像,葬有众多伟人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具有文艺复兴风格的圣保罗大教堂,还有见证过英国历史上黑暗时期的伦敦塔。天气好的时候他会背上画板寻一处安静的角落画画,梧桐树的叶子落下来,他会用羽毛笔在上面写些字,然后把叶子放在水里,祈祷康河的水将思念和祝福带到故乡,下雨天,他会待在屋子里看看书写写信,和朋友聊天……宿宁端坐一旁,听得十分入迷,偶尔在他停下喝茶的间隙紧盯着他追问“然后呢?”……
许久不曾如此畅谈,宿安忽然发现,那些她小心翼翼藏在心底珍而重之的回忆如潮水般涌现……
宿安的记忆里,有一处小小庭院,那里藏着她小时候,所有的快乐。
光绪二十七年,朝廷和洋人签订《辛丑条约》,把东交民巷划为使馆区。使馆区范围内的衙署都必须迁走,太医院一时找不到新去处,只得暂借东安门大街御医白文寿的宅第应差。彼时的宿安,虽只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却已熟读医典,精通药理。宿远更是乐得把她带在身边,俨然把这个聪明乖巧的女儿当做自己的衣钵传人来培养。因此,宿安的大多数时光,都是在太医院度过的。偶尔,从私塾回家的路上,林夏和宿宁会一起去东安门大街的白宅找她。
院子里的古槐树下,少年捧一卷书,静静品读。偶尔抬头笑看着在树下玩闹的姐妹。宿安不知从哪里找来一张白色的巨大纱布,宿宁则兴奋地冲他挥手,“林夏哥哥,快来呀!槐花落到布里面,就可以带回去做成槐花糕了!”
风吹过,乳白色的小花纷纷扬扬落下,宿安伸出手,落在掌心的槐花,柔软,娇俏,带一丝微凉的触感。凑近鼻端,便嗅到一缕淡淡的香气。林夏不知何时站在了她身旁,轻轻拂去她肩头的花瓣。
“想什么呢,这么出神?”
“味苦,性微寒。这小小的槐花可是凉血止血,清肝泻火的良药呢。”
林夏无奈地笑笑,“这种时候不是应该想到‘春风一夜庭前至,槐花十里不胜香’之类的吗?你这丫头,难不成真想成为扁鹊、华佗那样的一代名医?”
“……”
“谁把我晾在院子里的纱布拿走了?”尖锐的女声划破一时寂静,身着藏蓝色粗布棉衣,腰间系一条黑色围裙的妇女两手叉腰,气势汹汹地瞪着他们。
宿安怔怔地站在原地,脸色苍白,薄唇轻启像是要解释什么,下一秒,林夏修长的手指绕过她的腕子,并紧紧握住,他回头对宿宁喊了一句,“跑!”宿宁立即心领神会,拔腿就往院门口跑,林夏拉着宿安,也跟了上去。
他紧紧握住她的手,穿过喧闹的大街,可是她的世界一片寂静,只剩下自己一声一声,仓促而清晰的心跳。
“小姐。”素衣轻轻唤她。
她回过神来,茫然地问道,“怎么了?”
“姐姐,林夏哥哥说要不要一起去园子里走走?”
“哦,好啊。”她低下头,以免让人看出眼底的一丝慌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