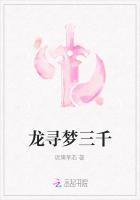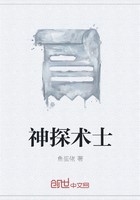昌珠寺是西藏的第一座佛堂。藏语鹞、鹏、鸟为昌,龙为珠,寺名昌珠,与民间传说“引龙出湖”、“断龙为三”有关。史书称它建于松赞干布时期,传说文成公主用五行算法算出妖魔罗刹女的一臂在贡布日的西南,需建一寺镇压,方能保证国运昌盛。而那里是一大湖,湖中有一五头怪龙在兴风作浪,于是松赞干布即在贡布日修法终成正果,遂令大鹏鸟降伏了怪龙,湖水也随之干涸,昌珠寺亦即在此建成。
步入大门,映入眼帘的是拉康大院,大院前有高大的门廊,门廊两端与围绕在整个大殿外面的转经回廊相界,适成一周,是为该寺外转经回廊。门外两侧塑护法神像二尊,站于两旁;门内两边又塑四大天王,分立左右。大院内,前部中央为天井院落,其后接错钦大殿。围绕天井院落和错钦大殿一周,则是内转经回廊。沿着中转回廊四周,内向分布着十二个内容各异的拉康,形成了井然有序的朝佛“流水线”,信徒们循此便被导引去依次朝拜各个佛尊。这种布局和大昭寺大殿布局很相似。我与藏民一样,依次沿着转经顺序进入每一间佛堂。阴暗的室内,除了佛像前面供奉着的酥油所发出的光亮之外,这里没有任何的照明工具。我的视线时而往脚下看去,显得小心翼翼。而身旁的藏民对佛堂的转道曲径,显得娴熟有余。他们轻盈的脚步如同口中念出的经文,每走过一尊佛像前,布施一些零钱。他们的手里提着盛满酥油的容器,每走过一间佛堂,皆用勺子盛出一些酥油放置在酥油灯里。燃烧的酥油灯映照着每一个人的面庞,在神灵面前,他们的虔诚内心,被光明照耀。供奉,是一种修行美德。懂得布施,给予,是爱的细节体现。藏民族在历史的长河里,将宗教教义融化为人与人之间交往处事的行为道德准则。这是宗教的人性化体现。一个虔诚的信徒,因此懂得从神灵的教义中,广泛的宣扬怜悯,施舍,宽厚,博大。
步入二楼,在一间并不宽敞的佛堂里,供奉着一幅珍珠唐卡图,是一件世界罕见的珍宝。这幅用珍珠串起成线条绘出的“观世音菩萨憩息图”(坚期木厄额松像),是元末明初的西藏帕莫竹巴王朝时期,由当时的乃东王的王后出资制成的。整幅唐卡长2米,宽1.2米,镶嵌珍珠共计29026颗,钻石1颗,红宝石2颗,蓝宝石1颗,紫宝石0.55两,绿松石0.91两(计185粒),黄金15.5克,珊瑚4.1两(计1997颗)。珍珠唐卡掩不住时间的洗礼,但还是美得那么夺目,那么耀眼。我想用相机记录下这幅被时光雕刻过的唐卡。当我准备拿出相机,抬头处一行字“请勿拍照”阻绝我的肆意行为。在与美邂逅的那一刻,我们会有一种强烈的冲动,就是一种握住它不放的渴望:将它占为自有,并使它成为自己生命中举足轻重的一部分。我们有一种迫切的想去表达的欲望:“我曾在这里,我看见了它,它对我很重要。”这出于我们对美的理解。罗斯金曾对美作出五条结论:首先,美是由许多复杂因素组合而成,对人的心理和视觉产生冲击;第二,人类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倾向,就是对美作出反应并且渴望拥有它;第三,这种渴望拥有的欲望有比较低级的表现形式,包括买纪念品和拍照的欲望;第四,只有一种方法可以正确的拥有美,那就是通过理解美,并通过使我们敏感于那些促成美的因素(心理上的和视觉上的)而达到对美的拥有。最后,追求这种敏锐理解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尝试通过艺术,通过书写或绘画来描绘美丽的地方,而不考虑我们是否具有这样的才华。但现代人普遍使用的方式,就是拍照。“恐怖的十九世纪,机械给人们带来了各种害处,但照相机提供了一种解药剂”,罗斯金批评道,“使用者不是把摄影作为积极而有意识的观察的一种补充,相反,他们将它作为一种替代物,以为只要有一张照片,自己就把握了世界的一部分。事实上,照相机并不能使我们真正拥有。照相机模糊了观看与注视之间,观看与拥有之间的区别。它或许可以让我们择取真正的美,但是它却可能不经意地使意欲获得美的努力显得多余。”
历史离我们越来越远,站在它的面前,手中的相机被击溃成一地尘埃,注定我是微不足道的子臣,周围的铁栏阻绝我与唐卡的接近。它获得与神灵一般的殊荣,与凡尘保持距离,只可远观,不可亵玩。
珍珠唐卡的附近,有一根柱子。上面挂满了各种各样的旧物。发夹,手表,佛珠,护身符……达娃次仁告诉我,这些都是信徒身上长期携带的物品。例如有些人生病了,家人就会把病者身上经常佩戴的一些东西取下来,放置在寺庙里,接受神灵的加持。藏民认为,供奉神灵的佛堂是神圣之地。身上的旧物放置在这里,自己也会获得神灵的保佑。藏民对神灵的信仰,如同把自己的一切都交付给神灵保管。
昌珠寺是当年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联姻时修建的。昌珠寺最初的规模很小,据说只有六门六柱和祖拉康,后来,该寺一度遭毁,曾经三次大规模的修缮和扩建:
(一)寺史记载:“乃东贡玛司徒菩堤幢曾对该寺大加修建”。其时代因而不会早于公元1351年。这次修建后增添了较多佛堂,可以说大体奠定了以后昌珠寺的格局。
(二)五世达赖时期曾对该寺作过较多修缮和增建,加盖了大殿金顶、错钦大殿门的门楼,除其底部留有少量原来建筑外,余皆五世达赖时期改建和增建。该寺前庭院南侧的桑阿颇章也系其时的建筑。
(三)“七世达赖格桑嘉措亦曾修缮此寺”。这次修缮和扩建后的昌珠寺,规模比以前扩大了百倍,面积达4667平方米(长81米、宽57.6米),拥有21个拉康和漫长的转经回廊,屋顶饰以富丽堂皇、熠熠生辉的金顶,更显得非同凡响。
寺庙多次遭到破坏,且年久失修,现仅存大殿。殿内的正中原来供奉的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等人的塑像现在荡然无存。二层的西部,即拉康大院的门顶上,正中为达赖的行宫,行宫的北边有较小的房屋两间,名结月康,乃传为贵族休息之所,其中原存铜法器及用具甚多。有一件大明宣德年款的铜钹,是很珍贵的文物,“文革”中惜已流失,现山南地区文管会有一征集来的铜钹,与之年款相符,是寺藏原物。十年浩劫中亦未免大难,除被其时用作粮物仓库和僧人居住的少数建筑有幸存留外,错钦大殿和绝大多数的拉康、转经廊等建筑皆荡然一空,其他文物也散失殆尽。
流动的时间长河,历史动荡不安。有一种遗憾,因为自身的渺小无法抵抗时代的抉择,文物是无辜的。但人们总喜欢在他们身体强加罪名,遭戮杀。同时,我又感到些许庆幸,毕竟历史的真相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还原本来面目,这些犹存的文物,成了命途多舛的幸存者。
从昌珠寺到雍布拉康,只有六公里。我与达娃次仁乘车而行,作为导游的他,一路上向我介绍起雍布拉康。雍布拉康是西藏第一个藏王聂赤赞普在西藏古老的土地──雅砻平原上建起的第一座宫殿,也是西藏最早的建筑。距离现在已经有两千多年历史。按藏文的意译,“雍布”是母鹿,“拉”是后腿,“康”是宫殿,合译为“母鹿后腿上的宫殿”。因雍布拉康所在的山形似一只侧卧的母鹿,宫殿恰好建在这“母鹿”的后腿上,故名"雍布拉康"。
冬日的泽当,远山光秃,蓝天一尘不染,参差对照,如同人工布景。蓝天与远山之间,间隙分明,而且那么层次有序。一个从内地而来的人,总会明显感觉到视觉分辨色度的明亮冲击。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这种景象更应在经过加工的风景明信片里存在。
在山脚下,我看到西藏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康伫立于群山之巅。它的身体与天空无比接近,为青藏高原开启第一座仰望的天堂。伟大的建筑,总是以高度见长。在西藏,或许出于宗教因素,或者当权者的政治色彩,宫殿往往起建于高处,坐拥群山。如布达拉宫正是如此,可见两千多年前修建者的深思熟虑。
通往雍布拉康,有一石阶梯。蜿蜒曲折,盘旋而上。我感受到体内传来的沉重呼吸声,高原里的氧气稀薄,加上爬山的肢体运动,力不从心,我的呼吸上气不接下气。总会有一些藏族人轻易地越过我,直到他们的身影渐渐消失在我的视线之外。从我身边走过的藏族妇女,或是孩童,他们的呼吸声很低很低,脚步轻健如飞,易如反掌地打击一个见多识广、阅历丰厚的旅行者的骄傲。我的身体置于半空中,临涯独行,有一种“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的孤独。此时次仁凭着藏族人天生的一副强健身体,已走在离我二十多米的前方。越接近雍布拉康,离天堂的距离就越近。午后的阳光,浓稠得如同天堂撒下人间的帷幕。抬头处,雍布拉康伫立在雅砻河谷,与我邂逅是在了二千多年后,它的来路因此模糊不清。只有石阶知道这里曾经的辉煌以及没落。但沉默不语的石阶,对历史的来路保持一贯的缄默。我只能看到“现在”的雍布拉康,所谓的“现在”,是一条流动的河。永远处于一种运动状态,永无止尽的漂泊是它的宿命。所有的一切,都将成为过去。历史掩藏在时间深处,对此我一无所知。石阶对我这个不速之客,最大的礼遇不仅为我提供一条进入雍布拉康的通道,更重要的是,时间的痕迹通过空间来展示形骸。石阶的存在,为我打开一道看不见的历史隧道,我由此看见那些暗藏在时间深处尘封千年的历史记忆。
雍布拉康据说建立于公元前2世纪,民间传说云,“宫殿莫早于雍布拉康,国王莫早于聂赤赞普,地方莫早于雅砻”,雍布拉康正是聂赤赞普在雅砻地方建造的宫殿。很长一段时间,这里曾是部落首领居住的地方。直到松赞干布那一代,政治中心真正转移到拉萨。在书上,关于第一个藏王聂赤赞普的传说,具备神话色彩。
昌珠寺
传说中聂赤赞普本是天神的儿子,后降临人间,到了现在山南境内羌脱神山,被十二个放牧者看见了。这个小伙子的言语举止与本地土著不同。放牧的人们辨别不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应该如何处置这个年轻人,便派人回聚居点报告。长者派出十二个颇为聪明的巫师教徒上山,盘问小伙子从哪里来,这个小伙子用手指指天。这伙人自以为小伙子是从天上来的,是“天神之子”,格外高兴。十二人中为首的便伸长脖子,给这位“天神之子”当轿骑,前呼后拥地把他抬下山来。聚居在这里的人们纷纷前来,见这个从天上来的小伙子,长得聪明英俊,便公推他为部落首领。这就是后来叫做“吐蕃”的部落第一位领袖。这是公元前二百三十七年的事。人们尊称他为“聂赤赞普”,也就是“用脖子当宝座的英杰”。藏语中,“聂”是“脖”的意思,“赤”是宝座,“赞普”是“英武之主”。自此,历史上把藏王称为赞普。这个聂赤赞普,便是吐蕃部落的第一个首领。苯教典籍还把聂赤赞普说成是色界第十三代光明天子下凡,所以氏族和苯教徒共同把他拥立为王。从他开始,到吐蕃王朝建立,一共传了三十二代。
聂赤赞普建造了雍布拉康,为了防止其他部落侵犯乃至野牦牛群的冲击。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vre)说:“有一种空间的意识形态存在着。为什么,因为空间,看起来好似均质的,看起来其纯粹形式好似完全客观的,然而,一旦我们探知它,它其实是一个社会产物……让我再重复一次:有一种空间政治学存在,因为空间是政治的。”
雍布拉康分为两部分,前部是一幢多层建筑,后部是一座方形高层碉堡望楼,与前部相连。雍布拉康一共三层:第一层距地十数级石阶,前半部为门厅,厅外是一个带檐的小平台,往里是佛殿,殿内供有松赞干布、文成公主、尺尊公主等人的塑像;第二层前半部为三面环绕矮墙的平台,后半部是带天井的回廊;二层以上原有第三层,后廊有小门通入碉楼式建筑中,现在尚未修复。祝勇在书中写道:“为了减小地基的承载力和墙体自重,营建者有意加大墙体下部与地基的接触面,从而减小墙体对地基的压强,同时,由墙体下部逐渐向上收分,以递减墙体厚度,降低墙体自重,避免墙体外倾;宫殿任何一个墙角的横切面,都必然是一个直角,而所有直角的顶点,又必在一条直线上……几何学转入中国是明代以后的事,然而,早在公元前2世纪,雅砻王统第一代赞普聂赤赞普时期,藏人就凭借自身对世界的认识修建的雍布拉宫,证明中国石构建筑的技术在2000年前就已成熟。”
公元7世纪后,雍布拉康逐渐演变成了一座佛殿。据王毅《西藏文物建文记》记载:“殿内中塑三世佛,北壁为松赞干布、赤松德赞两王像,南侧壁塑文成公主、尺尊公主坐像。在两边塑像之外,北塑吞米桑布扎立像,南塑禄东赞立像。藏桑布扎之侧还塑有文殊像及长寿三尊像,在禄东赞之侧,则有木制神舆。造型极精美,塑法浑厚朴素。如释迦面部宽而短,眼较狭长,两耳偏上,这是西藏早期雕塑手法特点。”这些历史人物,被幻化为与神灵一样崇高的位置。他们是宗教与权力的综合体,被供奉为神,由此可以世世代代被人瞻仰。但毕竟身体只是一张皮囊,不能永久完好保留。历史重大的人物被视为精神图腾,需要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于是,塑像的出现合乎人心。“它们担负着与今天的明星画像类似的功能,只不过后者更倾向于审美,而前者更像是意识形态的替身。从此,领袖的身体以高高在上的方式深入到民众中去,完成政治意图与民间冲动的完美结合。”
在雍布拉康的山脚下,不少藏族妇人在卖经幡。我从中走过,便被一个藏族小男孩扯住了衣袖,那双清澈透光的眼睛,看了我一眼,又看看手里的经幡。脸上的高原红,如同风中飘扬的五彩经幡般朴实无华。他似乎想表达什么,但不知道是羞于启口,还是语言不通,他站在我面前,略显窘迫。我用眼光询问他的用意,停顿几秒,见我准备转身,洁白的牙齿裸露在阳光里,闪闪发亮。他用一句藏语“咕叽咕叽”(求求你),我已经明白他的意思,周围卖经幡的藏族妇女在一旁解释道:“帮他买一叠经幡吧。挂在雍布拉康的山上,神灵会保佑你的。”我看到他眼神里的渴望,从他的生涩看来,应是刚刚学着卖经幡。他的表情,极为真诚。所有的心事如同写在风马旗上的经文,让人一目了然。
最后,我买了一叠经幡。在雍布拉康旁,五颜六色的经幡挂满了山头。五彩经幡是神灵嘴里不经意间遗下的圣言,传递着天堂与人间的互译密码。每一个朝圣雍布拉康的藏民,兜里总会带着一叠五彩经幡。挂在最高的山头,随风飘扬,舞动经幡之时,相当于念经一遍。
经幡又叫风幡或神幡,藏语为“隆达”,人们更习惯称之为“风马旗”。“风马”的确切意思是:“风是传播、运送印在经幡上的经文远行的工具和手段,是传播运送经文的一种无形的马,马即是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