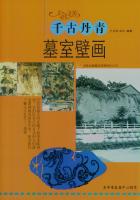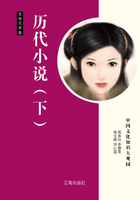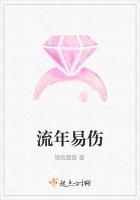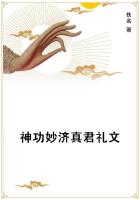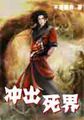冯骥才对于古老建筑的维修有过如下阐述:“对于古老建筑的维修,历来分为两种方式,也是两种观点。一是整旧如新,即粉饰一新;一是整旧如旧,即在修整中尽力保持古物历时久远的历史感。前一种方式多出于实用,后一种方式则考虑到古建筑蕴含的历史和文化的意义。古人常用的办法是推倒重建,或者添砖加瓦,换门换柱,壁画重绘,雕像重刻。这办法美其名曰‘旧物重光’,实际上就是现在所说的整旧如新。 ”没有想到,现代人依旧无法摆脱古人的意识,依旧在整旧如新。他们文化意识的眼光还停留在远古时代。整旧如旧的方式,似乎很难得到城市建设者的认同,所谓的整旧如旧只加固古物的结构,使其牢固耐久,但对其古老面貌原封不动,甚至加倍珍惜那些具有历史感的痕迹与细节。这样,不仅古迹得以保护,历史也受到尊重,被摆到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位置。整旧如初。整旧如新是消灭历史;整旧如旧是保存历史;而整旧如初是回到历史潮流原貌。
一座城市的价值,在于一种空间转换价值。如果一切原本的事物都被篡改,一切古老建筑都被铲除,那么一座城市的记忆将很难搜寻。在一切因素之中,建筑是相对比较稳定的因素,以一种存在并活着的方式,展示一个城市独特的文化气息。时间的远去,很难窥见。空间的建筑,为我们设置了一个进入历史的通道,让我们看到一座城市最生动、曲折、富有生命的情节所在。于是,保留古老的民居是多么的重要。历史需要实在的见证者,需要遗存。建筑无疑就是最好的见证者。建筑提供的实在场所,比一切历史书上记载的生硬文字,更显得有力。五百年的日喀则,关于它的城市历史,我只在旅游书上获悉。但很难在视线的范围之内,作为身在现场的目击者读懂这座城市。
在一间商铺里,还能买到当年“文化大革命”的宣传画。那些斩钉截铁的口号,将一切旧的事物都认定为恶魔,誓要把一切过去的东西都焚烧消灭掉。传统的事物,都被描述为阴暗、落后、愚昧的。人们恨不得快马加鞭,超英赶美。这种画报,因为年代的久远,当年的0.8元,现在已经翻了十倍价钱。终于在与老板的讨价还价中,我买了三幅“文化大革命”的宣传画。现在的商人知道历史遗存的珍贵所在,并千方百计的找到一些古老的东西来赚取一笔。但我所不解的是,城市建设者似乎太过急功近利,只重视了面前利益,在城市规划中,往往看不到长远历史的价值所在。犹如“文革”时期的洪亮口号,以冠冕堂皇的理由,大肆屠杀古老事物。
这条风情古街,专为游人而建。于是,走在这样的街头,满目琳琅的商品,各式各样的商铺林立,我亦不感到起劲。我所追寻的日喀则风情,不在这里。它应该是九曲回廊处,在一条看不见的巷子尽头,有酥油的芬芳,有戴着老银饰品的藏族妇女,有美丽的张大人花,有阴暗的灶头,有呢喃的藏语,有转经的老人坐在门口晒太阳。
拉加里王宫——欲望的宫殿
一座超过七百年的宫殿,一个挥斥方遒的王朝,时间凝固在空间里。当我迈上拉加里王宫的第一级台阶,仿佛掀开了一本厚重经书的第一页。这座庞大而复杂的宫殿,形如迷宫。每一间房都连接着另一间房,每一间房的入口,同时又是出口。永远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符合藏族人根深蒂固的生死观。
七百年前的王宫和村落景观,对我而言形同迷宫,它悠久的历史深度使我的旅途变得焦虑不安。据史料记载,吐蕃王朝灭亡以后,西藏经历了近400年的分裂割据时期。公元12世纪,由于战乱被迫不断西迁的吐蕃王室从上部阿里返回时,在曲松一带建立了一个小王朝,建造了一座名为“加里”的寺庙,并在此修建宫殿,行使地方统治权。从此,这一吐蕃王室后裔便以“加里”为名,并冠以“拉”字,形成了象征权力与荣耀的“拉加里”姓氏。该王系曾在如今的西藏山南曲松县一带逐渐形成并迅速发展,历经萨迦王朝和帕竹王朝统治时期,仍保持着相对独立的地方统治特权。直至西藏民主改革之前,拉加里王系还统辖着拉加里、桑日、加查、隆子四个宗方圆百里的广大地区。据说,当年拉加里王去拉萨朝拜,西藏政府要派四品官员去拉萨河渡口迎接;会见朝拜达赖喇嘛,拉加里王的座位比藏地最高统治者也只低一层卡垫的高度。
为便于统治,拉加里王系的统治者在今天的曲松县南侧高台地北缘修筑了新的拉加里王府宫殿。王宫北临河谷,远远看去仿佛高置于山顶,有一股王者君临天下的气势。拉加里王宫遗址现存建筑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建筑藏语称“扎西群宗”,始建于13世纪,现存最高为12米的宫墙残段和南、北大门;中期建筑藏语称“甘丹拉孜”,建于15世纪,为拉加里王宫遗址现存主体建筑,由王宫、仓库、拉康(宫殿)、广场、马厩等组成,原为5层,现存3层,尚残存部分壁画;晚期建筑称“夏宫”,建于18世纪,现存部分为一基本完整的院式宫殿。拉加里王宫遗址基本保持了原建筑的布局和结构,融合了汉族的建筑风格,在西藏王宫建筑中极为珍贵,亦是研究西藏地方历史、建筑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拉加里王族的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其属下的56个比较富裕的家庭,拉加里王从这些家庭里收差税,包括农畜产品、矿产和一些地方特产等等,所收的产品有100多种,甚至漂亮女子也可以作为王宫的差役,连同她的父母也一起进宫支差。王宫直接管理的牧场有25个,每个牧场都有100多头牲畜。牧场一头牲畜都不杀,所以叫放生牧场。拉加里王吃的肉由辖下的差户拿粮食或钱去藏北换取。
王府握有该地区的控制权。王府可以制定法律、设立监狱、打造刑具、判决案件。我曾看到在拉加里的府宅院门两边,各挂一根直径6到7厘米、长1米多、蒙着虎皮的法棍,用作震慑农奴。拉加里像多数贵族一样,常年住在自己的庄园里吃喝玩乐,生活奢侈,并不过问具体事务,而是命其亲信,设立强佐康(管事房)掌管领地范围的一切行政、财务、司法及庄园的大小事务。拉加里法王在山南拥有桑日、加查和隆子4个宗(县),占有19个庄园、2000多户农奴。 此外,还有15个直接为王室服务的手工业作坊,400名朗生。
研究拉加里家史的德国学者卡尔斯顿,为人们提供了一些更鲜为人知的史料。他写道,拉加里家族通常是藏传佛教宁玛派的信徒,但他们习惯于在自己的家族中有一个“古辛”家庭,这个家庭信奉西藏的原始宗教——苯教,他们声称这是从松赞干布时代一脉相传下来的。他们,并且只有他们能在赤钦和这个家族的其他成员的葬礼上充当司仪。当这个家族的头领去世时,需挖一个陵墓,并用银子围裹,就像用金子围裹的达赖喇嘛的那些陵墓一样。
公元18世纪初,在清军入藏驱逐准噶尔部的战争中,拉加里法王因协助准噶尔军与清军对抗而在其后受到西藏噶厦政府的严厉制裁,被割取了部分庄园与土地,并由噶厦政府加强了对其政治上的控制。从此,拉加里王系的统治权利才日趋衰退。
拉加里王宫记载着一个王朝的辉煌与覆灭,在复杂的空间里,多组名词出现在我的脑海里:王爷、妃嫔、官吏、少爷小姐、差巴朗生、战争烟火、勾心斗角、权力更迭。每一组词语里都可以阅读到那个时代的欲望、不安与茫然。历史在这座宫殿里已变得模糊,支离破碎。它越来越成为一种虚拟的空间,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中。
由于年代久远和自然侵蚀,拉加里王宫文物古迹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险情,为保护文物遗址,2006年,自治区相关部门将拉加里王宫保护维修工程列入西藏“十一五”重点文物保护工程向国家申报。2007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西藏自治区“十一五”规划项目方案》,批准实施重点文物保护工程,计划安排2050万元实施拉加里王宫文物保护工程。国家总投资2050万元的修缮款中,其中1052万元用于一期修缮。范围包括复原拉加里王宫主殿、红楼、大仓库、点心房、马厩、广场、夏宫等。据山南文化局局长白玛次旦介绍:“拉加里王宫的文物保护工程内容包括主体建筑的保护维修、清理非王宫设施、清运场地垃圾、修补卵石广场、通过加固工程继续保持遗址的现有状态、寻找并疏通王宫地下通道、山体边坡加固。”
据白玛次旦局长介绍,在整个维修过程中,将严格按照古建筑维修“修旧如旧”的原则,如特制传统的牛粪砖和购买了“白玛草”用于墙体修缮。并从附近的寺庙找回了原本属于拉加里王宫的梁柱和斗拱。山南文化局和文物局严把质量关,科学组织、周密安排、紧密配合、精心施工,确保拉加里王宫保护工程按期完成,保质保量,确保文物安全。
目前,拉加里王宫已经完成了主体建筑的外部修缮,内部修缮是一个当然困难的过程。拉加里王宫的一处即将坍塌的墙体上,表现法王祖宗三代造像栩栩如生又岌岌可危。“这是西藏重要的‘艾支派’壁画的代表,修复壁画是我们在修缮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难题。”山南文化局局长白玛次旦介绍。
拉加里王宫的保护和开发工程,正热火如荼地进行。白玛次旦局长说:“我们将在拉加里王宫开设王室生活体验中心、新旧对比教育中心、拉加里文化交流中心等。此外,关于拉加里的历史、民俗、传说资料已收集完备,今年年底这本恢弘的历史之书将出版,呈现在大家面前。”
一座城市的价值,在于其空间转换价值。在变动的时间里,建筑是最稳定的因素,它是历史的器皿,是时间的量具和物质载体。人们在拆除房屋的同时,也拆除了构成时间的逻辑关系。使城市不再处于一个时间链条上,而永远成为一个断点,孤立无援。所幸,拉加里王宫的修缮工作多年来得到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在保护中合理开发,在合理的开发之中进一步保护历史文物。保护拉加里王宫,这不仅仅只是政府的职责,也是每一个人应有的文化自觉。
拉加里王宫是整个山南曲松县的腹部,五脏俱全,它在历史长河里闪烁着耀眼的光。多年前的阳光和现在一模一样,我把手伸向蔚蓝的天空,我多希望触摸到一张布满皱纹的脸。
牧民的帐篷:流浪的开始或结束
千百年来,牧区牧民大都择草而牧、择水落帐,没有固定的居所可言,所以,牧民所拥有的房子便是牦牛做的帐篷。帐篷以结构简单、支架容易、拆装灵活、易于搬迁取胜。其形状有翻斗式、马脊式、平顶式、尖顶式等。在迁徙频繁的游牧生活中,藏族牧民的“家”是驮在牦牛背上的。帐篷,是牧民的根部,是他们流浪与漂泊的开始或结束。从一个草场到另一个草场,牧民和牛羊一样,在季节里迁徙。那曲的日光,在地平线向右四十五度的地方。羌塘草原枯荣一季,雪山终日凝望。牧民们放牛喂马,织毛毡生娃,东南西北随风安家。
羌塘草原常见的帐篷就是黑色牛毛帐篷,平面呈不规则的方形或长方形。帐篷料有25厘米宽,长短由帐篷的大小而定,然后把若干幅料缝成两片,两片相接的缝隙有60厘米宽,顶部当作天窗,相接的两边都用白色帐篷料镶着,这样两片相接以白对白。牧民忌讳黑对黑接,因此,帐篷门帘是白色的。
还有一种帐篷是白色的。大都是用羊毛织成的。这是富裕牧民在小范围内机动游牧时经常使用的。到了春夏之际产羔时当作羔圈,防止被冻;还有到盐湖驮盐等一般外出时携带,既保暖又轻便。一望无际的原野,白色的帐篷,牦牛如群星散落。牧民们在风里张开双手,闭着双眼,聆听遥远空间里,传来天地之间的呢喃。又到了牧场换季,牧民们早已习惯将身体寄放于草原,从一顶帐篷,抵达另一顶帐篷。你长久没有与人说话,风的语言便是你原始的母语。你从不知道吉普赛人的存在,但你身上遗传着流浪的血液。一个长发飘逸的牧民男子,长时间目送最后一朵云翳的消逝,不经意间,两行苦涩的泪水,像一首佚名的诗篇失散于空荡的夜色中。羊群和牦牛,是牧民如浮萍的宿命依附在世间的唯一凭据。
在作家扎西达娃的小说里,牧民能听懂牦牛和季节的交谈。对此我感到深信不疑,因为牦牛是大地系在皮绳扣上的魂。牧民的日常生活被劳动填满。放牧、迁徙、耕种、贸易,成为藏民族史诗里的固定章节,千百年来未经修改和润色。一顶帐篷是家庭的基本单位,在寒冷的冬季,牧民们在帐篷里烧着牛粪火,酥油和奶酪的香气,瞬间充溢其中。牧民的生活,因牛羊和草场而流浪。他们的吃喝拉撒与天地自然共呼吸,他们以牛为主要食物,以粪为燃料,为人取暖和煮熟食物。在牧民身上,我看到天人合一的梦想,在广阔无垠的草原上成为最寻常的生活。吃喝拉撒,生死歌哭,畜生不留下粪便,人类不留下肉体。
羌塘草原存在于每一个牧民的身体内部,成为他们为此流浪的世界。每一顶帐篷,都是一个微型的宇宙中心,盛放着盐巴、经书、爱情和根深蒂固的生死观。谁也不知道,牧民与羌塘草原构成一个无限的世界。这是一个无法告人的秘密:他们与羌塘草原相依为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