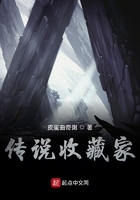钟小念一出病房,倚在门外的男人就主动到近乎霸道地牵起她的手,将她拉到病房外的护士站。
还没走近,就有护士殷勤地从护士站里跑出来,鞠躬,打招呼,“院长好。”
他拉着她径自走进去,让她在座椅上坐下,才对跟在身后的护士长吩咐道,“替她额头包扎一下。”年轻低醇的声音,却独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威严。
很快有人推来了器具车,护士长亲自上阵。
不知是不是太久没有享受这种特权待遇,钟小念心中有些抵触。坐立难安之中,护士长已经用沾着碘酒的棉签替她清洁伤口。微凉的刺痛毫无征兆地传来,她不自禁轻抽了口气。
放在肩上的手忽然一松,“给我。”他走上前去接过护士长手中的碘酒和棉签棒,就势蹲下。
看着护士长不安的脸,钟小念极难为情。她本就不再是个娇气的人,更何况刚才那一下根本算不得疼,只是她一时分了心罢了。
温热的手托起她的下巴,他摆弄着手中的棉签棒,忽然抬头眼光一落,饶有兴致凝着她微红的脸不敢用力呼吸的模样。
钟小念实在不喜欢这种被动的局面,她咬了咬唇伸手去拿他手上的物什,“你给我,我自己来就可以了。”
“别动!”
他微皱起眉按住她的肩,神情严肃而认真,“不好好处理,你额头没准会留疤,到时候你别哭鼻子怨我。”
“我哪儿有。”钟小念窘迫地嗫嚅道。
“嘘,别动。可能有点疼,忍着点。”
棉签棒在修长的手中仿佛有了生命似的,他半蹲在她跟前,前倾着身,竭力将手上的力度控制得最轻,时不时还低下头往伤口处吹气。
他的鼻息如羽翼轻扑在脸上,身上TERRE的淡醇香味将她笼罩得有些透不过气来。
这到底算是什么事儿呢?中午的时候她特意躲开他,却怎么还是被他找到了。
“好了。”他徐徐审视了番,似是松了口气地一笑。揉揉她的头,细声叮嘱,“这几天吃东西要留心,有酱油的、辛辣的食物不要沾。”
时隔几年,曾经安静内向的男生也长成了温柔内敛,却又适时霸道的男人。
钟小念不自在地笑笑,“谢谢你,林奕扬。”
“哦?”他仿若惊讶地挑起眉,眼中溢出丝玩味,“还记得我?”
“育才中学三年二班,和我一年考进S大医学系,林奕扬。”钟小念看着面前眉目含笑的男人,一字一字清晰地说。连她都不知道,竟然会记得这么清楚。
很小的时候起他就会被他爸带着到钟家来做客,但是他都很少说话总是安静地坐在一边,而她性格顽劣最看不上此类只会读书的呆子。所以尽管他们每年都会见面,但真正有交集却是开始于高二那年暑假。
为了能靠近靳慕白,自初中开始就门门功课高挂红灯笼,稳坐年级倒数前十的她立誓要考进全市高材生挤破头都想进的S大。本来家里早计划好高中一毕业就送她出国,等她几年来第一次想认真学习却茫然到无从下手。最后听闻同她一届的林奕扬成绩优异,她便让她爸委托林奕扬他爸逼着林奕扬来给她补习。
林奕扬到她家给她补了整整一年的习,最后她低空飘过S大的录取线,而林奕扬以全市状元的身份进了S大的医学系。两人同时接到通知书那天她气得牙痒痒,明明林奕扬也没有比她用功多少啊。
林奕扬一定是很不情愿给她补习的,那一年他一直对她不冷不热,除了讲题便不再多说话。可就在接到通知书那天,他忽然做出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就是因为那件事情,中午她看见他时便下意识地想要逃走。
收到通知书那天,她很开心,庆祝了一通直到晚上的时候突然想起他来,便第一次打电话给他想要说声谢谢。电话才接通,他说他在她家大门外,希望她能出去。
她没有多想就走到大门边,只看见满地的玫瑰和摆放成心形的蜡烛阵里的林奕扬。
微醺的夏夜,玫瑰,蜡烛,爱心……他向她表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