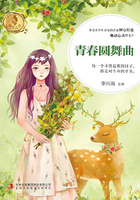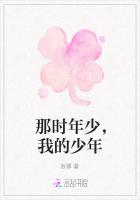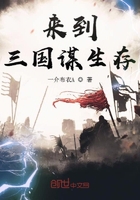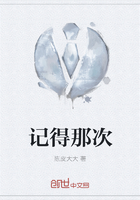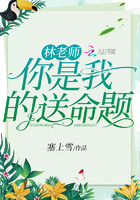茶马古道不仅是世界上自然景观最美丽的风景线,而且是中华文化的大走廊。在茶马古道上,几千公里的沿途,看见数不清的寺庙,往往令人迷惑:这来自印度的佛教,为何在中华大地如此的兴盛?后来才从唐宋八大家韩愈的坎坷经历中得知,在上千年间,佛教是得到了统治阶级的大力支持,才得以如此兴旺的。名气大如韩愈的人,在唐朝已经官至司法部副部长,就因为不赞成唐宪宗迎接佛骨,便遭遇了“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不过话说回来,这佛教既然在民间有众多的信徒,总还是有它的一些原因,也还是要尊重民众信教的自由。
大邑县,也算是川藏茶马古道的一个驿站,山后就是属于雅安的地界,此地至今还有大熊猫在山间走窜,这些毛茸茸的小东西一会儿在大邑西岭雪山,一会儿在雅安苗岭一带,弄得两地都说自己是“大熊猫故乡”。此地有一处藏传佛教的古寺,名叫白岩寺,是一处清静道场,没有许多寺庙的那种商业气息,甚是难得。这白岩寺建于一处巨大的白色岩石之下,因之得名。十里之外即可见一片白色巨崖,壁立天下,如有阳光,反光极亮,甚为壮观。我曾经好奇地爬山到白岩顶端,仔细观察过这片白岩,其实在近处看并不是常见的白岩,而是许多白色的拳头或者拇指大小的鹅卵石凝结而成的板块,颗颗碎石都有着汉白玉般的朦胧美,虽然并不算剔透。在光线的作用下,仿佛就是一大片白色岩石。这种地质结构叫沉积岩,与成都平原在上古之时是一片汪洋大海相符,由于沧海桑田的变迁,地壳将海底的石子掀上了高山。
白岩寺的建筑群依山而建,据说在东汉永平十六年,由印度高僧迦叶摩腾、竺法兰二尊者创建,是汉地唯一的藏传佛教寺院,有独特的藏地风格的转经筒,还有极为精致的印度佛塔。寺庙间银杏参天,多由明朝僧人所种,秋季满山银杏叶一片金黄,是画家和摄影师喜爱的地方。白岩,古寺,金叶,白塔,转经筒,古道,寒鸦,山溪,野鱼,竹林,蓝天,高僧,构成了一幅蜀山秋旅图。
我们来到白岩寺,一不是为了赏景,二不是为了画画,而是为了吃一顿饭——一顿素餐斋饭。跑个百十公里路程,就为吃一顿饭,的确是有点怪癖了,但这不是普通的一顿饭,是一种文化体验,精神探索。当时正值盛夏,公路旁的水稻一片翠绿,就像铺上了一望无际的绿色地毯,每当看见这种景象,我就会想到北方人是没有这种眼福的。这绿色地毯整齐得就像割草机剪过的一般高,一缕缕清香从稻田里随着热气升腾起来,这种香气是米在锅里的那种香气的时光倒流,是人在赤婴之初的混元之香。在绿毯和稻香之间,抬眼望去,便可见隐隐约约的白岩在山间壁立千仞,白岩之上是葱茏的树木,再往上看是蔚蓝的天空和朵朵的白云,虽不似茶马古道高原上的寺庙巍峨,但也是颇为神圣。
佛教中的吃素也叫吃斋,和尚尼姑必须终生坚持。吃荤是佛教的大小乘戒律和南北派所共同禁止的。佛教中的荤还包括蒜、葱、韭等气味浓烈的东西。佛教从南朝以后,开始实行《梵冈经》的规定“不得食一切众生肉,食肉得无量罪”。这一教规又是由于皇帝的推崇,由梁武帝召集诸沙门立誓永断酒肉,并以法令形式告诫天下沙门,若有违反则严惩不贷。由此开了中国佛教素食的先河。素食的初衷,除了大慈大悲,不杀生之外,还有避免五辛多污秽、增淫欲的原因。
除了宗教方面的原因,近世的医学研究发现,素食对于人体的确有诸多好处。高脂肪、高蛋白已经成为现代人的致病因子,有医学家提出动物蛋白在肠道内腐败会污染血液。素食已经成为风行欧美的健康新风尚。
我们朝着白岩寺进发,这里并不似一般寺庙汽车可以一直开到山门。停车之后需要沿着一条古道石阶步行几十分钟,才能到达寺庙。从古道石梯的磨损残缺可以判断是唐宋以来的吧。道旁的杂木野花,小溪流水,竹林幽篁,夏蝉高嘶却也喜人。
庙里的食堂叫斋堂。院子里有一处水井,并不像一般的水井从地下挖掘而出,而是在岩壁之上挖进一个大坑,有泉水从四壁浸透下来,盛满井池。池中之水清澈无比,如不仔细看,仿佛无物一般。能长饮此泉,高血压心脏病不治自愈。
我们向斋堂的义工居士提出欲吃斋饭,希望方便一二。初始,居士有些犹豫,我心里知道这是因为山上的食物来之不易,这里又是清净道场,一般不会让人到斋堂搭伙。这斋堂门口就是一条索道,大约有好几百米,一直延伸到山下,是寺庙运送给养的运输通道,阳光下,高高的索道看得人头晕,山下起点处的一个蓝顶小屋,仿佛是一只杯子放在那里。不过,佛门人士慈悲大度,不会凌厉拒人或者讨价还价。居士让我们稍等,待众师傅饭毕。
斋堂名叫“五观堂”,四壁洁白,餐桌整齐,木凳直列。据说从前较简陋,5·12地震受损重建。众师傅坐成一行,清风雅静,神态肃穆。佛教僧众一贯沿用印度修行者的习惯,沿途托钵乞食。现在我等一干人反而成了修行者。僧人即使在寺院里用斋,也有过堂仪式,将进食视为重要的修行方法。这其中的观想和祝愿,是最有意思的。观者,看也;想者,想象也。白岩寺的僧人通过口诵真言,眼观斋食,想象七粒米可以变成四十九粒米,四十九粒米再变为无量无数的米,然后可以“生饭”,体恤饥苦的众生,愿他们同得饱满,不受饥寒。这种思想境界,是佛教的精华,在此之前,我是不太懂得这种境界是如何深入僧人的思想的,今天才明白了,多年以来,如果一个人每天都在吃饭之前观想粮食,体恤众生,自然会有思想的结果,自我修行的结果自然也会比灌输的结果根深蒂固。
僧人进食之前,不仅要体现慈念众生的菩提之心,进食时尚需心存“五观”。佛陀教导弟子在饭食之时需作五种观想,记录于此,亦可启迪:佛家弟子不可平白受食,要记功量德。不可作践饭粒,粒米维艰。不可计较食物而存好恶之心。要思忖自己的德行,是否对得起十方善众的供养。食物只是滋养慧命的药物而已,不可恣意贪食。在进食之时有了这五种观想,进食就成为了一种修炼,天长日久,自成其果。这是一种人对于食物的态度,也是在思想中认清物质与生命和意识的关系。每餐如此,每口如此,天长日久,水滴石穿,僧人对于饭食,便有了既定的宗旨与认识。
我们伫立在斋堂之外,眼望着僧人默默地用餐,一言不发,目不旁视,其实他们的头脑里正“初即观食,然后观身,再则观心”。僧人食毕,会对施主给予祝愿。一般的内容是祈望众生获得利益与安乐。无论是托钵乞食还是寺院素餐都是如此。我在观看和了解了白岩寺“五观堂”的斋饭,并且亲身体验之后,才懂得了吃饭也是一种思想活动,是人的一种德育活动,是人的一种向善机缘。我们一天三顿饭,却忽略了;我们一年365天,却忽略了。“举箸常如服药”的古训更是被遗忘了,所以多了许多“糖尿病”、“高血脂”;多了许多“筷子一提,可以可以”;多了许多“感情深,一口吞”;多了许多公款挥霍,饕餮暴食;多了许多淡忘盘中之餐来自于十方民众的供奉等等。
这一顿素餐斋饭我们其实吃得简单:白米饭、馒头、四季豆、豆腐乳、米汤。按素餐习惯先吃三口白饭,不使五味杂陈,始终缄默不言。但是由于也有了一些观想,多了一些愿望,在口味和精神中对于这素餐的感觉便大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