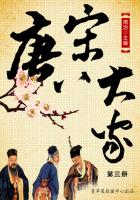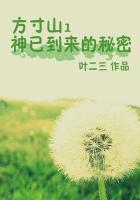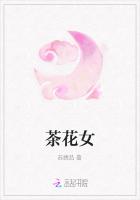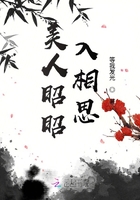可推开寺门,见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年代久远的庙宇个个闭锁,院落弥散着冷清衰落之气,看来好久没住出家人了。虽然这里申报为国家森林公园,但荒废颓势的寺庙建筑明显疏于管理,缺乏整饬。我记忆中的几棵树也没看到:门口的一株高大的乌桕树,院西南的一株樱桃树,还有一个庭院里的小水杉,几年不见,应该成材的。这十多年里,不知发生了什么,是谁涂改了记忆的图画?
儿子那年留的一张照片:正在喝着饮料,露出小得意的表情,背景是密密的修篁。竹园并不大,长势却好,竹子粗实冒绿,那种内部生长着的油绿往外一个劲儿洇染,血脉正旺,园里冒出的笋似小孩子的襁褓那样粗大,长出来的竹子个个英气逼人,真是一块适合长竹子的土地。竹园中间有条向山攀行的小道,穿过一抹翠色。
竹园是白云寺重要的点缀。提起白云寺,知道的人会说,里面不是还有一个竹园吗?历史上竹林七贤曾在辉县百泉等地活动,他们“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喜欢将饮酒吟诗、文学创作活动搬至竹林,可见名贤与竹林是相知相惜的,他们看见的不仅是竹子,还有他们的心灵显影。白云寺离百泉仅几十里,听说这一带就有竹林七贤的活动足迹。
可我们没有古人雅致旷达,会选择在幽篁里弹琴长啸。我们的到来只不过是重复,这重复却也如此短暂而飘忽。
但现在的竹园着实萧条荒芜。那黄瘦的竹子气象也不如从前。
还有,那时的香火好像很旺盛,香客不绝,卖小吃的,卖当地特产的,路旁皆是。
身边的小王说,现在这里缺乏的是僧人。旅游局一直想和宗教局联合,引进僧人,恢复香火。但这里又是国家森林公园,林业部门不允许。
看见了那棵大殿前存活了百余年的挠痒树,我照例上去体验一番,挠挠它的枝干,看它的叶子是否晃动。一位朋友说,其实挠痒树就是紫荆,又叫百日红,公路上美化经常栽种它。最后还补充道:我查过资料的。我听了颇为怅然,有些失落。因为我从小就听说白云寺好多传奇的故事,其中就有这棵充满灵验的“会动的树”——挠痒树,令少年的我神往不已,此时却被朋友一番话语破解得神秘全无,天上的仙女忽然下凡成身旁的村姑。神秘即美,而有些美是不能被现实拆解的。我的村庄离这里有几十里之远,但这里的一切早已是一个传说,在这片地域流传。小时候就听老人们念叨:白云寺,好景致,玉石奶奶挠痒树。
老人们说的玉石奶奶为白云寺的镇寺之宝,是一座汉白玉雕的菩萨像,位于寺院的奶奶殿内。康熙二十八年,由一个浙江人敬施,像高四点八米,通体为一块精美的汉白玉精琢而成。但几个大殿年久失修,常年由一把卑怯的锈锁掌管,就别提玉石奶奶的下落了。
向西穿过一个角门,来到一座小院子,房子虽旧,倒十分清幽,让人想起那句“应怜屐齿印苍苔”的诗句来。门前一棵十几米高的白玉兰引领了众人仰望的目光,但见枝叶茂实,一指长的辛荑处处可见。几位朋友不禁联想,这里的环境十分宜于读书写作,是建书院的好地方。人气太盛的景区,喧嚣浮躁,幽寂之所反倒是静心研读之处。
在白云寺的后坡上,我们见到了元好问所书塔铭的“通悟禅师徽公塔”。徽公法号澄徽,元好问与他有一面之交。元好问记载:“……度不可终辞,因就师像前问师,能为吾说法否?寂听良久,捧手曰,法王法如是,乃退而为之铭。”这是元好问写塔铭之前的精神活动,颇有几分神秘色彩。碑文叙述了徽公禅师生平、经历和声望。
明代李贽三十岁时,出任此地教谕,这是一位晚年著书讲学,对当时的假道学等进行强烈抨击,最后被迫在狱中自杀的明代思想家和文学家。从他的《白云寺探胜》《偕诸友避暑白云山中》《对弈》等诗题,诗句“早晚离尘事,谈空向野僧”和“行吟出树下,云在意俱闲”可体会到,李贽经常与同道好友上山寻幽,饮酒对弈,作诗论文,他的诗作被题在白云寺大殿东角门壁,寺与诗相得益彰。
一二百年之后,清乾隆帝曾巡游至此,为寺院题“白云自在”一匾,悬挂在寺门之上。但如今乾隆的御书已不知何处,寺门现今的“白云寺”匾额,是当代著名书画家侯德昌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手迹。
寺门前新筑十来米高台,往下望,暮色中依次而立着几株唐朝的千年银杏。这样的隔绝,让人觉得不妥。记得以前是个土坡路,从远处缓缓而行,先入视野的便是这几株茂盛粗大、需几人合抱才可量度的唐银杏,观瞻一番之后,才入寺门。
八年前,寺庙一座元塔遭劫被盗。此塔身造型优美,雕刻细腻,堪称元代石雕艺术佳作,属国家一级保护文物。后虽被公安部门破获追讨,那部分仍被保管异处,古塔至今还是残身。望之,有种无处归依之怆然。
千年古刹,古塔成林,或砖砌,或石雕,古塔的历史风韵掩映于山林中。一塔一人,想来那高僧圆寂后的灵魂又会因为佛塔的残缺而不安了吧?阿弥陀佛。但佛又是慈悲为怀的,已经超度的灵魂还会责备人间的恶吗?
暮色中,匆忙在竹林、山门留影。新结识的朋友小王说,附近的一座山峰上还有刘伶醒酒台。可惜天晚了,今天没机会看了。刘伶著有《酒德颂》,文曰:“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想到这里,竟觉得“唯酒是务”的刘伶至今还醉卧在那块平坦的巨石上,世间没有什么能将他唤醒。
盘桓回望之间,我听见竹林七贤振荡山林的声音在呵呵笑我,听见元好问一根竹杖叩访高僧的闲逸,还有李贽结友吟诗、抨击世相与封建传统的快意畅谈,他们心无藩篱,胸无戒律,阅高山流水,看白云自在,抒千古胸臆,是真正的精神高蹈者。
而我们一行浮浅的身影则很难融入其中的白日、夜晚,其中的风雨雷电。那竹园,那佛塔,那唐银杏,才是真正的传奇,今人的行为早已隔膜了古时的风景。
但我暮色苍茫中的神色分明带着沉湎与不舍。
注:文中所写白云寺位于豫北辉县市境内,在距市西三十五公里的白麓山下。
郁愤的达夫
最近在图书馆借了一本《郁达夫的女性情感世界》,郁达夫与王映霞之间的情爱恩怨是着重的一部分,读毕让人喟叹良久。
郁达夫的作品即是他的精神史,他在文字中剖析了在日本东京的留学经历,于异国旅馆的寒灯下,或是街头的徜徉中,弱国子民的悲哀、男女间情欲的纷乱便雾一样漫上心头。除了他悲苦压抑的心迹,他在日本的嫖,在上海的嫖,他都告白于众。
郁是这样的一个男人,并不隐讳自己的作为,有人说他是暴露狂、神经质。暴露个人是种真实而奇特的行为,但也许于其他方面并不可爱。
比如对待心爱的女人,往往使女人受不了,结果是,适得其反,女人的心愈加远离,终至无觉。郁追王映霞而不得,便骂之,并写进日记中。写进日记中,作为私语藏匿不见光就算了,还要发表,王发现后与他吵闹。发现王与情人的瓜葛,便登报宣扬,殊不知,这既是王的丑事,也是自己的丑事,可他考虑不周,一怒之下就是公诸社会,去暴露个彻底。
暴露可以泄一时之愤,却不能解决实质问题,反而使两人的问题更加剑拔弩张,更加不可收拾。既然不想离婚,何必要把事情闹大,何必要争个你粉我碎。郁的头脑发热起来可不得了,忘了王可是他千辛万苦追求来的。
才人追求佳人,尤其是贫寒的才子情种,付出的代价便是成为灰烬。中国文坛自然还有别的例子,比如浪漫诗人徐志摩,因为要兼职,多挣些家用给陆小曼过优裕生活,行踪便仓皇些,因赶时间的缘故想到搭乘飞机,没料到落得个机毁人亡。
郁在追王时,对妻子孙荃及孩子久拖不见,等于抛妻离子。一场疯狂的恋爱燃起的烈火总是不管不顾,而家人感受的却是亲情的酷寒,从此心如槁木的妻子孙荃断荤茹素,成为虔诚的佛教徒。
王是名贵花色,郁处心积虑撷其芳心,柳亚子还赠诗郁达夫,称其“富春江上神仙侣”,但神仙侣也渐渐成了怨侣,年龄、性情的差别,环境的动荡,王的貌美与虚荣,都是埋伏的随时可发作的炸雷。再加上郁处理家事的简单,麦秸火动辄即燃,动不动就要登启事,那个时代这种举动也是名士常用的方式,但他暴露癖发作,痛快无余地昭示世人,把家丑大白于天下,可以看出他气恼至极,无措至极,但骨子里是懊丧、恼怒,是爱与恨的交加,是弱者唯一的武器。
不禁感叹,名世的文豪也有可怜处,也有无奈处,一家之主的男人竟狼狈至此,这就是生性浪漫多情男人的际遇吧。
之后便是懊悔,再登道歉启事,承认自己以前是误会,是“神经失常,语言不合”,呼唤王快快回到自己和孩子们的身边。
赔礼道歉,灵魂下跪,想不到一个大作家也至于此种境地。他和王映霞发生了家庭纠葛,郭沫若也从中救火调解,并说“达夫始终是挚爱着王映霞的,但他不知怎的,一举动起来便不免不顾前后,弄得王映霞十分难堪。这也是他的自卑心理在作祟”。
当然,郁的尴尬背后并非空穴来风,后郁怀着悲愤之情写了《毁家诗纪》,郁求得的签诗有“不是有家归未得,鸣鸠已占凤凰巢”,王与许某的关系作了此诗的注脚。而王与戴笠也有类似关系,为避戴的蛇蝎之心,郁被迫远走南洋,而终遭日本宪兵谋害。
阅读的契合
在列车上读陆游的《老学庵笔记》,“东坡在山岭海间,最喜读陶渊明、柳子厚二集。谓之南迁二友。予读宋白尚书《王津杂诗》有云:‘坐卧将何物?陶诗与柳文。’则前人盖有与公暗合者矣。”读至此,心想,自己近来颇喜一位江西散文家亲赠的两本散文集,一本《正版的春天》,一本《内地以内》。
在我从牧野之地新乡迁往商都郑州后,它们亦谓之南迁二友。某种程度上它们成为我的精神私语者,“夜晚的声音”,或是“枕畔的声音”,毫无例外,它们给了我慰藉与参照。
2007年的春天,在思忖新书《彼岸灯花》序言这件事上,神使鬼差,我贸然给他,一位外省的青年散文家打了电话。手机拨通了,一位南方男子的声音,音节短而柔和,我向他说明并表白后,没想到,他竟同意了。
合上手机,一条喜悦的小溪在心头淙淙流淌。他是我经常翘首的才子。早在前几年,他发表的作品就准确清晰地击中了我的心房。他的文字像在河里淘洗过的沙子,洁净湿润,从不拖泥带水,而青春的记忆又带着别样的令人追怀、不忍弃之的伤情。
他笔下的乡下同学常常骑着一辆旧车,跑来和他讨论与生活无关,与精神有关的文学,这是印象中的一个细节。看似普通的述说却似针尖轻微地扎疼了我。因为忧伤和无助,他的同学在文字中寻找慰藉,打捞支撑生命的那根稻草。还有一篇好像是他在广东一家企业时写的,文后的简介还有“经理”字样,写的好像是城乡接合处:垃圾,垃圾中出现的安全套。我常常惊异他对生活的发现与界定,对语言符号奇迹般的运用,就像把沙子淘洗成金子,令人眼前霍然明亮。
因为对另一种关乎精神生活的求索,他离开了那座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城市,同时也失去了高薪,回到闲散而缓慢的内地城市谋了一份文字工作。就这样慢慢记住了他。
他的文字如同琴弦在静夜微颤,看他弹吉他的照片,专注自恋,像一个男孩抱着自己喜爱的玩具。
他的眼睛与耳朵是忧郁的,他眼中含着家乡水波浩渺的鄱阳湖。在他的回忆中,故乡的树叶翻动出无限的美与感伤。而青春有时是狂放不羁的,他骑着山地车在乡下公路上一边奔跑一边用美声高唱《我的太阳》。热爱歌唱热爱绘画热爱写作,对艺术的过分沉溺成就了他。
2007年我请他给我写序时,他看我的简历,知道了我的经历。他说他不赞成为了文学而放弃正当职业。我想,他以往的“漂流日记”中一定也充满了怀疑、茫然与黑夜里悄然发生的惊心动魄。
他曾经写道:“不断地自我否定和勉励使每个夜晚变得动荡不安。回到这个欠发达的中部城市,失去了高薪,却也没有职业上的安全感,全部的希望押在比天空还高远渺茫的写作上,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是在拿亲人的生存安全担保去猜一个也许没有谜底的谜。”类似的句子就是我那时病态中要寻找的良药,精神饥馑中要吃的食物和慰藉。为什么我们要离开原地,过上这种不确定的游牧生活?我呼吸到了他文字间散发的特有气息。也许是惺惺相惜,它离我的生活如此之近。某种程度上,它就是我的生活我的心迹的翻版。我从他的句子中照出我慌乱的影子,闻到一股浪子飘浮的特殊的呛人味道,它熏染了我的衣衫、脖子、衣下的皮肤,在我脆弱而坚韧的血管里游走。
一如我要依赖的精神鸦片,隔一段要读一读才解瘾。然后长长地呼出一口郁积胸中的浊气。
远去的经典,女人书,都不能映照出我。而他出生、生长、生活的时代,所看的电影、唱的歌曲则可共鸣共享。所以,我可以说,他在酿自己文字的酒,却醉了那路上的客。
他笔下的文字是陷阱,大凡所有的好的文字都具有这样的特质吧。温柔的感伤,在水中浸过的文字,缭绕着他家乡鄱阳湖的水汽,时时把心脏掏出来抚摸它的跳动。音乐从未离开他的生活,文字带着节奏,带着吉他流浪的乐音。
一本《内地以内》,另一本《正版的春天》,他记录回忆了曾经的时代,时代里的温情蜜意,而里面始终有一条他行走的路线,隐约而曲折的心脏奔波过的痛与诗意的行迹。躺下去,侧过身,习惯地伸到床头探摸到它——感受那文字沉醉的袭击。
睡在地坑院
几年前,深秋季节的一次陕县之行,印象最深的是那一带特有的地坑院——窑洞。
一路上,不时可见高高低低的依黄土塬而建的窑洞,它们形成这里特有的民俗风貌。有的尚住着人家,有的看上去已长久弃置,有的窑洞旁则盖着白瓷砖装饰的新房子。土窑洞似面容沧桑的老妪,新房子像刚娶进家门的新娘,两种建筑形式的陈列解读着这个地域的过去与现在。
夜晚被告知,要在离地面六七米深的一个地坑院子下榻。在我从前的居住经验里,这样的“房子”从未见过。我的家乡位于南太行山麓,石材曾是人们建房子的主要资源,而这里则纯以土为材料,以天然穴居为安乐。对照起来,这样的居住体验格外新奇,让人从建筑意义和生存环境上细细将它审视打量。
第一眼看到地坑院,心里便呼作“地下的窑洞”。其时,暮色四合,从一条下行的通道下去,便到了这一方天井。老乡说,我们住的这个地方是由几个地坑院打通而成。现在几乎没有人住地坑院了。
从老乡嘴里,我知道了地坑院的来历。过去,因为当地建筑材料匮乏,村民盖一所房子需要很高的成本,砖、水泥、石头、木头这些基本的东西样样都要从外面购买、拉运,靠天吃饭的村民往往难以负担其中的财力和人力,于是,他们就选择了这种掘地“挖穴”、掏土成洞的方式建“房子”,过着穴居生活。
不言而喻,撇开当地人的智慧不讲,其中隐含着他们生存的尴尬与苦涩,透显着无奈与悲凉,民国期间有解嘲对联云:分明是钱短木料贵,还落个冬暖夏天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