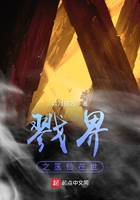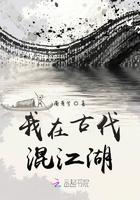人的河流安静地流进流出,每个人都是一痕小小波纹,身上携着一路上的细细风尘,急急地又要跋涉到未知的远方。随身的行李携带着行动的秘密,不管是时尚女人精致的靓包,还是农民工身旁鼓鼓的来自乡村的编织袋。
流动或者出发就像身体内的血液,对于每个人都是必需、必然。出站口的地下大厅里有些空旷,散发着一些体味和被褥的味道,原来有许多人在这里过夜,硬硬的地板砖带给身体的冰凉,不知会不会让他们回想起家里粗陋而暖和的炕头。
身边陌生的脸也是风景,几个美院的学生在给旅客画素描,一个乡村女人拉来自己的娃,让学生给画一画。学生初出道,画得犹犹疑疑,但每一笔都特投入。选择这里画画,人脸的资源可谓丰盛,画艺一定能有长足进步。
有个和我坐同次列车的女孩,几乎让我的目光生出胶液,黑漆发丝,卷翘睫毛,白而无辜的娃娃脸,她对女伴说出的那个地名恰好是我老家的县城。曾经的青春的影子啊,时间仿佛轮回到被时光恩宠的岁月。
很少和旅客聊天,有一次和一个小伙子聊起来,他说在郑州上大学,我马上问:“郑大?”“不,一个职业技术学校。”我立时觉出自己的唐突和冒犯。这个留着小胡子的十九岁的男孩闯过广东、深圳,已是小江湖了。毕业之后不准备回老家了,他说郑州不错,准备在这里干出一番自立天地,颇有男儿口风。
小小候车厅,短暂停留的驿站。在这里,人们谋划更长的山水,更长的行程。
博客里的气味
网络降低了发表的门槛,形形色色的博客、微博,如同杂花满地,拂面相遇,总有些意外发现。
一次,在网上忽然闯入一名记者的博客。一篇篇看去,生活与采访的真实记录,桩桩件件来自生活底层的故事,冲撞着这名记者的心灵。他采访失学儿童,垂危而无法治愈的贫困病人,无计可施而被迫爬上高高的建筑讨要工资的农民工,报道之余,他痛苦地发出“近来为什么容易醉”?
他说以前是很少醉的,自己有八九两的酒量,可近来喝二三两就倒地醉了。由于经常接到弱势群体的求助,在采访中遇到诸多社会问题,有些事件报道后作用甚微,不能及时找到最佳的解决途径,所以作为一名有良知的记者,渐渐淤积起一些无法宣泄的负面情绪,为此而彷徨苦闷。
有人告诉我,这名记者就是我们报社的某某,我顿感意外。博客里的心灵释放与他平日的木讷内敛形成了强烈反差。在人群当中,他根本就是一块木头,即使熟人和他走路相遇,他几乎也是不说话的。
他还把自己被毙的稿件贴出来。也许是导向缘故吧,编辑为了慎重起见,没敢采用。一篇篇读来,感觉他博客里有一种令人不安的山雨欲来的压抑,读到紧迫处,甚至能闻出雨拍风尘的腥气。
前段时间,杂志社的一位朋友谈到了一个博客,便进去看看,越看越觉得博客的主人很像以前身边的一个人,话语颇耳熟,像黑暗小巷里飕飕的朔风,神秘,犀利。
她去采访一个美籍艾滋病志愿者,对话里有许多关于东西方文化的异质探访,比如对性观点的追问,那种近乎凌厉的采访风格,使我猛然想到她。对,就是她,有时她就是这样的,发问的时候喜欢穷追不舍,不管你是舒服还是不舒服。这一点有些像大牌主持人王志的风格。
她是报社的校对兼记者,在众人眼里她朴素、随和、爱笑。我并不知她还在写博文,并且把文字揉捏得如此逆常,完全迥异于她表面素色温和的日常生活。平时那么沉静的一汪水,博客里却暗浪层层涌动。或者说,人们眼中的她是一个面,而她的博客则像一眼离奇的井,趴在井边望去,触到的是幽深的洞穴,彻骨的罡风。
因为他和她,这两个博客与日常反差极大的人,我想,庸常平淡的背后可以堆砌着浪漫绮丽,平直苍白的背后可以抚触奇绝火热。如果说白日是通行规则的运行,博客则是黑夜自由心灵的涂抹与弹奏。
为了白日活动的安全,人类也需要像动物一样为自己抹点儿保护色,以适应大家共同生存的环境。
而内心世界,才是真实原态的,它是活跃的生命力在喷发游走,灵魂若磷火在星辰观照下随风飘移。
人类想的远比说出来的多,甚至我们想的远不是说出来的那回事。
或许因为生活中太多的言不由衷,博客才释放了这种有毒情绪,还原了真实,思想得以在这里自由呼吸舞蹈,个性之花得以在这里舒放自如,心灵之曲幽咽如泣,狂歌当哭。
因此,喜欢一个人的博客,是喜欢闻他文字里毫不遮掩的真切气味,活生生的,来自第一现场的观感思虑。
这两个记者,他们把笔墨浸泡在生活里,把生活中复杂的气味通过自己敏感的笔触提炼了出来,让人嗅到了真实和不安。这种真实的气味,没有经过香精的掩饰和伪装。就像一个女人在一群男人中间坐了,身上头发上被熏了呛人的浓浓烟雾。或是与朋友在一起吃了火锅,衣服丝丝缕缕的纤维里,都饱和了牛羊肉的膻腥。这种难以驱散的个性化的气息与味道,从博客里奔突逃逸,让每个经过的人意外驻足。
火车,火车铺满雪的铁轨
候车厅济济一堂,到处都是被大雪滞困的旅客,广播中传来一个男声:“某某次晚点,某某次晚点,给你带来的不便,我们表示抱歉。”
终于盼来了等待的车,好不容易挤上,没座位,连走动都不可能。我被夹在两车厢间,头顶不时有水珠滴下来,冰一下我的脑袋,我想避一避,来自背后的力量说明了抗议。
加一个人就可多挣一分利润,或者也不尽然,咱们是人口大国,这个省的人口又是全国之最。适逢春节,人们回家心切,这条线路所承载的就格外繁重了。
想起那个芜湖火车站遇难的女大学生,便觉今冬的寒冷。健康与平安要常默念于心,只要好好活着,便是福分。
坐火车变成了站火车,车厢内没什么好看,全是男人与女人麻木疲乏的脸,只好定定看着窗外。
雪覆盖了原野,公路上偶见农用三轮车奔忙。一排排失去叶子的小白杨,裸露了细密的枝条,远望,像是大地浓密的眼睫毛。旷野上一座被遗弃的小房子,树上一个个黑黑的鸟巢。村庄接着来了,庭院,宽宽的街门楼,甚至近得可以看见“和为贵”、“紫气东来”的字样。
十几年前,读过从维熙的小说《雪落黄河静无声》,小说情节忘了,只记得这个题目,下雪,黄河,这个意象落在我心中,呈现的是一种无边的静穆。当然,还是黄河边的一座小房子,那里面有人物的内在与外在活动。
黄河是一条悬在地面上的河,每次看到河床中间露出的片片沙滩,将黄河水隔开,黄河再不能恣肆狂奔,滔滔汹涌,显得无奈与柔弱。此时,一种沉重的思绪就蔓延过来,恨不得运用非凡力量将阻碍黄河脚步的泥沙都清走,给黄河一个可以奔腾无碍的深度与宽度。
雪地茫茫,红尘滚滚,总有些梦想难以割舍,迈出来,也就迈出来了。外面寒风凛冽,但开阔中延伸了人的思维,行走的快感很快就回到自身。
除了家人、身边的同事,常常见到的就是列车内的旅客了。我和他们之间反倒有种默契。
在自己的声音里前进
K179次列车早6∶07发车,站台周围还是一片朦胧的晨雾。等待着,列车来了,拥上去。对于突然“闯进”的乘客,列车上睡眼惺忪的乘客慵懒地睁开眼皮,瞅瞅,又困顿地掩上眼皮继续睡去。他们一定还有长长的旅程。
我开始找座位。一个男人躺在三个人的座位上,在上面睡觉,我朝他说了一句话,他有些不情愿地稍稍将身体弓起,脚头留下点空地,我才坐了下去。可他穿着袜子的脚还在我身边,这让我厌恶,但也不得不忍受。由于早上起得太早,没有完全从睡眠状态中解脱出来,于是靠着座背闭目小睡。
这时,一股浊臭气袭过来。男子的一双皮鞋,他的袜子,对面男子那双脱了鞋的脚,毫无例外,污染源就是这些。
对面两位男子在聊,一个在郑州郊区上班,但已“郊”到洛阳,另一位家住登封,现在北京做事,他们在谈手机卡哪一种更优惠。我觉得他们的闲聊是多余的,不如养神休息。不过,其中一个显然精力旺盛,另一个也是在应付。
1989年到1994年间,我和火车每年都有个约,在大中原与大东北之间咣当来回。此后火车在我的生命里便沉默下来,从颠沛流离到安居下来。随着丈夫转业,我充满荆棘意味的军嫂的称呼也被取消,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从动荡到安定,终于和这种生活说再见了。
谁知,命中有此注定。公元2007年,我竟又从豫北的一个城市跨越黄河来到了省城,但家并未随之迁移,所以又离不开火车这个家伙。
一位80后年轻作家写道:火车又开始在自己的声音里前进。我喜欢火车。从小,我就喜欢它单调寂寞的声音。
和她一样,在火车的声音中,我内心充盈着莫名的欢喜,或者疲倦。
吉卜赛
得知又要搬家,心里便掠过郁闷的云翳。好容易平静一段了,自以为要在这儿住个一年半载的。
站在居室里,透过窗,北边是高大蓊郁的女贞子,阳光下是她光线斑驳的枝条,长长的椎状花序,那种香气无所不入,在小区四处弥漫游走。枝条间生活着无数的灰喜鹊,灰喜鹊的分泌物随意泼洒到地面,院子的空地上全是层层的鸟粪,我不得不把自行车搬离树下。因为一夜醒来,马鞍上全是它们的恶作剧。
紧挨居室的南面长着与楼层一样高的悬铃木,想着是造楼的时候栽的,与楼有着不一般的亲情。清早拉开浅绿的窗帘,便现出它碧透的叶子,这是一种始终干净乐观的树,雨后更是清清爽爽,它总是抹过我心头的不悦。那种翠绿很容易地成为我心里的底色。
这旧而发亮的木质地板,朝南的大卧室。
这三层的楼高,如履平地,没怎么费劲就到了。
这诸多的好处是我不想搬走的原因。
外面的两个集贸市场,非常之方便。我已与这里形成一种默契。比如我一站在那个卖海产品杂货的小伙面前,他就微躬着身问:“要杏仁?一包还是两包?”
还有里面一家卖卤肉的小伙子。每星期必有一两次到这里,扫一眼油亮亮的肉品,最后固定在一个地方,喉咙里冒出水水的东西润着:“三只鸡爪。”
还有两块一袋的江米甜酒,打一个鸡蛋花洒上去,可以喝得浑身出汗。
说这些都没用,房子是租来的。这就意味着,随时都有搬走的可能,已经培养出的温馨也要无情抛掷。
街头有只肥公鸡,永远不过马路,在行道树下心定气闲地偎着卖干货的主人,它的活动范围就是几步之间,但它不急不怒,更不会在闹市不合时宜地引吭高歌。每次路过我都会瞥见它,这只在城市里淹没自己的公鸡。它乖乖的,适应了豢养,脚力与翅膀已经退化,丧失了奔跑和在同类中争霸的能力。嗓子如同摆设,再没有歌唱,也没有意见发表。
公鸡甚或雄鸡,这个代表性别与力量色彩的名字已经被它所阉割。
波德莱尔一生在巴黎搬过四十二次家,从出生的拉丁区某街,直到蒙巴那斯公墓。诗人北岛写道:“我虽如此热爱搬家,也没到波德莱尔那近乎疯狂的地步,尤其在一个自己土生土长的城市。准有什么东西让他不得安宁。”冥冥中,与心事重重的波德莱尔一样,有种不安宁的东西驱逐着我,因而,我遵从命运,并热爱搬家。
与诞生《恶之花》的波德莱尔所居住的巴黎不同,郑州有着明媚强烈的阿波罗之光,甚至光线过剩。
张爱玲也是一位热爱搬家的作家,据张爱玲遗嘱执行人林式同说,从1984年8月到1988年3月这三年半时间内,她平均每个星期搬家一次。这似乎是夸张,因为这样算下来,张爱玲搬家次数有一百八十多次,据说她随身携带着简易的行李,只要在住处发现跳蚤就马上离开。有人分析,搬家对她是一种心理病症,因为她一直在设法避开华丽旗袍上的虱子,从笔下对人生的怀疑,直到生活的具象,她一辈子都在与“虱子”死磕周旋。
是的,搬家,对每个人而言,各有各的道理,因为总有什么东西硌着了他的感觉,与其充满疑虑地住下去,不如采取唯一有效的行动。
当最后一只大纸箱搬进车尾,车子发动,我轻轻关上副驾驶车门,心里忽而滑出——“吉、卜、赛”,这来自异域,融入血液,令人战栗又带来快感的音节。
陇海路的那些蔷薇
几年前十月的一天,老家的一辆车捎我过来,将我丢在陇海西路这条干道上。看着它随即毫无牵挂地疾驰而去,如一沉重的物件,我不知将自己搬向哪里。
省城对于我的记忆几乎是个空白,也是个迷宫,对它的认识寥寥,省城人的熟面孔也仅是说过话的几个。
初中时的地理课本上写着,省城有两条铁路动脉经过,一条是南北走向的国家大动脉京广线,一条是东西走向的陇海线,陇海路因之而得名。与铁路线一样,它与另一条京广路相交。
一个人几年的光阴就在陇海西路上的一家单位驻扎下来。
最初的念想,像一只彩色气球,每天上班的路上都会拽着它。
日子一天天流走,岗位没有像预想的兑现。抑郁、泄气,朋友时时充当我的打气筒。他们和我一样把未来抱在心里。他们最常送我的礼物也是这样的气球。一只被现实的利器戳破了,另一只完好的就马上攥在我的手心里。
他们不肯让我的天空失落。大地可以陷落,天空却不能陷于绝境。
以陇海路为中心,我的住处曾经每隔一个时期摇摆于附近。几次迁徙,改变了我观望外界的目光,像一股被断开的水流,总能很快与新的水塘融为一处,共享这里的天光云影。我喜欢每处称之为家的地方,没过几天,周围的气息很快就消融掉我身上的生疏感,它们一个个亲近地聚拢过来。
周围的邻居,窗外的女贞泡桐,房主留下的弱小盆栽,都在我身边形成新的陪伴。
熟悉又失去。旧去,新又来,这一切变换着我的四时,在变化中顺应,守望。
命运似乎从青春期就开始了。二十年前,部队的一个炊事兵兄弟,操着满口棒子味的山东腔,对前来探亲的我叹服道:嫂子,你的适应能力很强啊。
对未知好奇,对将来不带偏见,瞳仁里放大世事的纯美。这种贯穿生活的心态不知是值得嘉勉,还是该称之为我一向的致命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