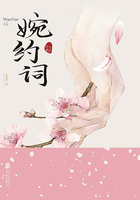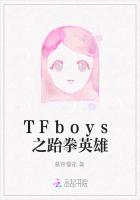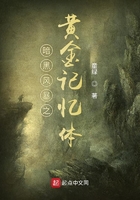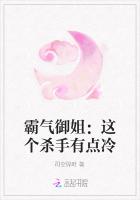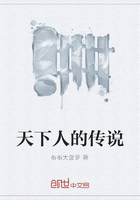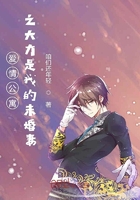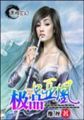荒芜之梅
春节回乡落脚,打听到一个老宾馆更为优惠,一家人带着行李奔过去,打开房门,见屋内整洁,还有小阳台,好不快活。美中不足的是,房间暖气稍欠,布局设施有些老套,但从另一面说,这石砌的建筑透出历史的味道,在当时来说一定是最好的了。
拉开窗帘,透过阳台瞰览小城,大半城区尽收眼底,再观两旁,左右皆苍翠松柏。猛然醒悟,住在这里性价比着实高了许多,因为这是风景区啊!
这个宾馆依山而建,在上世纪有着骄傲的历史和名望。现在,在众多新式酒店的对照下,它的身影才略显落寞,但读一读这座青石建筑铸就的过去,宾馆后门碑廊记载的名人墨迹,心里便会涌出万千感叹。
出门,下到坡底,即是百泉景区西华门。再从西华门一级级下去,足有二十来阶吧,这才踏到百泉湖边的土地。
不过,还可以踏着湖中的石阶,继续下,直至下到湖底。这不是白日说梦话,这是悲哀的现实——湖底不知何时变成荒草湖泊,一马“草”川。
时隔几年未见,也曾听闻百泉的衰变,但这一遇,还是一头撞蒙了,怀疑自己走错了地方,本要去旖旎温柔之乡,及至眼前,却是另番荒凉断肠之地,反差太大了,令人沉默无语。
百泉是家乡对外递出的名片,曾经婉丽清扬、美貌无比,如今却是华彩尽失,落为行乞,尘灰满面。湖北面有几间旧房,半面房顶已经坍塌,屋檩横斜得不成样子,如若一个裸露伤口却无钱去医治的贫病之人,简直令人痛心。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难道人世间就是这样的轮回,人以及自然的命运都逃不出时运的魔掌?
曾写过《流入诗经的泉水》一文,文章还就《诗经》中的泉水引来了地域之争。百泉妩媚、诗意、灵动的过往,转而成眼前的死寂、颓废、枯竭,唉,真的难以想象,它遇到了怎样的劫难,美好的自然遭遇怎样的涂炭。
偌大的湖,一旦失去清波浩渺,便等于抽去生命之附丽,与宣告死亡无异,从此的存在犹如横陈僵尸。
还是走一遭吧,脚步如同祭奠,祭奠逝去的那个泉水丰饶、明眸笑靥的少女般的百泉。
“苏门山涌金亭”落款眉山苏轼,当年苏学士亲见的盛况已不复存在,只留下这几个具有苏氏风格书法的大字让人生发幽情。
与涌金亭相对的是喷玉亭,“涌金喷玉”多么富于表现与诗意色彩的词汇,此时像是反讽讥笑,衍生遗恨。
好在宋代易学大师邵雍祠堂的腊梅安慰了我。
进去湖西侧这座徐世昌题有“驾风鞭霆”字样的院落,有一种异样的气息。正西的三间远远望去有邵雍的泥塑,身披黄衣,下面陈设香案。几年前这里并非如此摆设,现在一代大师也成了人们头顶上的神。不是破坏就是崇拜,一些事情总是走极端,为什么不能正常地当作学术与文物来保护?
脚步停留在一株不起眼的花木面前,走近才知是腊梅,悄悄折去两枝,如同携去大师思想的芳芬,满意而去。
出祠堂,一轮淡薄红日映于一株垂柳后,喜且留影,再观镜头,奇怪里面全无。虽寒气冽冽,到底不忍就此离去,于是沿着发亮的青石板桥曲折而行,途经清晖阁、湖心亭等,记忆中曲曲折折的影像也一一释放出来,儿子让我找以前留影的地方来个“记忆再现”,想想历年所游,从少年至今,全家、姐妹、朋友、同学……玩耍的次数如同百泉湖水的波纹那样繁密,如今,人事全非,岂能一一再现?
仰头望去,熟悉的苏门山似乎在向我招手。上面的每个台阶不知走过多少遍,往年,这里会吸引几多游人前来观光休闲,节日更是繁华异常,灯会、烟火,老少齐聚,游人如织,摩肩接踵,而今的冷落让人不适。
碑廊的圆门紧锁,里面珍贵的石碑在以前是开放的,看来又无法造访。只好顺着斜坡登苏门,再登晋孙登啸台,抚思其一啸千古,鸾音和鸣。其时,阮籍、嵇康尝追随至此,孙登并无言语相授。终了送嵇康一言,不要出世,嵇康未听信,后遭司马氏家族所害。
啸台为苏门山之巅,极目四周山苍野莽,几位白发老者窃窃私语,似在谈论时事,一位中年男人俯仰徜徉其间,也有三五游人嬉笑逗乐,做些不相关的事,说些不相关的话。如果孙登活在当世,茅草裹身、长发披散的他是否还是与众人无语?现代人观来,一定直呼是最酷的行为艺术。
百泉曾隐居着太多的遗世独立之灵魂,云烟已逝,泉水虽枯,魂灵犹在。
两日后,携两枝腊梅匆匆至黄河以南的郑州,一杯清水供上,几粒嫩黄花苞徐徐开放。置电脑旁,香芬袅袅,这是百泉的,也是曾隐居百泉的灵魂们的,每一朵,象征一个……
宓妃留枕
诗由兴发,或因嘉会,或因离群,而三国诗人曹植的《洛神赋》,则缘起洛水畔的一场梦遇。“翩若惊鸿,婉若游龙”,一千多字的娓娓描述,字字珠玑,暗香飘渺,旷世才子曹植,为何对洛神如此倾心,洛神原型又为何人?
历史记载《洛神赋》的原型是甄妃。甄妃出身名门,她的父亲甄逸是上蔡县令。虽然三岁丧父,但家境优裕,应该生活得无忧无虑。及笄后嫁与袁绍之子,袁绍也是一方诸侯。如果没有战乱,她的生活应该没有什么波澜,享受一生富贵。这样也就与曹操父子无缘,当然也与洛神的化身无关。像所有封建时代的女子一样,她的命运是被动的,从势顺应,贤淑知礼。囿于时代与环境,她只是男人的从属品,当夫家大势已去,随即沦为战胜方另一男人的财产。
甄妃为三国时期倾国美女,通文能诗,曹操父子三人皆为历史上之盖世雄才、诗人,随便哪个都可与她匹配唱和,况三人对她均爱慕有加,还有人说曹操打袁绍的那场战役就是为了甄妃。当儿子曹丕向他请示,想带走袁绍儿媳甄氏时,写出“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拥有帝王胸襟的曹操,唯有慷慨允诺,但也心怀缱绻,“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思慕之情终不能湮灭。
曹丕与父亲曹操一样,鞍马间为文,横槊赋诗,是位兼具文韬武略的帝王。虽说甄妃是作为战利品被掳掠而来,可面对这样一个人杰,也会为之心动吧,何况曹丕对她是真心爱恋。曹丕诗作《燕歌行》抒写的是边地征戍之苦及思妇相思之情:“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诗中的曹丕既是豪杰又是多情丈夫。
曹丕终究不是案前书生,为了他的统一大业,经常出外征战,只能将爱妃留在后方。小曹丕五岁的曹植便有了机会陪伴这位风华绝代的嫂嫂。生性自由浪漫、厌恶战争的曹植,与同样痛恨血腥战乱、有切身之痛的甄妃渐渐心有灵犀,声息相通。李商隐曾写下“宓妃留枕魏王才”,是真是假,已入了义山诗人的诗句。
爱情从来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当曹植在曹丕的剑锋下用血泪咏出那首句句如同惊雷的《七步诗》时,兄弟之情战胜了杀戮之心,但曹植也开始了被贬流放的命运。
历史传说中,心生悔意的曹丕将甄妃用过的金缕玉带枕送给曹植,曹植路过洛水,有感而发,成就了千古名篇《洛神赋》。也有说《洛神赋》原名为《感甄赋》,后因曹丕与甄妃之子曹睿避讳才改为《洛神赋》。
曹丕与甄妃也曾恩爱相守,生有一子一女,而后甄妃色衰失宠,郁闷中未免写幽怨诗释怀,甄妃在诗作《塘上行》中咏道,“众口铄黄金,使君生别离”,本来是写给丈夫曹丕的,却成罪证,曹丕听信谗言,令甄妃自决,夫妻的绝情如此令人堪叹。
在曹植的梦里,是美与理想的耸立,但面对现实都是不堪一击。一个是帝王之梦,建功立业的雄心。一个是爱情的不可触及,如梦如幻牵引着他的寻觅之途。
郑州歌舞剧院近年有原创舞剧《水月洛神》面世。公演那天,当《水月洛神》完美落幕,舞台上的“洛神”卸装后出现在媒体面前。只见她体态窈窕而不失健硕,舞台上古典忧戚,现实中讷言羞涩。令人惊讶的是,演员才十九芳龄。想想那时甄妃失宠时已四十多岁了,甄妃几经辗转,身如浮萍,人物内心一定是深沉沧桑。一个十九岁女孩,人生经历几为空白,演这个人物实有很大挑战性。人物穿梭于曹丕、曹植兄弟之间,矛盾、冲突时时迭起,都须掌控演绎到位。果然,女孩讲到创作难度时用了“内心纠结”这个词。
甄妃与曹丕,陷落,挣脱,纠结,归顺。甄妃与曹植,心生万千情愫,却无瞬息接触,亦不能回眸一顾。《水月洛神》巧妙地运用一把古琴,委婉表达两人的琴瑟相鸣,只见甄妃将自己的琴送给即将流放的曹植,失意的曹植怀抱古琴踉跄而去,犹似抱着自己破碎的灵魂。
剧情演到生死别离这场戏,舞台上十分写意地垂下一条长长白绫,美丽哀怨的甄妃结束了年轻的生命,香魂化作一缕青烟,离开这纷扰世间。
恰如凤凰涅,甄妃告别了甄妃,而后成为曹植心目中至高无上的洛神。
发生在甄妃与曹植之间的事情,本就是现实中的梦,追逐的结果定然是被撕裂,只有在神界才能达到自由、圆满、极致,华丽的爱情才能如愿迸发、呈现,也让观众欣赏到艺术世界的巅峰之美。
宋玉梦见神女而有《神女赋》,湘夫人因屈原而传世。在曹植眼中,一个中国美神与爱神的结合体——洛神,从洛水上凌波御风而来。“竦轻躯以鹤立,若将飞而未翔”,曹植与她在洛水河畔神会良久。
“怅盘桓而不能去”,这是曹植《洛神赋》的尾句。当人与神在清水皓月之间演绎那一场极品爱情后,想必久久不愿离去的观众也是如此心情吧。
月下的呈现与照亮
夜的呼吸,在月亮的引力下起伏着。
吃过晚餐,三人沿辉焦公路向东缓行,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圆月悬于东南方向,光华威仪。
桥上不时有拉货的大卡车轰隆驶来,谈话和步伐因此乱了阵脚。桥左侧的河谷里亮着微弱的橘黄灯火,一家采石厂正在作业,不远处的桥头上也有一家,碎好的沙子堆在一旁。他们碎石,也碎一个个的夜,夜的耳朵被撞击得几乎失聪。
生于19世纪崇尚自然的英国作家劳伦斯,对大地上充斥的越来越多的机械的喧嚣,进行谴责与批判。但文字的这类表达何其纤弱苍白,它只存在于文人对某种境域的耽沉与恋守。结果是,世界越来越聒噪,像一辆超载的车辆,碾压着人们脆弱的神经,并冲进黑夜,粉碎角落里的幻梦。
因而,我们一致期盼前面出现一条离开峪河大桥的岔道,并想着这条道是乡间原始的不规则的土路,寂寥,幽谧,适合诗歌和散文活动的氛围,因为我们一行全是属于这种意境下气质相类的人。
月亮是整个夜晚活动的核心,它的存在更具诱惑性。它引导我们的目光、话语乃至心理活动。它给我们看到的事物蒙上了薄雾般的玄思,又像给一本书加了薄膜的包装,让人更加愿意去抚摸,从而想象其中文字的美妙。
白天看到的太行山本来在西边,这时却神奇地出现在北面,不可逾越地横亘眼前,也许是我的方向感出了问题。山腰上两颗星在闪。细看,那里有人居住。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有光亮,这是一个温暖的逻辑。
终于在桥头发现可以下到河沟的路,但中间要经过一片乱石。经过判断,一行人果敢地通过决定。
月光在石块上晃动,像在透明的水里,我们小心平衡着歪斜参差的脚步。
双脚先是落入一片花生地。花生棵暗示了土地里睡着的果实,月光暗示了空气中诗意的流转。畅快地翕动鼻翼,若嬉水的鸭子扑进碧波。采石厂的噪声渐远,此地纯属自然的生态,喜悦在心底清澈活泛起来。
枯干的河沟,是月光下眯着眼的荒古野地。
这瞬间拥有的快乐,是因为心灵呼吸到了自由。“摆脱”与“进入”总是在争斗,而我们终于明白,“摆脱”总是不可能,而逃避地进入给了我们可能,适当地创造这种机会则是节日与盛宴。多少年来,没有过这种夜间的野外行走,这行走摒弃了汽车尾气与噪声,摒弃了霓虹光影,只有草叶间蛐蛐高高低低的鸣奏爬到耳边。
这是一个比一切缤纷光影与华丽歌声更值得沉浸与倾听的晚会,舞台由自然景物搭建,月亮是最好的照明师,秋虫躺在叶子的帷幕后,有的正在花生地里逡巡,有的在收获过的土地上看守,不管在什么位置,它们都在演出,季节是首席指挥,小生灵拉响了生命本能的丝弦。
柔软蜿蜒着的乡间小道,踏上它,就踏入了记忆的回归。
茸茸黄土上印着童真的脚印,泼洒着无端的欢喜,花布鞋,柳条筐,木制小推车,都从这条道上迤逦奔涌而来。
月光把它照成镜子一般的银白。置身于此,这土地倏然使我变作一株乡间的作物,精神忽而蓬勃起来,大脑和手脚不像白日在人前的拘谨,身上的每个毛孔仿若都得到清洗和疏通。近处和远处,清晰或模糊的图像,都是自由亲切的王国,连石头的呼吸也生动可闻。我只愿在这条路上行走下去,只愿延长这样行走的时间,唯恐另外的两位说,好了,咱们折回去吧。
那样,我会孩子一样失望。像走入了往日的时光隧道,容我再留恋抚摸一番。
我想起幼时在月光下做的游戏,中间隔着几十年的岁月。同行的他们不是我小时的玩伴,他们脚步沉稳,充满哲思的意味。不再心无挂碍、顽皮天真,却如此怀念天真的岁月。路旁的柿树挂了一盏盏灯,照亮了他们记忆中无忧的童年。树上的果,地里的瓜,哪一个不勾得他们嘴馋。其中一个回忆起看电影的趣事,或许是他少年时期印象最深的杰作——
一天夜里,也是一个月光的晚上,他和几个小伙伴在村口的几个柴垛间捉迷藏,当他顶着满头柴火屑钻出来时,却怎么也找不见伙伴们,这时遇见一个骑车子的问路人,看着那人带来的一些“匣子”,他认定他是个电影放映员。原来,这人准备到邻村放映电影,天黑迷了路。他问:“演什么电影?”那人说是两个战争片。他一听怦然心动,那两个片子都是他的最爱,里面有他崇拜的战斗英雄。
他将那人引到自己的村庄,并在村里散播“今晚演电影”的谎言。
三十年前的农村,文化生活何其贫乏。不像现在,电视、电脑是寻常之物。村里很长时间才能演场电影,每逢这天就如同过节一样热闹。所以,他就想让自己和村里人也过过节。
可想而知,他的这个谎言像一阵风潜入村里,吹得人们心头痒起来。村干部却哭笑不得,不得不以假成真,拿出生产成果,来换取村民的文化大餐。这是孩童时误打误撞的一场导演,却收到一个光明灿烂的结果,他的骄傲讲述使过去无限美好起来。
物质贫乏的时代,精神生活亦单调,那时他就对文化生活有一种隐秘向往。所以,如今他虽担任着复杂的行政工作,却还不忘做一个发现美歌咏美的诗人。
今夜,我们在一条河,一条记忆的河,试图抓住河里一条条曾经欢蹦乱跳的不寻常的鱼。
峪河的声音泠泠传来。
这是一条细弱的河流,在月光下跳动着光波。我们讨论了一会儿它的来处,最后朋友得出结论,它应是卫河的一个源头。在它的声音熏陶下,我们也像祖师爷孔子一样默然,望着河谷、月亮,想到几十年、一百年后,河流仍然存在,而月下谈笑的几个人,已成荒冢。
让人敬畏的河流。
不知谁说了一句,起风了,我们走吧。
我们没按来路返回,而去重新开辟新的道路。一块油菜地,一块不知名的收割过的田地,一棵棵看不清面目的野草。这些野草也许是我小时候寻找过的野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