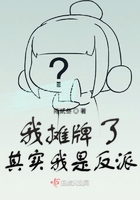黄烨
那个夏天开始的第一天,我径直去了 W 城,只因魏何的一句“W 城也有‘天 与地’”。——单纯至极的目的,就像当初我什么也没想 就去了 S 城,单是认定自己 的梦想在那里。
我拎很少的行李到 W 城,车站拥挤,站台不让送行,过往离别的画面终究成 了臆想。粉红色的车票捏在手中,仿佛随时会脱离,上车时人们总是争先恐后,我 总愿站在一旁静静看他们的姿态,未了才拎起行李尾随。
他们不知,先来抑或是后到,其实终究,都是一样的。 我就这样到了 W 城。 我就这样又一次见到了魏何,还有忍冬。
我们三个人相遇是在“天与地”——S 城。说来也是极有戏剧性的,天南海北 的三个人,想来是一辈子都不可能有什么交集的,确实这样说碰到就碰到了。“天与地” 也不是什么简单的地方,鱼龙混杂的,三人竟能在嘈杂的人群中碰见彼此,互相碰 了杯,交换了姓名也就算认识了。聊下来却竟也投机,缘分很多时候就是这么回事, 惺惺相惜的,千里相隔也不过是 弹指一挥就 解决的问题。那天,三人都喝了不少, 聊到后来竟都碰了心里的伤,落了泪。头次见面就敞开心扉的少,完全裸露的心还 能不让彼此恶心的更少,不让彼此恶心反而相见恨晚的就少之又少。于是我们三人 互留了号码地址,约定相遇下一个“天与地”。
W 城一聚,便因此而起。
其实那次事后我去找忍冬,穿越大半个中国,也是没由来地想念他,我认定万 里之外的他能懂,一厢情愿地去往 B 城找他,从我所在的 G 城北上,穿越地域的 垂直差异与人情的变化,眼看热带风情变成江南的恬静最后转为北方的风沙。我心 中藏着惴动,快到 B 城时拨通忍冬的电话告诉他自己行将到来。
一个人热情是好,过于热情了就显得轻佻。可惜我当时没想到,我把自己与忍 冬的投机当了真正的缘分,毫不保留地坦着自己的心思情绪却忽略了他的承受程度。 忍冬小我几岁,典型的北方少年,可惜这年头南北大有要对调性格的趋势,南方男 子们个个强悍了起来,北方汉子们倒落得心细了,也许憋屈久了就都得变,谁受得 了一天到晚的单样儿?就像我,憋屈久了也得变。
忍冬到车站接我,我说自己待几天就走,料得忍冬会说几句挽留的话,男女相交, 多是依着对方的性子,男孩子也得跟着女孩子发发嗲拉你的手学你的话,他却神情 恍惚地说好。心里也不知怎么一下冷落了起来。
毕竟只见过一次,就这样找上来终究不太好。 我在心里开始有些悔了。
忍冬在校外租房子,很小的那种,专供学生的,比宿舍强不了太多,我见他房 里的饼干泡面便说 :“这怎么行?姐姐给你做有营养的!”二话没说拎着钱包就跑了, 回来时手上多出许多大卖场的绿叶食物,我怕生腥的东西,自己平时也多吃素,倒 也凑合,却忘了眼前的小肉食动物,只能抱歉。忍冬从冰箱拿出速冻牛排揉着我的 头发对我笑说 :“你这个傻子!”
想是舟车劳 顿,菜 烧 得失了水准,吃是能吃,不免碍了胃口。忍冬不多言语, 细细地拣菜堆中的肉丝肉沫,他吃得安稳,亦未曾抱怨,如同驯服的食草动物。
这样的男孩,看了总要让人心生欢喜的。 饭罢疲极,与忍冬坐在他的小床上看一部片子,温馨的爱情片,两个因为任性
而无法相爱的恋人,片子色彩瑰丽,音乐亦作得丰盛,我靠着忍冬的肩不紧不慢地看, 他取下眼镜用衣角随意地擦拭着,我也摘下无镜片的眼镜要叫他擦,他被逗得笑起 来,不深不浅的两个嘴窝露出来,黑暗中在电脑屏幕的光下若隐若现。忍冬假装很
认真地擦起来,拿起来对着虚有的镜片哈气,用自己衣服干净的一角细细擦拭,末 了小心检查,转过头满意地要给我戴上。
然而忍冬转过头看到我的脸表情就变了:“颐朵,你怎么哭了?”他急急地问。 我急忙抹上眼睛,一手的泪水,我扯起嘴角对忍冬笑,“我没事儿,我没事儿……”
也不知怎么的,一说这话我自己就先受不住了,一下子落下泪来。忍冬忙手忙脚地给 我找面巾,我说 :“忍冬,我真没事儿,我看电影呢,你看这电影演得多好是吧……” 忍冬将信将疑望着我,我指他看屏幕,荧上两个苦恋的情人终于解开心结,修成正 果,吻得正起劲,我看着画面心里也纳闷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却又忍不住哭出声来。 忍冬看屏幕又看我,不说话,只单一把将我揽入怀里。
他胸膛宽阔。我将泪流在他肩上,小声与他说 :“忍冬,我有过一个弟弟,与你 一般大,小时他便死了,若他在,我也能常有这样一个肩膀,这样一个依赖了。”
忍冬的身体短促地颤抖了一下,复又将我抱得更紧。夜像海,我依着他这只小舟, 摇晃前行,却再也不怕风浪,我与他低低说我弟弟小时的事情。事已多年,其实我 根本不记得什么,若不是这么多年父母的提起。我大约是早已忘掉了的。小孩本是 残忍的,长大了便更冷漠,我说小时弟弟与我在街上的相互追逐,说他偷偷塞给我 他偷拿的糖果,说我答应长大后做他的新娘……
不知讲了多久,眼皮是支撑不住了的,言语却无停断,也不知是什么在支撑自己。 忍冬房间的空气混着泪,漾出发酵的味道。
忍冬只是听我说。他一语未发我却知他在听,一字一句地听,句句用心地听, 我感动,却止不住心里的伤。
天色渐亮,我终于疲极,睡倒在他的床,忍冬为我摆好枕头,掖了被子,叹了口气, 轻轻地,他说 :“颐朵,你都不知道自己藏不住话吗,你说的明明不是你弟弟,你说 的明明是你爱的人啊……”我思绪迷蒙,亦分不清是梦是醒,只听低低一句:“颐朵, 你不知我喜欢你吗?”
第二天我卷了所有行李仓皇而逃,不论昨晚的一切是否真实,离开总是最好的 办法。
我总是这样,习惯逃离。 忍冬的话像一盆水,硬生生泼在我这团火上,我对他热情是因了把他当朋友,
当弟弟,殊不知他生出了别的感情,我自责,伤心也遗憾。恋人好找,朋友却少,失 了忍冬,我下一次心碎该去哪里?若我被海上暴雨所噬去哪再见白帆再起?
不久魏何挂来电话,说 W 城也有“天与地”,我匆忙赶来,见到魏何。意料之外, 忍冬也在。
魏何笑着接过我的行李,说三人再聚必有好事,我心中却情绪复杂。 三人相聚,却各自心怀鬼胎。 魏何大我 几岁,已经 工作,准确说是已经 退学工作,他做设 计,电脑、绘画,
摄影与文字也略有接触,懂得品音乐,读音节,灵魂与摇滚相通,却长了一副爵士 的外表,随意却掩不住骨子中的不羁与满腔的才华。他是内陆男子,性格直条却又 复杂,不难摸透却难捉摸。忍冬其实也是放荡的,野心藏在他年幼的身体里,孜孜 不倦地燃烧,我们三个,也正是因为这点而意趣相投,我们都向往魏何的生活,却 只有魏何真正得到了这般生活。
我装作释然,嬉笑与他去向魏何的住处——一个独立工作室,不似想象中的糟 乱,他亦是个干净的男子。我们说来也是“愤青”,小屋中迅速溢满了我们的高谈阔论。 聊天并不是女生的专项,要知道真废话起来,男人也未必差,不然相声怎么净是男 的说的?
说到激动之处他们俩在一起争,我在一旁看。忍冬停下来朝我看 :“颐朵怎么 不说话?”眼中射出渴望的光来,我急急躲认,推辞对话题并不熟,眼光唯恐地躲 向一边。魏何也说 :“在‘天与地’,记得颐朵是说得最多的,怎么今天腼腆起来了?” 我推说旅途劳累,忍冬忙让魏何腾床 给我,我忽然心中生出一丝害怕,怕伤忍冬, 忙又装出精神百倍的样子,他们俩将信将疑,我真恨不得马上跑个千米给他们看。
W 城也是繁华之地,魏何提前完成了 case 陪我们闲逛。
城市雕塑被火热的太阳烤得发烫,魏何偏冲上去要与雕像拍那种看了让人浮想 联翩的 pose,我与忍冬拍下他,他好不得意。
三人日益熟络,本来就臭味相投又是一连几天待在一起更是熟得恨不得认同一 个爹妈,我将忍冬喊作弟弟,他也不回避地叫姐,我想真好,终究释了心结。
我拖魏何带我去 W 城著名的商业广场疯狂购物,他们看我一副势要将卡刷爆 的样子,吐着舌头骂我败家,我就把他们拖进内衣店看我买内衣,导购小姐耐心地 讲解,把自己的胸揉得像面团,我偷偷斜眼望去,魏何倒是在众人的目光中脸不红 心不跳的,到底是混过江湖见过市面的。只有忍冬不断看着 bra 叹着“世界真是虚伪” 来掩盖自己的窘迫。我一把将买好的 bra 塞到他手里说 :“你们男人因为胸爱女人 才虚伪呢!”逛夜市吃小摊,也是三人买不同的,你一口我一口,我的勺伸你的碗中, 有次我买的那份最好吃我一边吃一边赞叹引来了你们的一勺又一勺,可怜我只能哀 怨地看着自己的碗一点点空下去,下次学乖了买了好吃的就不断喊难吃,没想到他 们又伸勺子过来,连说“让我见识下什么这么难吃”。尝了鲜他们变本加厉连碗也夺过, 美其名曰 :“帮助受灾群众”,我更是百口莫辩。
就这样一日日游荡,一日日欢笑。 若是时间停留在此,纵使拿一生来换,也定是没有犹豫的了。
我们再去“天与地”是一个夜晚,W 城的“天与地”与 S 城的不同,W 城的“天 与地”竟是一个安静的地方。
魏何跑去帮我们买饮料,只剩我与忍冬,闲聊起来,忍冬说“:其实我也有个姐姐。” 我本看远处,听了他的话偏过头惊叫 :“是吗?!”忍冬微微一笑说 :“很小的时
候死了。”我笑起来 :“骗人的吧!”忍冬也笑,我朝他砸过拳头,他也不还手。 忍冬说 :“颐朵你知道吗,其实你的眼里一直只有远方。”
我朝他说 :“我们不都是,都在朝自己想要去的地方前行啊。”
忍冬说 :“不是,你想去远方并不是因为远方有你想要的,而是因为你惧怕过去 与现在。”
我被击了软肋,低下头不言语。
忍冬说 :“若你想去远方,请让我陪你一起流浪。”
其实我没有告诉忍冬,我爱一个人,这个人叫魏何,我第一次见他是在“天与地”, 第一次认识他也是在“天与地”。也正是魏何,在百万人中吸引我前往。我热爱流浪, 热爱远方,热爱逃亡,热爱那些没有目的的剪辑,热爱火车前行时的摇晃,如同在 母体中,随生命的滋长而震颤,而魏何,他就是我的流浪,我的远方,我像一只猎犬, 不,或许猎犬都不是,我闭上眼,关上耳朵蒙了口鼻我都知道他在哪,是的,他是 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着我前往,一切有关他的都足以让我失魂,我密谋向他出发, 直至我们三人在“天与地”的那次交汇。
我并不讨厌忍冬,如若没有魏何我定是会爱上他的,这样一个让人温暖的男孩 子。但若爱上一个人,心与身便不再是自己的了,它们背离自己而去,脑也支配不了 自己,若爱一个人,必然也爱他给你的这般折磨,我们好比一张张粘贴纸,未撕前 以为自己是完好的,一旦爱上了人,撕下了胶贴便漾出不绝的疼痛,分离出两个自己。 心的自己是粘人的一半,是要紧紧贴上自己爱的人 ;身的自己却徒留黄黄的一薄片, 没了表情没了魂魄,只有终日的恍惚。
魏何于我就是这样一个,他 就像一张长而炫目的波谱,从左至右,从长至短, 迅速掠过我的可见范围,依赖着流浪呼啸而去。
然而我知道魏何并不喜欢我,我于他如同忍冬于我一样,感情并不是一般等价 物,我说不爱魏何了这份感情便会转向忍冬,距离是这样一件事情,记得有个词叫 in distance,我与你,只要在距离中不论靠得再近也终有芥蒂,无法彼此相拥。忍 冬给我看的片子,讲的就是这,我看了便落下泪,亦不知他是真傻或假天真。
我想“天与地”其实就是指我和你吧。 真讽刺。
那晚我们又喝了许多,我其实是向来不易被酒精麻痹的,不过是精神上觉得“该
醉了”便迷糊起来。他们俩喝多了,抱着对方喊兄弟,魏何醉至深处朝我说“:颐朵, 难道你看不出忍冬喜欢你吗?”
我当即落了泪,魏何,为何你亦未曾看出我爱你。 第二天清晨,我收拾东西离开,盛宴总是要散的,我们相处,总不可以太当真,
太当真了也就该散了,S 城的“天与地”喧嚣而华美,W 城的“天与地”淡而伤感, 我想我再也不会来 W 城与“天与地”了,天与地总是以为自己天天相望,离得很近, 殊不知天终究是天,地终究是地,见得再多也无法相聚。
回忆是把精美的刀,等一切往事过去后便冷不防刻进你身体,痛彻心扉,忍冬 说我害怕过去与现在,我没有告诉他我只是害怕回忆而已。
于是第二天我背起包,走进另一片天,走进另一方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