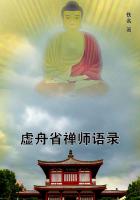车里很挤,马可把杨玉英箍怀里。他感觉到她脖子里的血像喷泉汩汩地喷着,在前方车辆刺眼的光亮中,他看到自己手掌心里粘稠的血已经快凝固。刘敬明就坐在马可身边。这个智障的胖子不停地哆嗦着,嗓门里不时发出怪兽般急促的咆哮声。他说她干吗不让他拿掉在床下的蜡笔小新呢,他说她不知道小新睡在地板上会害怕吗?他说她还用脚踩小新,他说她不光用脚踩小新还用脚揣了他裤裆,他说他没想用刀砍她是她先用菜刀吓唬他的,他说他不砍她她就会砍了他,他只好先用菜刀砍了她的脖子,这样的话他就能带着小新安全回家了……蓬蓬开着车一声不吭,索亚男跟蝎子不停地抽烟。
“死了吗?”索亚男问。
马可只是把杨玉英箍怀里,他的衣服已经被她的血浸湿了。
“死了的话就直接奔橐驼河,”索亚男说,“过两天可能水库排水。扔进去没人会知道。”
“我操你妈索亚男。”马可很安静地骂道,“我操你妈索亚男。”
“你激动个屁。你不是早对她厌倦了么?”索亚男说,“她死了正好,你再找个漂亮的。”
“我操你妈索亚男。”马可很安静地骂道,“我操你妈索亚男。”
“你不用骂我。你跟我一样,都是垃圾。”
“我操你妈索亚男。”马可很安静地骂道,“我操你妈索亚男。”
索亚男就没再说话。索亚男没说话,蓬蓬没说话,蝎子没说话,连刘敬明也不说话了。车里突然静下来。马可不知道蓬蓬会把车开向哪里……是开到医院还是真地开到橐驼河呢?他一点都不想知道。她快死了,开到哪里都是无所谓的…….杨玉英的身体开始还不住地抖动,现在是连抖动都没有了,她手臂上的温度也在一点点消失殆尽。他垂头看她。他突然想起两年前的那个夜晚。杨玉英花了五百块钱从北京打车来到酒吧时,已经是凌晨三点。马可正躺在前厅的沙发上酣睡,她费力地抱他,他不动,她就招呼出租车司机进来,将他抬进出租车。在车里的时候,他好象睡着,也好象醒着,杨玉英也这么着半倚在他瘦弱的胸膛,一双手抓着他的双手。她的手很凉,掌心是粗糙的茧花。后来,她一双手匍匐着伸进他的衬衣,他听到她小声嘀咕着,我们回家,我们回家……她的声音有些哽咽,他没动,那时他想,这个女人,肯定也喝酒了,要不她就是疯了,跑这么老远的路带他回家。不,她一定是疯了……
她现在就在他怀里,她的手不知道什么时候动了动,将他的手搭在她的小腹上。她肯定想告诉他一些话,可是她说不出来。她想告诉他存折藏在哪里了吗?还是一些别的什么?无从知晓了。花车转弯路过时代广场时,一排排烟花突然就盛开起来,让马可不由自主哆嗦了一下。马可想,一定是哪家商场在搞文艺汇演了,他们总是在夜晚的广场上演出些可笑的剧目,也不管有没有人欣赏。是的,马可已经听到了隐隐约约的歌声,一个花腔女高音正拔着嗓子唱一首非常古老的民歌。她的声音被夜风吹得时而飘渺时而真切,同时颤悠的歌声将明亮的烟花刺激地更为绚烂。当又一簇耀眼的烟花在黑幕中乍然怒放时,马可借着色彩斑斓的光亮看了看杨玉英的脸。她眼睛紧闭着,两行清泪顺着她逐渐萎缩的鼻翼,静静地流到她干瘪的嘴唇上。马可不知道这泪是他的,还是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