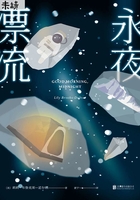这年的秋天来得特别早,还没到国庆就有不少人匆匆忙忙穿上了长袖的衣服。我不想再等,人生不应该是一场等待,更不应该等待一只习惯于攀墙的鹅。我决计要走。我半个月来一直不停地用手指在桌面上练习书法,我只写一个字――“闽”,门里虫。我想我不是虫,我有完整的双脚,我可以走。棒槌兄见说不动我,他叹一口气,说,八月十五,我请你喝酒。
八月十五夜,天蓝,奇迹一般的蓝,月黄如纸,边上一圈淡淡的光芒,捉摸不定,多看一会,眼酸,月亮太薄,似乎风一紧就会将它吹没了,怎么看都像是贴上去的。
我们坐在皓月岩下的皓月酒店的院子里。闽南有许多石头山,皓月岩是白水地面最著名的石头山,比皓月岩名气还大的是皓月酒店的盐鸡,盐鸡就是把鸡扒干净了白纸包起来,塞进盐巴堆里生烤。烤熟了撕开,天,香得盲肠也要抽筋,每一厘米的鸡骨头都不想放过。皓月酒店的院子没有围墙,只是虚虚地点了一线的盆栽菊花。院子里,百来张桌子,桌面上起起落落着忙碌的手,空气里都是啃鸡骨头的声音,都是鸡肉的香味,场面壮观宏大,动人,天上的月亮也有些把持不住。
我有个愿望,想把月亮倒进杯里,一口喝下去。
棒槌兄为了起到模范带头作用,不到半小时就把自己喝高了,右手五个粗短的指头把左手的指头捏在掌心里,不住地使劲。
他不笑,他不停地说话。
他说,我们是群白老鼠,时不时被抓起来扎一下针,死一批,剩下的,再扎另一种针,再死一大批,能活下来的,太不容易了!
他说,白老鼠活下来了,可时间没有了,时间是属水的,你伸手去抓,什么都抓不着,只落个两手湿答答。
他说,我们该学习该长身体的时候,赶我们到乡下和农民抢食!社员都是向阳花,每日围着墙根儿跟着太阳转,墙上写着:“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天天面对那堵墙,日子一天一天暗淡下去,那时候,不知道希望在哪里。
他说,我们都是坐在火车里的人,突然发现火车走错方向了,但是,这个时候,谁都不敢跳车。
他说,我们为什么歧视残疾人?因为我们是个靠身体吃饭的国度,不靠脑子或者思想,靠屁股。
他好像发现自己的说法有点不合适,他看了鹏程一眼,低头咬了一下下唇。往嘴里倒了一杯啤酒后,他拿纸巾仔细擦了擦手指,然后,双手搭上鹏程的肩膀:“兄弟,你不用担心,你男人女腔,命中注定大富大贵,我们苏部长也男人女腔。”
鹏程脸色有变,腮帮凹下去,嘴巴动了半天,没吐出一个词来。
忽然一阵冷风,一百米外刹住一排的士,侧门弹开,扑棱棱蹿出一百多号青少年,个个西瓜大砍刀,举过头顶,呀呀叫着奔涌过来:“有没看到……有没看到……”
他们喊的是闽南话,他们要找的人好像叫“肚皮疼”,如果不是刀锋闪亮,我会当场把嘴里的啤酒喷成雾和雪。
涌进来,问老板,老板抖着嗓子说,没有吧,我没、我没听过这名字。这时,一个少年突然尖叫一声揪住鹏程的领口,鹏程正把头埋在桌面下啃鸡腿骨:“啊,在这里!”挥刀欲劈。我手刚刚抓着椅子的靠背,棒槌兄已经撞进两人之间:“慢点!慢点!别劈错了!人命关天!”过来一个上身只穿文身的青年,手里拖着西瓜刀,他抽出一张照片歪着头看了鹏程一会儿:“错了!那人比他胖一点。”
西瓜刀一收,潮水似的退去了。路面空荡荡的,太安静了,静得连月亮的脚步声都听得见。
鹏程脸色白得像高考的草稿纸,上牙不住地敲打下牙:“不是我,不是我……”
我把手里的靠背椅放下了,一抹头脸,都是水,咸,冰凉。我闻到了菊花刺鼻的香味。
棒槌兄说,阿弥陀佛,幸好你不是干部。他的语气平和,好像刚才只不过是一场恶作剧。
啃鸡骨的声音再次响起,有人划起拳来。鹏程不咬牙齿了,他端起杯子说,谢谢你,棒槌兄。
我举了酒杯磕向棒槌兄:“大兄,谢谢你!我走后,请大兄好好照顾鹏程!”
棒槌兄连连点头,我的眼角却瞥见鹏程抬头望着月亮,鼻孔里轻轻嗤出一声来,那一声在一片咀嚼声中,显得那么刺耳,冰冷。我一下就失了兴致。也许,也许他是鼻炎发作。
鹏程就在我面前,可我再也够不着他了,怎么伸手也不行。我知道,我和鹏程之间出了什么问题,但我不是故意的,因为我如果故意伤害别人,我会看不起我自己。
那是刚入夏天的一个傍晚,花香袭人,我们在宿舍里学泡功夫茶,无意中看到小舟从苏部长家攀着墙翻到花圃里来,小舟手脚很麻利,但此刻小舟身上着装很不规范,下到地面时,小舟把上身的那点布料脱下来,在月光下仔细调理了一番。小舟比月光还白,小舟身材宜人,一眼就让你明白健康身体的重要性。小舟是鹏程所在节目组的主持人,小舟眉心有颗美人痣,紫红,让人过目难忘。鹏程的呼吸一声重过一声,上身快探到窗外去了。
我笑了:“花朵是植物的生殖器。小舟就像花儿一样。”
说完我就出去吃饭了。回来时,宿舍里一片黑暗,只有浴室的门缝还漏出一线光亮。我心里想,鹏程这家伙,老是忘了关灯。我刚才在一家江西饭馆吃的饭,没想到,江西菜竟然差点辣掉我的舌头,只好再吃下两瓶啤酒,可是,还没到家啤酒就变成了另外一种液体,在膀胱里来来回回地使劲,受不了了,赶紧冲向卫生间。
我推开卫生间的门。我的天!鹏程正握着自己的第三条腿,模拟活塞运动,他神态投入,动作极端夸张。鹏程的眼神!我永远都忘不了!绝望,羞辱,仇恨,蓝幽幽的,似乎有把我切成碎段的强烈需要。我竟然说,继续继续。要是我说你看没看到我床头的《骑兵军》多好啊,那样我就是什么也没看到。